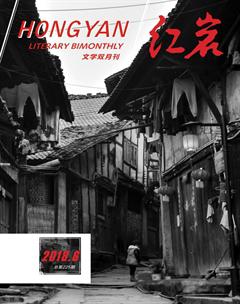在回忆里走
东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发表作品百余万字。曾两次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儿童文学)。山西省作协委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5年,我上了高中。
那时,小城只有两所众人认可的中学,一中和二中。人们以为,它们的差别不大。
一中在城外,距颓败的北门口还有一段路,不走大路走小路,要经过一片田野。夏天时,地里种了麦子,麦绿麦黄,在麦垅间走,远远看,风吹麦浪,腿没在起伏的麦子里,人仿佛坐了船,在漂移。
二中在城内,中心地带,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龙王庙街十字路口交汇的一侧。龙王庙街本该叫西大街,人死了,称驾鹤西行,于是活人走西路便不吉利,故称龙王庙街。
二中的历史长,校址是早年间的文庙。文庙里有过叫凤鸣书院的学堂。后来求学的人多了,在庙里盖了二中。
二中之所以行二,是因它隶属县级管辖,而历史短的一中却隶属专署管辖。专署比县府高级,名头也就占先了。
我上高中那年,不考试,实行平时成绩考量加师生推荐,初中毕业生有一半人可以上高中。其中,一小部分人上一中和二中,其他人,则去“带帽中学”。那种原本只有小学部和初中部的学校,为了解决升高中人数增多的问题,设置了高中班,这样的学校就是“带帽中学”。
班里成绩优秀又被推荐的同学多选择去二中,因为离家近。那时,大部分的居民住在城内。
我选择了一中。
如果二中还是叫凤鸣书院,名好听,可能选择它,我这样想过。
那年,一中招十个班的高中生,六百多人,来自城乡的各个学校。
一中的教室是一排排灰砖瓦房,墙体很厚,三角形的屋顶。排房前有一棵又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浓郁,落下的树荫与灰色的房子融在一起,使环境显得静谧。
一排房子,有三间教室。
与我同来的有七个同学,分到各班,在不同的教室里,不特意找,竟都不见了。
我在高二十二班。
上学的第一天,新同学,我一个也不认识。
教室的门锁着,五十六个学生聚在教室前等待老师的到来。隔着粗粗的树干,男生聚在一侧,女生聚在另一侧。有的女生可能来自一个学校,或是街坊邻居,本来熟悉,一团一伙很兴奋地说笑,打闹,伸开的手指,虚虚地握着的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有点儿落寞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看着她们。男生们打交道容易些,为什么事,不为什么事,相互推推搡搡,不一会儿就围成一大群。有两个落单的,站在人群外,都个头矮小,皮肤细嫩,眉清目秀,猛一看,像女生。他们有点儿像我,也落寞地站着,看着。一个男生被推搡出群,踉跄向女生,他红了脸,有点儿急,返身拼力地想再挤回人群。有几个男生突然大声地叫道:胡萝卜缨子!男生们的目光立刻集中地投向一个女生,多是匆匆地一瞥,就收回了。一个女生对一个女生说:胡美英,叫你呢!胡美英说:胡说八道!谁是胡萝卜缨子?我不由得笑了,想,胡萝卜缨子一定是她的绰号,因名而得。
后来的后来,有个叫戎爱红的女生对我说:哎,知道吗?那天,我本来想和你說话,但没敢说。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穿了一套蓝制服,上衣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看上去挺厉害的样子。
那套蓝制服是父亲的衣服。要上高中了,母亲才发现我的衣服都小了,我穿了,觉得它裹身体,突显着胸部,很难看的样子。母亲要借给我一件衣服临时穿,我不穿,嫌她的衣服瘦。我选择了父亲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没想到它竟使我有了很厉害的样子。
戎爱红是个高大粗壮的女生,小眼睛,嘴唇很厚,说话前下唇总要裹一下上唇,湿润了嘴唇才能说出话来一般。这样,她人显得笨拙而老实。
老师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一男一女,都四十多岁的样子。
男老师高个,很瘦,长条脸,显得噘嘴尖鼻,眼距窄。
女老师长得小巧玲珑,短发,圆脸,深眼窝,大嘴,厚唇,像南方人。
他们一前一后到了教室门前。男老师用一把提前捏在手里的钥匙打开了门锁,推开了门。老师们进了教室,学生们跟着鱼贯而入,先男生,后女生。
老师们走上讲台,站在讲桌后,他们的背后是黑板。
由于没分配座位,学生们自由坐了,坐成男女两个阵营。
高中的课桌与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课桌不一样,不再是双人桌,而是单人桌。
单人桌的桌面由两块木板组成,前面的木板窄,水平地固定,可以稳妥地放文具盒及课本。后面的木板宽,用两个合页连接在前面的木板上,掀开来,露出下面的箱体,可以把书包放在里面。桌面有坡度,写字时胳膊撑在上面很放松。
我个子高,自觉地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上。
男老师先说话了,说话前,他把左手捂在左边的脸上,像似害羞,又像似在遮挡什么。他的这个动作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教室里有了群蜂飞舞似的声音,嗡嗡嗡的不绝于耳。很多人发现,他的左眼竟是假的。那只假眼过于黑白分明了,且不会转动,睁眼闭眼后,漆黑的眸子仍纹丝不动地定在眼中间。
有个男生小声说:他是个独眼龙!
众声附和:哦,独眼龙!
女老师从讲台上拿起黑板擦,当当地敲了敲几下。
教室里又安静了。
男老师说:我姓乔,叫乔云阶,教语文,是你们的班主任。
乔老师从讲台上拿起一根白色的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字很漂亮。
女老师也用粉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李静。
女老师说:我教英语,是你们的副班任,叫李静。
我当了班长。当得很偶然,因为学生们来自各个学校,彼此不了解,没法选举。
乔老师用一只眼威严地巡视了一下学生们,然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乔老师说:你,当班长吧!
我说:我?
乔老师说:对。就是你!是临时班长。
没料到,这班长,我一直当到高中毕业。
真正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好多课程并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
在黑板的一角,有打了格子的课程表,主要有这么几门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美术、体育。没排课的格子空着,是不言而喻的自习课。
开学后不久,学校曾组织全体师生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决裂》。
观影后,有两个情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大家津津乐道。情节一,一个戴眼镜白头发的老师讲课,讲关于马匹的知识。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条马尾巴。他说:接下来,我们讲马尾巴的功能。什么是马尾巴的功能?底下的学生哄堂大笑。情节二,一个脸庞红里透黑的农村青年考试成绩不好,将没资格上大学。一位正气凛然的大叔抓起他一只满是老茧的手,举起来,说:什么是资格?这就是资格!周围的人掌声雷动。
之前,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解她和老师的矛盾。她的信里写道:……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那封信要求学生们背会,所以我始终记忆犹新。
之前,有批林批孔运动。其中的孔,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批判他,我才知道他是“万世师表”。孔子名丘,字仲尼。在古代,兄弟间排序用伯、仲、叔、季,仲代表第二,孔子行二,批判他时称“孔老二”,有贬低意。批判“孔老二”的同时,也批判现在老师们残留的“师道尊严”。
再之前,报纸和广播里宣传过“白卷英雄”张铁生。他被推荐参加上大学的考试,结果理化试卷仅做了三道小题,其余空白,几乎得零分。他在考卷背后写给“尊敬的领导”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此事一出,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编者按: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后来,他被大学录取。
从此,老师们不怎么敢管学生了。
我们的课堂有时很混乱,老师在讲台上自顾自的讲,学生们在座位上做自己想做的事,交头接耳,小动作打闹,睡觉,有的女生用钩针钩线花,我多是偷偷地看藏在桌下新借来的书。
我有个不可遏制的欲望,也成了嗜好,总喜欢把看过的书里有意思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一般情况,自习课没有老师盯班,由我负责维护课堂纪律,主要是管理同学们不要随便出教室,不要大声喧哗。这两点,我们班比别的班做得好。我认为,是因为那时间我在讲故事。女生们围着我坐了,男生们坐在不远处,假装不在意女生这边,实际上他们有不少人在侧耳偷听,我讲到精彩处,他们一动不动。
语文课的学习,除了课本上的内容,乔老师有时会拿几张近期的报纸,说其中的一些文章很重要,那节课就成了读报课。他读读,又叫几个学生接着读读,一张张报纸传来传去。他读的时候,有的段落会放慢读速,反复着一句句话,要求学生们做笔记。不过,除了上课,乔老师比别的老师操心,不定什么时间到班里来,查点一下学生,或调解男生打架女生吵架之类的事情,课间操时跟在队伍后面去操场,站在一旁,看学生们做操。
乔老师与学生们相处最多的时间是在一个春天。
有个离城三十多里的山村叫李家沟,开春没多久,乔老师就带我们班的学生去那里开荒。
去李家沟是步行,每个人都扛着一卷行李拎着一网兜吃饭洗漱的用具。出发前,有人的行李卷被他人嘲笑,或是没捆好,松松垮垮,像一堆泥;或是太小,怀疑没有被子,或没有褥子。所有的网兜都叮当作响,是搪瓷脸盆碰撞着别的东西。但无论怎样,扛了拿了它们,几里路后,它们就是累赘和负担,使沿着公路边行走的队伍溃不成军。有柔弱的女生,先是把网兜让体壮的女生帮着拿了,自己只顾行李卷,一会儿扛,一会儿抱,尽力向前。松垮了的行李卷抱在胸前更不好走路,挡了视线,头从一侧歪出来,看一段路,走一段路。这样,队伍拉得很长,队尾看不到队头。后来,乔老师挑了几个高大的男生,在队伍的前面拦住他们,命令他们往回返,去帮助落在后面的女生扛行李卷。我发现,尽管男生女生不说话,但在帮助女生时,都没有违抗命令。他们扛着拎着两个行李,大步流星。那行李所属的女生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班里一直传说安建平和陈晓萍好,恰恰他帮她扛了行李卷,他们走在一起,女生们就窃窃地笑,有男生打口哨。乔老师把一只手捂在脸上,大声说:你们在想什么!
我一直不明白在李家沟开荒属于什么课。
开荒是很苦的活,主要是早春时的土地还没完全解冻。女生用铁锨,一锨挖下去,只在地表留一个浅浅的痕迹。男生用镢头,抡起镢头一下一下刨,很多下,地表的冻土才被破坏了,露出下面软质的土。于是,劳动程序成为:男生先刨,女生后挖。这样,女生比男生闲,得等待。于是,去了地里,女生們就扎堆聊天。当然,聊不了一会儿,有人就打断了无聊的话题,鼓动我讲故事,也就是讲那些从书里看来的故事。我就讲。在沟坡上,即使是微风,它也无孔不入,像一条条冰凉的小蛇,从领口,袖口,裤腿儿下面乱蹿进来,贴着身体游走,凉丝丝。
这样几天后,很多人的手皴了。刘云的手皴得最厉害,从手背到手腕,竖着,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裂开的小口子,像一种什么小动物张着的嘴。刘云没有雪花膏,也没有凡士林油,冷水洗脸,什么也不抹,脸皴了,没裂口子,手皴了,却裂了很多口子。她干活时,手一拿铁锨,就咧一咧嘴,手疼的缘故。我借给她凡士林油,她抹了,又用手绢包了,好多天,那些小口子才有了痂。
我们住在村里的农民家,睡土炕。本来一铺土炕睡六个人,但后来,我睡的土炕上睡了十个人,有四个人是擅自从其它炕上过来的,大家挤在一起,就为了在熄灯后的黑暗里听我讲故事。
乔老师一早一晚会走几条村街,到几个院子里。早上进了院,他就吹响一个挂着脖子上的铁哨,很尖锐的嘘嘘声,是在叫睡在院里某间屋里的学生们起床。晚上进了院,他不再吹哨,进男生住的屋子,查点人数。他不进女生们住的屋子,而是站在窗外,听屋里的人报数。
乔老师说:怎么六个人变成十个人了?
有人说:人多了,挤着睡,暖和。
尽管数学老师张裕德教学口碑很好,但大部分学生不喜欢上数学课,尤其是女生,我属其中之一。张老师按课本讲到了函数,之后,抛开了课本,开始讲一个叫华罗庚的数学家发明的“优选法”。张老师说,优选法以数学原理为指导,是尽快找到生产和科研的最优方案的方法。在实践中,它能减少实验次数,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选取最合适的配方配比,寻找最好的操作和工艺条件,确定最好的设计参数……等等。围绕着这些,每一节课,他都举例说明,再强调优选法公式里的一个数字:0.618。
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虽是高中毕业生,但数学水平只达到初中阶段。为此,在后来参加高考时,面对试卷上的考题,觉得它们都很陌生。
有一段往事,1977年恢复高考是很突然的事,得到消息,距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要考数学,我心里没一点儿底,就去一个不收费的辅导班去听课。一日,当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对数题,竟叫我站起来,把题念一下。我看着那题,不认识,很懵,就说:老师,是先念前面,还是先念后面?是先念数字,还是先念字母?是先念下面,还是先念上面?老师说:你什么毕业?我说:我高中毕业。
李老师的英语课更不被学生们重视,因为大家实在想不出那种语言对自己有什么用。
我初一后半学期才从农村转学回城,村里的学校不开英语课,落了课,字母都认不全,半路和同学们一起学,有点儿跟不上。初中的英语老师姓董,女的,身材苗条,大眼睛,很温和的人。她曾叫我去办公室补课,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办公室在一间大殿里,过去的庙堂,十几个老师远远近近地坐在桌子旁。我诚惶诚恐地垂手站立在董老师的身边。她坐着。她拿着课本,我也拿着课本,从字母开始,她念一个,我念一个。那一刻,我觉得有不少老师在看我,像看一个怪物。我被看得心慌意乱,完全在机械性的学习,鹦鹉学舌。这样几次,董老师讲了音标,她说:学会音标,就会说英语了。然后,我再没去办公室找董老师补英语。好在期末考试是朗读课文,自己挑选一篇。我挑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那篇课文,我让英语课代表常萍反复地念了几遍,我默记。考试时,讲台上,董老师坐在一个凳子上,一个接一个叫学生到跟前,朗读一遍自己选的课文。我拿着书,打开来,一副照本宣科的样子朗读了。其实,我是在背诵。初中毕业,我的英语成绩:96分。
李老师的英语很流利,一站到讲台上,就满嘴是英语,伊利哇啦。观察同学们的表情,他们都很木然的样子,我明白,我的英语不好,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我觉得,李老师上课时一定很崩溃。好多次了,她念一句英语课文,后面跟一句:阿干!同学们就鹦鹉学舌,念一句那课文,后面也跟一句:阿干!这让李老师很生气,不说英语了,说中国话。她说:阿干,是我说,而不是你们说。它的意思是再一次,就是让你们跟我读一遍!明白了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明白了。其实,好多人没明白,再读英语,一切照旧。后来,李老师上课就不操心了,自顾地自讲。
有人说,李老师不适合给中学生讲课,她原本是大学老师。不过,她在大学教俄语,在一中教英语。
本地原本有个大学,办着办着,突然就不办了,撤销了,很多老师就地调动工作,大部分在一中任教。比如乔老师、张老师、胡老师、陈老师、罗老师……
李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她结过婚,离婚了,四十多岁,与几个年轻老师一样,住在单身宿舍里。
有时,为班里的事,李老师会联系我。
我也就多次去过李老师的宿舍。
李老师的宿舍是单间房,十来个平方米,一门一窗。墨绿色的平绒窗帘总拉着,白天屋里亮着灯,仍光线昏暗。屋中间拉着一道素色的花布帘子,帘里有一张单人床,帘外有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个很大的收音机,它的音量总是很低,里面有外国人在唱歌,我听不懂。
李老师说:你别对别人说我在听外台广播啊!
我说:好。
在李老师的宿舍,我借到一本《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上册。通过文字,有几部电影印象深刻,它们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桃李劫》。那些剧本写得真好,画面感很强,都没看过的电影,却仿佛都看过了。
美术老师欧阳一禾本是教历史的教师,历史课没开,他就教美术。为了实用,他主要教各种美术字。美术字很神奇,普普通通的字,经过加工,美化,装饰,那字就变得整齐,醒目,美观。用它写标语、黑板报、墙报,效果很好。欧阳老师教完各种美术字后,不再来上课了,课程表上虽然还有美术课。
有传闻,欧阳老师与李老师关系暧昧,但他有老婆,有孩子。
我的美术字学习得很好,开始负责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
化学老师姓秦,是年龄最大的老师,不苟言笑,穿一套深灰色的制服,领子上的风纪扣总是扣着,几乎全白的头发短而硬地密集在头上。他的课,多数去校园的一个果园里上,去操场后面的一大块田野里上。果园里种植着各种果樹,田野里种着小麦。去这两个地方上课,学生们会提前得到通知,带了铁锨,带了箩筐,带了剪刀,带了牙刷……铁锨用于挖地翻粪,箩筐用于采摘,剪刀用于剪枝,牙刷用于授粉……秦老师表情严肃地讲解着生土和熟土的区别,讲解着优质肥料该怎样沤制,讲解植物生长的不同时期需施多少肥,植物为什么需要授粉才能繁殖。
果树修剪时秦老师最忙,在偌大的果园里来来回回,从这棵树到那棵树,不断地对手里拿着剪刀准备对果树的进行剪枝的学生强调注意事项,生怕他们胡乱剪。剪刀并不是用来剪树枝的工具,能凑付剪细小点儿的枝条,粗壮的,只有靠秦老师剪了。他拿着一把专门剪树枝的剪子,像大鸟的嘴,弯钩状,嘴一合,树枝就剪下来了。
秦老师说:小树的修剪很重要。它应该以主干为中心,确定枝条的去留,修剪恰当,一棵树才能长势良好。树还幼小,面对恣意生长的枝条,要进行控制,这就需要剪枝。不剪,看上去枝繁叶茂,但影响通风采光,徒有其表,结果情况并不好。但是,小树的剪枝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它还没定型,要考虑它未来的发展,所以,能不剪的尽量不剪,要逐步剪。剪得太狠,多伤口,不利于它的恢复。
秦老师在讲果树,我听着,却觉得在讲人。
果园里有个很大的粪坑,平时各班打扫卫生的垃圾,厕所里掏出来的粪便,周末组织学生到街上义务劳动捡拾的骡马粪,统统都倒在里面,日积月累,逐渐满了起来。过一段日子,有的课,学生们就是用铁掀翻腾那粪,把下面的翻到上面,把上面的翻到下面。翻起来的粪有股酸臭味。
麦田有上百亩。初夏时,秦老师带着学生们在地里分散来开,人人一手拿着一张展开的纸,一手拿着牙刷,凑近一个个正在扬花的麦穗,用牙刷把穗头上的花粉刷下来,落在纸上,端着,从麦田的这头,走到麦田的那头,距离尽量远,把花粉交换地撒在穗头上。
秦老师说:我们所做的劳动,都有化学原理。
化学元素周期表有: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不太明白与果园和麦田有什么关系。
物理课最好上,因为基本不讲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实践性的学习和掌握“三机一泵”的工作原理和作用。“三机一泵”指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
课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高中毕业后,很多学生将会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当知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在那篇作文里,我很诚实地写了自己的两个理想:当兵和上大学。它当范文在课堂上念了,却遭到很多同学的嘲讽,认为我的理想都不会实现,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一点,已注定了我的理想是胡思乱想。
拖拉机并不常见,带拖挂的拖拉机常常载着灰色和橘红色的砖进城,运到建筑工地,卸了砖,就轰轰隆隆地开走了。唯一的电影院和前进剧院里各有一台柴油机,演出停电时发电救急。水泵更陌生,完全属于农业机械,有离心泵、轴流泵、混流泵、拉杆泵等。
真正学习起来,确定只学习电动机,一个班一个班轮流着学。
物理老师王国栋带领学生,去郊外的一个电机厂实习,为期一个月。
那个月,我很兴奋,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工人,跟着工人师傅三班倒。早上5点到中午1点是早班,中午1点到晚上9点是二班,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是夜班。
我喜欢上二班,因为可以骑车,可以带饭。饭是母亲特意做的,有饭有菜,装在铝质饭盒里,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在不平的路上,嗒嗒响。父亲在我上二班时会步行去上班,把自行车让给我,因为下班时已是晚上,骑了车,可以飞快地经过一段路边有坟墓的路。
电机厂有有七个车间:翻砂车间、机加车间、组装车间、测试车间、包装车间、库存车间和进料仓库。
翻砂车间主要铸造电动机的外壳。车间里到处黑乎乎的,地上堆着黑色的砂土和砂箱。有个烧焦炭融化铁水的小高炉。铁水倒入砂箱里黑砂土凹出模型内,冷却后,剥离砂土,铸件就做好了。这个车间的活儿又脏又累,都是男工人,他们的脸上时常抹着黑。
机加车间有意思,有车床、铣床、磨床和锻压机。机器开动,机声轰鸣,穿着有油污的蓝色帆布工作服的工人师傅在机器旁操作,举手投足间,一个个精致的零部件就加工出来了。但操作机器有危险,据说有个梳长辫的女车工干活时不小心,掖在帽子里的辫子掉出来,缠到飞转的钻头上,卷进车床,为保命,她拼力掀掉一大块头皮,头才挣脱出来。还有一个工人的右手被锻压机轧掉了大拇指和食指。
我去了组装车间,大部分女生去了其它车间。
我的活儿,是给师傅们打下手,用手动绕线机绕出一匝匝电动机下线用的缠漆包线,用刀片裁出一张张小纸条样的绝缘纸,给定子和转子上下好的漆包线圈刷绝缘漆,给电机外壳刷防锈漆……
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一天,校门口拉了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别着黄纸剪的大字“欢迎工人阶级上讲台”。
于是,一个叫洛宜的纺織厂女工被抽调到一中当政治课老师。
没见到洛老师之前,我对她没有一点儿想象,以为就是一个穿了蓝色帆布工作服站在讲台上念报纸的人。
洛老师出现得很安静,悄然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把拿在手里的一张报纸放在讲桌上,朝学生们微微一笑,没介绍自己,就开始讲课了。
洛老师二十五六岁,皮肤白皙,高额头,大眼睛,牙齿整齐雪白,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她没穿蓝色帆布工作服,穿浅绿色小翻领的确良衬衣,卡其色直筒涤卡裤子,齐耳的短发偏分梳着。她的声音很好听,标准的普通话,音色悦耳,娓娓道来。她与小城人很不一样。
洛老师是北京知青,在农村插队几年后去纺织厂当了工人。
洛老师每次上课都拿着一张报纸来,把它放在讲桌上,从不再动。我以为,她讲课前一定是熟读了那张报纸,所以才能滔滔不绝。我曾偷偷地翻看过那报纸,发现上面并没有她讲的内容。
那报纸,随着她一路走来,不过是她做为老师的标志物。
整整一个学期,洛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关于美国,关于苏联,关于日本,关于中国的事情。除了中国,我不知道那些国家在哪儿。洛老师在讲它们时总是这样起兴:这个美国,这个苏联,这个日本。她讲了很多它们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不是像我一样在认真听。我听了,有感触,觉得自己原本在一个幽暗狭窄的小黑屋里,突然有一扇窗打开了,又有一扇窗打开了……透过一扇扇窗,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它有很多令我新奇的东西。那陌生的世界在洛老师的讲述中,我逐渐熟悉起来,以为有一天会更了解它们。
在洛老师的课堂,我没看过闲书。
我觉得,洛老师就是一本书,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书。
所有的自习课上,我都在讲故事。
冬天,教室外北风呼啸,寒冷刺骨。
在一节自习课,我又一如既往地给女生们讲故事。
教室里有两个火炉,一前一后。我们女生围着前面的坐了,男生们围着后面的坐了。不知为什么,后面的炉子总没生着,男生们不断地往里扔各种可燃的东西,它们着了,又灭了,冒一股股的烟,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
教室窗户上的玻璃从来不完整,打碎了,没镶上,就用纸壳子钉了。玻璃是不敢隨便破坏的公物。窗外有其它班的男生路过,不定是谁,会朝纸壳子打一拳,或丢半块砖。“嘭”地一声,纸壳子烂了,窗户上又有了洞。冷风便从洞里趁虚而入,对面的窗若也有破洞,它裹了一些烟,从那里出去。有几个男生扑到破洞前,探头探脑,想看清是谁使的坏。窗外早已没人了。他们缩了回来,彼此笑笑。那一刻我明白,他们也对其它班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正讲得兴致勃勃,乔老师突然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沓像传单样的纸。
同学们不再扎堆,散开来,慌忙回到自己的座位,有人还搬着凳子。
乔老师站在讲台上,用力地把那一沓纸拍在桌面上,拍得腾起一片粉尘。他的一只好眼转动着扫视了一遍学生,最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乔老师说:讲!讲!讲!有什么好讲的?
然后,乔老师宣布了一件事:公安局来人了,在校革委办公室里等着。他们要清查看过反动和黄色书籍的学生。这沓纸上,有被查书籍的目录,每人一张,对照着,检举揭发谁看过什么书,把详细内容写在目录背面。
各小组组长领了目录,分发给自己的组员,人人面前摆了一张。
教室里极安静。
同学们面对着目录单,表情严肃地做思索状,之后,有人开始伏案写字了。
我察觉到,好不少同学在回避我的目光,有的更是侧了脸,一只手写字,一只手捂了写的字,怕我看到,怕别人看到。我意识到,他们检举揭发的人一定是我。
我看了目录,大部分书看过,而且给同学们讲过。那一刻,我觉得很多书名很刺眼,如《梅花档案》、《绿色尸体》、《一个少女的心》……
我想了想,除了我,再想不起还有哪个同学看过那些书。她们不看书。如此,我要检举揭发的人,只能是自己了。
想到等待在革委会的警察,我不禁觉得事情有点儿可怕,也许将发生可怕的事。
我见过对学生的处理。
前一段时间,另一个班的一个男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在做课间操的时候,突然被两个警察在操场上摁倒在地,用手铐拷了,揪着带离了操场。
更可怕的是一次公审大会,枪毙的人中有个年轻人,叫王大伟,是我初中同学王红伟的哥哥。王大伟打死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不满十八岁,半年后,年龄够了,五花大绑地押在公审大会的主席台上。他剃了光头,发青的发茬儿衬着一张刷白的脸,穿了一套新的黑色的棉袄棉裤,里子是白色的,领口袖口露着白布。棉衣虽然很厚,裹了他,像个套子。当宣布他是死刑立即执行,站在他身后的人把一个写有他名字的长木板插进他脖子后的绳子里时,他向下委着身体,放声大哭,说:叔叔阿姨,我不敢了!但他的哀求什么用也没有。他被架着,拖下台子,拽上一辆卡车,一边一个警察扶持着,站在车前。他的头刚刚高出驾驶室。载了他的卡车开走了,一路尘土飞扬,不见了。
我拿着笔,看着书籍目录,斟酌了好一阵儿,才在纸的背面写下:我看过《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家》、《野火春风斗古城》。
我知道,我在避重就轻。
乔老师收集了全班学生写的检举揭发信,拿走了。
没有老师,也没有维护课堂纪律的人,同学们都一反常态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很多男生装睡,趴在桌子上。有好几个女生低了头,在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手,有的指甲然红了,用夏天的指甲花,这时它的颜色淡了许多。
教室里极安静。
不知谁压抑不住地小声咳嗽了一下,声音显得很大。
一个窗户上的纸壳子突然被人在外面捶了一下,嗵地一声。我听到有人在窗外叫了我的名字,又喊了一句话。
他说:乔老师让你去趟办公室!
全班同学都看我,趴着的,也抬头看我。
我出了教室。
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宿舍。他和高二十六班的班主任赵老师住在一起。
我进了屋,乔老师站在火炉旁,手里拿着一个炉钩子。赵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背着身,在看一张报纸。
在乔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刚才他收集起来的全班人写的那一叠检举揭发信。
乔老师的表情很凝重,脸显得更窄了,那只假眼一动不动。他用炉钩子不断地勾起放下炉圈中间的小炉盖,好像总觉得没放好,不严密,担心有煤烟冒出来。看到我,他用炉钩子使劲敲了一下炉盖,又用它指了指那叠检举揭发信。
乔老师说:你自己看看吧!
我拿起那叠纸,开始看。一张一张地看。
看着看着,我越来越紧张,感觉头发在起伏,额头上有了汗,手心有了汗。那叠检举揭发信上,每一张都赫然地写着我的名字,写着我看过的书,书名列在传单的目录里。有的写得更详细,写了年月日,哪节课,我讲了哪本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字我熟悉,写字人是我认为的好朋友。有的字陌生,字体也粗旷潦草一些,像男生们写的字,他们检举揭发的人竟然也都是我,他们坐在不远处,听到了我讲的故事。我没想到,在这一叠纸上,算上我,全班同学竟攻守同盟的一致,矛头都指向我。
我想到还等在革委会办公室的警察,就不仅是紧张了,开始害怕了。
我看完了所有的检举揭发信,拿着它们,呆呆地站着。
乔老师把检举揭发信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乔老师说:看完了?
我说:看完了。
我的声音很低。
乔老师说:讲!再去讲!还有什么故事没讲?还想让人家知道是谁在讲故事吗?
我说:不讲了。
乔老师突然把手里的检举揭发信撕了,撕烂了,又揉成一团。他用炉钩子挑开那个小炉盖,随手把纸团仍进了炉膛。炉火遇纸,先是焖出一股烟,接着窜起火苗,烧着了纸。炉盖又盖上了,看不到那些纸。
乔老师说:回班里吧!什么也别说。
我说:我再也不会讲故事了。
赵老师自始至终背着身看报纸,没回头,没说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走在校园里,有风吹,有一些干枯的槐树叶在我的眼前飘然落下。
我抬头看,才发现,即使在冬季,有的树叶还在枝头。
创作谈
关于散文,我的概念很模糊,也没多思。于是,从读到写,自己像一个走夜路又没秉烛的人,匆匆又匆匆,时而脚下踏实,时而脚下悬空。
前段时间,看了女儿的一篇文章《当我读散文的时候,我在读什么?》。她的文中写道: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文章,杂文亦包括其中,相比于‘形散神不散、‘语言优美之类的特征,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个分类特点是‘不很长的小文章。……于生命和语言的无数细小琐碎之处,窥见有趣的灵魂。这段话,让我茅塞顿开。
再写散文,我会下意识地努力。
每个人对世间万物的感觉是独特的,由此,也应写出不一样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