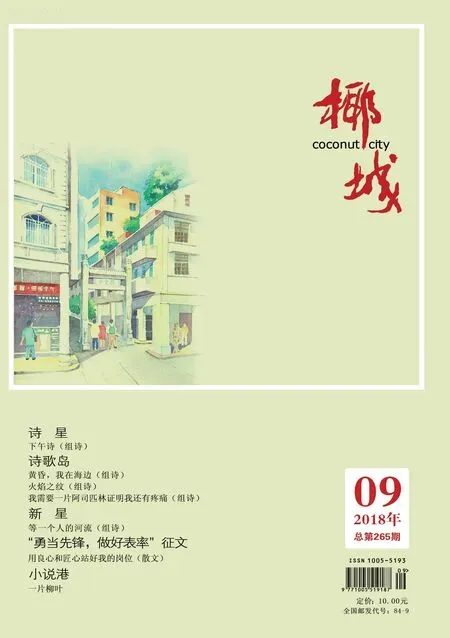读阿翔近作
阿 西
阿翔经过较为漫长的探索,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使其能够进入自觉性的诗歌写作。我们知道,但凡有一点抱负的诗人都想找到自己的语言系统,并认为这是进入有效性写作的基本前提,然而,尽管很多人都信誓旦旦,真正进入到这种写作状态的诗人却少之又少。如果用一个数字来表示的话,恐怕不会超过5%,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写作者,不过是一种对固有文本的重复性写作而已。阿翔经过相当长的探索,发现了那个真正属于诗的“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就是直接地专注于生活本身,直接进行此在的诗性转化,无论对象是否具有诗意,无论场景是否适合诗的要求,他都会主动地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发出声音,写出一首关于本地现实的诗。也就是说,阿翔摒弃了那种高蹈式的写作,也摒弃了那种梦幻式和所谓的主体性写作,而是仅仅坚持对生活的客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上世纪末伪经典范式写作具有矫正意义。
下午通过灰白的蒙蒙细雨,逐渐成为
汽车的一片喇叭声…………
………………我听到的是,炉火
弱爆的声音。在下午的河岸,看上去
流量不大,无关任何现实,唯一获得是方言
的慰藉。经常如此,所以山水开阔
——《下午诗》
我摘录出的这段诗,很好地诠释了阿翔的写作趣味,那就是他只关注于“下午”这个词,并在这个词中找到“慰藉”与“宽阔”。我们知道,许多人其实都在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幻觉充斥在各种意识活动之中,而所谓的诗人几乎很难获得一次“超然”的精神定位,他们只好去写一种虚假的诗——无论是出于官腔的正义还是出于个人情怀。而阿翔仅仅抓住“下午”这个此在的现实,就足够完成一次有效的写作。这也说明了他终于解决了所谓的当代性问题。当然,对于阿翔来说,此在的诗性实际上就是他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对于消逝的抵御和消解。他的近作,总是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混乱,似乎完全有意为之。我们知道,阿翔早些年的诗歌有一定的歌谣特征,后来又有了些许的“思辨”趣味,直到近年,他开始直接与现实对话,真实录入现实的状态。“树林上空的是火焰,手臂上枕着,没有什么/比诗歌微小而微小的柔弱更有力。生气的人戴着马脸/坏人装着狗肺/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拟诗记,诗歌史》)这里表面上围绕着诗人一词而发的感慨或揶揄,但语态极其接近俗语,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观点,只是以“无力”、“马脸”和“坏人”代指,勾画出非经典时代的存在脸谱。这个脸谱,即是与某些诗人相关,更与社会情态相似,一切都有一种非主流的形式感,这是当下的一种无序性特征的表露。
新时期的诗歌观念已经发生了本质化的变革,诗再也不是那种神谕之词,而是返回到物的基本面,与现实几乎平行一致。在这个前提下,诗歌才会真实,才会拥有发言权,与我们期待的深度相对应。在我们对一个诗人进行考察时,就要看这个诗人是否与时代处于同步状态,是否直逼现实,这些是衡量虚伪与真实的重要尺度。阿翔积极回应现实,因而取得了某种“虫蚁”些许的“伟大”,这就是一个诗人卑微中的伟大。阿翔,一直都在某种颠沛状态下生存,虽然已到中年却仍难以摆脱“小剧场”中小人物的卑微感。
阿翔的许多近作都呈现出一种随意性,似乎他一直处于“拟诗”状态,而不是写诗状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确认自己在写诗,而是在模拟诗,其实他就是将生活本身看成是诗本身,写作无非只是一次模拟而已。比如他的《迟疑》,“日子没有动过一下,看着窗外发呆,他喘气的声音/接近于危险,想一想:他仿佛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只是变换了小角度,他写诗,继续/占据空气”,就是写友人的某种基本面,并不刻意去深入灵魂,而这恰恰是最好的深入。在《10月2日,肥美语》、《从“情书”开始反对诗》和《给Y,感冒危机》等诗歌中,阿翔还流露出了许多的无奈和破败感,好像自己一直“在旅馆过着另一种生活”,“掩饰彼此虚构的身份”。这种游移不定的表述,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碎片化生活的基本写照吗。另外,这是一个“好人比坏人更为复杂”的年代,阿翔却依旧要“对着国家滔滔不绝”,他是多元的文本本身。
一个优秀诗人,不仅仅写出自己的时代,还要建立属于诗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诗人的人格化与语言场域的相互交融,体现出一个诗人卓越的内在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上看阿翔的写作,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自觉地从流逝中建立回归的秩序,透过混乱与驳杂,去厘清语言的基本要义,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而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则往往缺乏这种自觉。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诗人止步于情绪的发泄,无法实现秩序的重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诗歌的造神运动,大师化的诗人比比皆是,但非常明显这些大师们需要打上引号,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值得信赖,究其原因这些文本更重视外在秩序——形式上的徒有其表和姿态的模拟。当然,阿翔的这种建构,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完善的建构,但他基于生活本体性的建构,是接地气的努力。
其实我畏惧藏匿的使命,我的出生地
使我不停地颠簸,……,……
那是我的出生地,被摧毁了,挟裹着一切泥沙
我还能奢望什么,在我回去的时候
很难自圆其说,很难给我清白。——《拟诗记,出生传》
我们知道,诗人的出生地已经面目皆非,往日的一切都已经流逝,但这种流逝并不能阻止诗人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更多的只是精神和语言的回归——让自己重新进入某种序列中,并按照既有的轨道运行虽然并不是诗人的真正愿望,但确是诗的一种归途,是对于混乱场域的一种抵抗和纠正,而这“很难自圆其说”。在题为《异乡人》这首诗中,阿翔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最难捱过的是漫长的夜晚,我客居在这里,不陷落于/胖子的体重和忧愁,远处,我的黑帽子不见了,没有人察觉/需要存疑。同样,我看到/你的诡辨术和隐遁术……”阿翔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隐在的神秘之乡,他需要语言抵达它,并且在那里实现精神的人格化。这既是对混乱的抵抗,也是对秩序的呼应,体现出对诗歌更高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