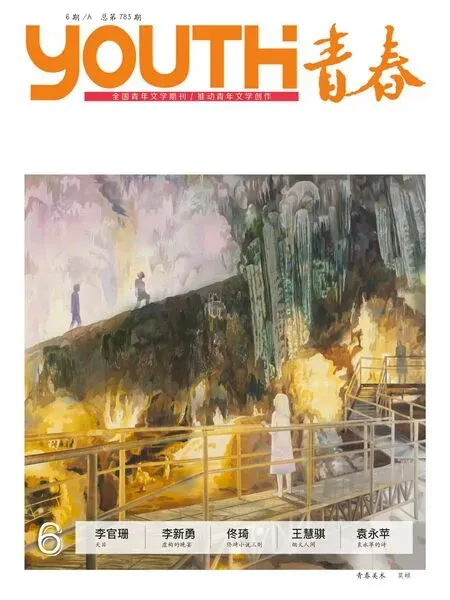狗 冢
口
第八个月已经过去二十一天,老皮依照惯例在晚饭后出去坐一会儿。老皮养成这个习惯才用了不到六天,他是如此享受腹中的食糜和落日一起消融的感觉,以至于不愿再回想六天之前的半生他都是如何消磨的。
哦,这个想法倒提示了他:建平走前,他习惯于坐在客厅沙发上听他洗碗,有时厨房太嘈杂压过电视新闻的播报,他便甩出打包好的话去难为他。而如今,这些记忆已经过分渺茫了,一只碗一双筷,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得很响,他便发明般地把餐具留到次日早晨再洗:晨间光阴短且人混沌,声响大小就于心情无碍了。而那些其余的晚饭后和日落前呢?他实在记不得了。
老皮的院子没有围墙,这在如今实在少见,这独居老头和他裸露的院子在邻里街坊或强盗小偷眼里倒也早已见怪不怪了。而就在近几个月,老皮突然萌生了砌围墙(或至少拉一道栅栏)的念头,他也说不清这道计划中的围墙是为了保卫些什么,哼,就像他还有什么值得宝贝的东西似的。老皮陷在院前草丛上的沙发里,再次为自己的荒唐感到哭笑不得。
虽然沙发的皮面已经风化斑驳,但看得出来原先还是很气派的。有一天,老皮使了老劲把这组沙发拖到了院子里,可是,本就荒芜的客厅立刻就显得过分空旷了。终于,老皮受不住,使了老劲又把沙发塞回了客厅。然而他顿时又嫌客厅里满眼的沙发涨得目眦尽裂,便决定永远将沙发拖到院子里。第二天清晨,老皮打起精神拖沙发。回头看看刮花了的地板和压塌了的月季丛,老皮长舒了一口气。
月季是建平不知从哪里移过来的,自打那次被沙发压过,这丛月季就贴着地长开了。月季每月都开花,就像女的每月都有月经,男的也配套着每月发情。老皮回头检视那丛月季,天渐暗,他看得不是十分清楚。路灯还没亮,太阳却已经没了踪影,半熟的黑夜就趁机跋扈一会儿。
“大伯,你家的狗呢?”
(伯,读作“掰”,切勿读作“勃”。读“勃”太酸软,两不情愿。)
这声音老皮不认识,但触耳坚脆又沙质,像咬了一口涩梨,便觉得应该哪里见识过。“小伙子,你多大?”老皮脱口问道,也不顾是谁先发的问。
“呵,我……二十啊,咋了?大伯认识我?”
“小子,最多十八吧!”老皮并没有当面拆穿或给他难堪的意思,老皮永远不会这样对他,只是觉得自己一般不会错。
“虚岁二十,虚岁二十。呵,大伯怎么知道的?”
“你又怎么知道我养过狗?”老皮没有回答他,却又追问。
“这儿有个桩子,而且周围的草全秃了。”
老皮向旧狗窝方向望去,两眼一抹黑,再下决心一看,又只有花灰的视网膜的噪点。老皮没有夜盲症,老皮只是老了。
“呵!是个有心的好小伙子。那你怎么没看见木桩边上的土堆?”老皮在黑暗里得意地笑笑,像受表彰的小学生。但即时又收敛了,他敬畏男孩的夜视力。
“呵!真可惜了。它怎么了?”
“我勒死的。它是建平养的,不是我的,可是建平走了。”
“建萍是您太太?”
“呵……建平,是……我的儿子。”
老皮焦急地等待路灯,西天稀薄的落霞像极光似地狂欢却本性冰冷,“他和你一样,今年也十八了。”
“大伯怎么会这么肯定我今年十八哩?”
老皮没有回答。男孩知趣,以为老皮不爱理他,就别过头蹲在地上点烟。老皮看到某处打火机的跃动,暗中随即闪出一枚亮亮的鼻尖。那鼻尖不知道老皮不是不爱理他,而是太久的独处让大脑结了痂。老皮只是心里央求男孩不要走,嘴上却不说一句话。缓缓地,东北地渐渐有广场舞的声音传过来。男孩起初有些迟钝,不过终于也捕捉到了,暗中的一点烟火就随着音乐的律动游移开来。老皮把瞳孔开到最大,眼球随着那某处的红点左右移动。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专注过了。
“大伯,你会跳广场舞吗?我一直想学呢!最好是那种双人的。”
老皮被这没来由的提问惊得心一悸,他定了定神,夜幕已四合,四邻已上了灯,东天也只一划澄清的新月。他想起身,脊柱却弯陷在沙发里定了型,酸热一阵也直不起,上半身就悬佝在半空中,像一具正在重启的机器人。虽然眼前依旧混沌,但手臂潦草一捞,便是男孩湿热的棉质T恤、挂在中间的瀑布般的腰和悬崖样的背。他知道男孩能看到他。
老皮当然不会跳广场舞。他扭了几下就绷不住笑了,男孩也是。
“学会了吗?”
“呵!学会了!”
西街路灯亮了,一个追着一个,从西头杀到东头。
“小子,你叫什么?”
“我叫吴明。”
吴明。
老皮燥得睡不着,掀开被子,让夜凉流灌进来,像被舔掉胞衣的幼兽一样打了个激灵,神爽气清。侧头望钟,正是四点零八分。他坐起来,两脚在地上胡划乱拨地找拖鞋。倏地,其中一只被踢得没影,塑料的鞋底在屋子的空旷里划出一记耳光。老皮干脆赤脚,他下床走到窗前,院子里路灯下,一对恋人拥抱着轻轻摇晃。老皮闭上眼睛,下决心听,却没有捕捉到合拍的乐声,只有杳杳的白噪音。老皮没有耳聋,老皮只是老了。
再睁开眼,那对恋人轻轻地,胶着接吻。
老皮突然意识到,距离建平离开家,已经八个月零二十二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