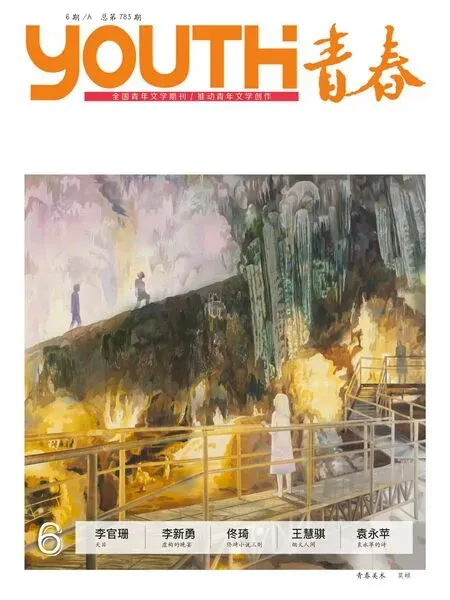所谓爱情
口 叶凉初
时间有点早,大堂里空落落的,只有服务员在小步快跑,做着晚餐前的准备。餐厅很大,一面临湖,夕阳下的湖水波光粼粼,像一幅绝美的布景。桌面辅着洁白的台布,整齐的餐具,桌椅的距离分毫不差,仿佛在等待一场战争。
实物点菜,就在大门口,多种菜蔬和海鲜。有一种巨型的塘鲤鱼,用呆萌的眼神看着她,她也看着它们。男人停下脚步,问,想吃?她忙说不。男人便说,吃点虾吧,这个季节的虾好。她点点头。男人又说,吃点肉吧,难得吃点不要紧,她又点点头,如此,很快点好了菜。
服务员过来倒了茶水,男人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她下意识地看看四周有无禁烟标志。
她记得,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十二月,而现在,已是另一年的春天。重逢的喜悦,令她几乎贪婪地看着他,抽烟的样子,咳嗽的样子,抬头与她相视一笑的样子,把装虾的碗碟轻轻推到她面前的样子。她突然垂下头来,久久凝视着桌面上的茶杯,不能抬头,她怕他看到眼中的泪水。
别这样,好好吃点东西。他仿佛洞悉一切,绕过桌子,坐到她身边,轻轻握住了她的手。她听话地抬起头来,泪花闪烁在睫毛上,勉强笑了笑,说,我是高兴的,太久没有见你了。
三年前,他们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上相识,彼时,她刚离婚,惶惑如一条丧家之犬,被好友拉出来换换空气。她们怕她就此死去或者腐朽,骤然失去了家庭的中年女人,像一株失去土壤和空气的植物,无所依附,很危险。可是她知道自己不会,她是那种看似柔弱,内心无比坚韧的女子,安静,低调,深情。只是这世间,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承担她的深情。
不是不像电影镜头的,她躲到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男人在阳台上抽烟,她返身要走,男人立马掐灭了烟头,连声说对不起。她在暗淡的灯光下笑了一笑,在角落里坐下来,习惯性地抱着自己的双肩。
你冷么?男人问。
她说不。学过心理学皮毛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自卫的姿势,也是一个别来惹我的提示。男人没有再说话。夜风已凉,浩浩荡荡,吹得香樟树大幅度地摆动枝条,叶子唦唦响过。
春天的晚上,总是不期然地有这样的大风。“年轻时去外地上大学,父亲关照,春天的晚上出门要多带件衣服。”男人双臂伏在阳台上,看着院子里高耸的香樟树,自言自语地说。
香樟,是这座城市的市树,常绿,却在春天里换新叶,黑色的果子掉落在地上,轻轻一踩,吱的一声,溃烂成浆;如果落在车子顶上,那肮脏的黑色很难去除,像一种无法回避的过往。
那你听你父亲的关照了么?她在角落里,闲闲地接了一句。
没有,当然。
两个人在黑暗里无声地笑起来,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她已不年轻,结婚早,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岁月不可避免地在她脸上落下了风霜,眉梢眼角,细碎的皱纹,提醒逝去的时光,但还好,在相宜的灯光下,她还是颇可以一看的,比如此刻,客厅里泄漏出来的光线,正是下午两点十分的角度,落在她脸上,平添了一层光彩,像有一只神奇的手,一下子抹去了岁月的馈赠。
喝点什么,我去拿。他对她说。
咖啡或者酒。他点点头,她这才看清,眼前的男人也上了年岁,但欣长的身材没有发福,两鬓轻霜点缀了他的儒雅,步履轻快地走向人群熙攘的客厅,像一条鱼游向了大海深处,她甚至不确定会再次见到他。
可是,他很快折回来,端着两杯咖啡。她心里不知怎的,有了一丝感动,为咖啡,或者为他那么快回来。
就这样相识,加了微信,QQ,常常聊天,很奇怪,她对他说的话,比任何一个人都多。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寻找同类。她想,他是她的同类。因为那些难以启齿的秘密,她毫无压力,自然而然地说给他听,多半,他只是专心倾听,并不给予评论。当然,她也慢慢知道了他的故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公务员,妻子是同事,不过比他得志,至少,局长大人比较喜欢她。
她一听,就明白了。想来,他的日子更不好过。当然,他想过离婚,可是,孩子还小,小升初,中考,一个关口接一个关口,让他没有精力考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委屈,日子流水似地过去,居然也是一去经年。
她没有笑话他,只觉得心疼。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看他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眉目紧紧皱在一起时,她觉得那紧紧皱着的,也是自己的心。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好上了,他开心很多,她希望那不是自己的幻觉。
他对她很好,比她之前的男人都好,她能够感觉到,他的内心积攒着无比的热情和爱,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一个女人。每个节日都不会落下,他给她买礼物,请她吃饭,礼物不贵重,她却很看重。她的闺蜜知道了,叫她赶快放手,这样的男人沾上了就是湿手沾了干面粉,以后甩也甩不掉。她想,不知道谁是谁的干面粉呢,她都快四十了,找个相投的人并不容易。闺蜜却有另一套说辞,她说他又不能跟你结婚,还不能给你钱,干耗着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人生一定要有什么意思么?爱情一定要有什么意思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内心喜悦跳跃的感觉,这是她看重的意思。她不敢对闺蜜说,他对她承诺过,等孩子高考结束,他一定会提出离婚和她结婚的。她觉得,这并不重要。闺蜜说,你就是一傻子,人也不重要,钱也不重要,老了你怎么办?
在不是太老的偌长时间里,她都可以照顾自己,独自一个人安静地生活,她一向不是个热闹的人,因此也并不担心老了的孤苦。以为紧紧抓在手上的,也许是流失得最快的。至于闺蜜所说的钱和人,那都不是她能控制的,她唯一可以掌控的,是与他在一起的每一段时间里,自己内心的快乐安宁。比如,这一刻。
可是今天,她觉得他不像平时那么开心,抽烟的时候固然皱着眉,不抽的时候也并没有笑意,看着她的脸,像怀着满腹心事。也许,是自己刚才的眼泪招惹了他,她有些后悔,怪自己的任性。见面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了。
夜色暗下来,笼住了不远处的湖水。站在空荡荡的阅湖台尽头,仿佛站在了大湖的深处。灰色的轻烟均匀地铺在湖水之上,近处的灯光,远处的星光,随着波光漾动,旋转,变形,水面之下的世界光怪陆离。湖面绵延无尽,直至被彼岸的灯光拦截、阻断。
他伸出手揽住她的肩头,她感到自己轻轻颤抖了一下,然后,像一块磁铁那样,紧紧贴在他的胸口。抬头的那一刹那,他的吻准确无误地落下来,湖水,灯光,远处的人声,天地间的一切,如同她的眼睛,轻轻合上门。随着他的吻,她的心起起落落,身体仿佛漾在温暖的春水里,柔软如水草,失去了份量。
她如此紧密地贴合着他,感受他胸膛的起伏,心跳的变化,听到他模糊地呻吟了一下。
他说找个地方坐坐。她没有异议,虽然这和从前的每一次约会都不同。从前,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她,以至于有段时间,她觉得他就是为这个才和她约会的,但转念,处在他这样的位置上,他和她妻子之间,早已是有名无实,便止不住地心疼,也忍不住地欢欣,他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这种想法平衡了她对他妻子的欠疚,如果她不想结婚,他也不想的话,这是一段美好的,可以维持的关系。
可是,他不这么想,他想要婚姻。他说,如果你在婚姻里,你再优秀我也不会心动,如果你不和我结婚,我再心动也会放弃。他只是,身不由己,因为孩子正读高中,太辛苦了,做父亲的怎么忍心百上加斤。他抱着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嗅着她刚刚洗过的,散发着茉莉花香的头发,轻轻地说。这让她柔肠寸断,她怎么能再要求他更多呢?还有半年或者更短,她将完全地拥有他,整个的,从白天到黑夜。
今天,他们坐在一间咖啡店的半包厢里,灯光自然是幽暗的,特别设计过的,它让他们不再年轻的脸庞看起来柔和,色彩均匀,泛着瓷玉一样的光泽。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来看你么?他再次点燃一支烟,这回,因为急着想要他的答案,她没有看周围有没有禁烟标志。她摇摇头。
因为她中风了。他吐出一口烟,习惯性地拧紧双眉。
她只觉得惊诧,中风,不是应该上了年纪的人才得的病么?她知道他今年五十不到,她也不过四十七、八岁,柔光下照片中的女人,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怎么可能中风呢?接下来,一颗心笔直荡下去,向着无边的深渊。她知道,有什么事情在他们之间被改变了。
情况很严重?她知道一些关于中风的知识,因为多年以前,疼爱她的祖父就是中风走的,从发病到离开,中间不过隔着二十个小时的昏迷。
是的,严重,只是因为年轻,才抢救了下来,但失去了语言和行动功能。以后,怕也很难恢复了,要终生坐在轮椅上生活了。他说着,垂下了眼睛。
她才发现,他好像瘦了许多,一定是因为伺候妻子太辛苦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她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容忍妻子那么多年,认识她之后,也不会犹豫这三年多时间。他是个善良温和的男人,缺乏那种杀伐决断的魄力。可是,她就是喜欢他这一点。善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金子一样的品质,一个人失去了善良,就失去了做人的根基,是比什么都更可怕的。
那现在,怎么办?她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他的脸庞,那冰凉的粗糙的触感让她微微吃惊。
已经从医院回家了,请了护工,我的生活倒没有大的变化,孩子好像受了点刺激,自觉了很多。他在洁白的烟灰缸里掐熄了烟头,他抽烟,但总是抽一半就掐断,不知道是习惯还是突然意识到她坐在对面。
别担心,对孩子也许是好事,他会突然明白,父母已经年纪大了,需要自己独立,懂事,这是一种被成长,虽然痛苦,但也有禆益。她说这话时,想到自己的儿子,当年离婚时,孩子虽然表示了支持,但很长时间脸上都没有笑意,那种落寞,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她为此心疼到不行,也后悔到不行,为什么不忍一忍呢?忍到他长大,可以接受生活中这样的变故。
只是我们的事……他看着她,那目光让她心碎,让她无法不别过脸去。
我们,还像从前吧。其实,生活中每天都有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是她的真心话,在她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就知道了某些改变的发生。这会,面对他的欠疚,她内心升起温柔的迷雾,他总是为她想的,他知道自己很难兑现当初的承诺了。可是没关系,她紧紧抱了抱他的右胳膊。
现在,她的情况,即使孩子上了大学,我也不能提出离婚,否则,就是遗弃。他脸上的表情复杂,眼神痛楚,不知道是对患病的妻,还是对不能爱的她。
她眼前的胡萝卜,突然给人拿掉了,她只不过一愣神,仍然惯性地跑动起来。
他用力捏了捏她的手,表示感激,或者了解。然后他说,上次,不是听你说有个同事帮你介绍了个教师,不处处看?
那个教师,是,她想起来,一个沉默寡言的数学老师,拗不过热情的同事,又不能实情相告,她的确去约会了一次。但是一进门,看到他的样子,她就知道没戏。怎么说呢,他看起来比实际年纪着急些,头发,虽不至于秃顶,却已十分寥落。她喜欢头发浓密的男人,每一根头发都像钢针一样,哪怕花白了,那挺立的姿态和气势仍然在,一根根直指天空,又仿佛是生命力的象征。
他一开口,让刚刚落座的她差点要站起来。他说话不多,神情里,有一种莫名的倨傲。他比她大三岁,他认为这距离太小了,多少三十出头的女人想嫁他。她的心里,一下子冒出许多促狭的话来,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忍着,几近内伤。到最后,她不得不提前离座,并会钞了两杯咖啡的费用。她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计较两杯咖啡的付出。难捺好奇,去问同事,这个数学老师到底因了什么离的婚。同事说,她老婆出轨,和一个学生的家长。她笑起来,好像出了约会的那口恶气。闺蜜说,为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但连钱都不为你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比之更恶劣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视金钱如粪土,临了却锱铢必较的人。
男人看她独自微笑,不觉心酸,握住她手说,终究,还是我负了你。我只能祝你幸福了。
她从对数学老师的回忆中抬起头来,来不及收住脸上的笑意,说,你说什么呢?我能去哪?我也不想去哪。有句话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对我怎么样,而是我喜欢那个和你在一起时的自己。傻瓜,没有人能像你给我爱情的感觉。
男人在离开咖啡店时,去上了个洗手间。回来重新落座时,突然紧紧抱住她,仿佛生离死别的最后。她不知道,他是因为感动,因为他的不能离婚而她依然不离不弃,还是因为别的。她有些麻木,但努力配合着他的姿势,这姿势其实让她别扭而累,但她一动不动,忍着右胳膊被反转的疼痛。
她突然很想带他回家,她一个人的住处,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么多年里,他们一直在各种高低档次不同的宾馆里开房间,也说不清为什么,她从不提起让他一起回家,他也从不要求。在她这边,那房子里,有从前生活的痕迹,另一个男人留下的痕迹,还有孩子的气息,她竟做不到,让另一个她爱的人,加入这房子。或者说,是她的生活。在他这边,每次约会,由他安排食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但是今晚,他们心照不宣,既没有回她的家,也没有在外面过夜。他说,他要早点回家,因为护工到晚上八点就回去了。她听了,脸上流露出着急,时间早已过了八点,而他开车回去,至少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除了不能结婚,许多别的事情也改变了。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妻子,年纪轻轻的中风了,好像是对她往昔风流的一种报复。而他,终于等到了这理想的结局,有一种你终于落入了我手心里的快感。这念头一起,像毒蛇那样紧紧缠着她,甩也甩不掉。其实,她是不应该这样想的,妻子中风,他的苦难明显加重了。为什么她有这样的闲心逸致,或者胡思乱想呢?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
看他的车子离开,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她提着包,独自蹒跚着走回家去。身体的每块肌肉都很痛,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拥抱,还是别的。她疲惫地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突然很想抽一支烟。关于抽烟,她劝过他很多次,但都没有成功,他说,烟是他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唯一的伙伴,依着它,才在屈辱和寂寞中活下来。
夜已深,凉如水,她抱着自己的双肩,看天空中稀疏的星光,身边朦胧的路灯光,整个小区都睡了,夜色如同一层轻纱,温柔地笼住了所有。不远处停着的汽车,像一只只蹲伏的怪兽。她突然想起,他今天说过,要买辆车给她。自然,她拒绝了。虽然不富裕,但从来没有花别人钱的习惯,哪怕这个别人是他。这话题让她伤心,放在今天说,特别的不合适,显然是对她的一种弥补。可是,在她这里,真正的感情就是相互心疼,不需要弥补,也弥补不了。也许,男人的心思就是这样的吧,当他们无法兑现承诺时,总想从别处补偿。可是他不知道,这补偿,反而生生地将两个人拉开了距离。
本来,她是不想去学开车的,别看她心灵手巧的,却是个机器白痴,连电瓶车都不会开。自行车还是工作以后学的,她觉得自己在那些方面是特别没有能力的。可认识他后,有一次一起去附近的城市,他突然对她说,老了,一起出去自驾游,她开一段,他可以歇下来抽一支烟。她想象那场景,心动不已。冬天的时候,去报名学车。她对自己的判断很准确,学车颇吃了一点苦,也没少挨师傅的骂,但终究也考出了驾照,她很感激他,让她有勇气去挑战自我。
推开家门,借着微光,她看到,家里和她早上离开时一样,没有一丝变化,她的拖鞋,一只在毡垫上,一只在远处,像害了相思病, 遥遥相望。她换上近的那一只,又单脚跳着去找远处那一只。桌子上放着早餐的残羹冷炙,一碗炒酱,一碟常州萝卜干。她不是生活讲究的人,她觉得花时间力气穷究食物之精致,不如看看书,练练书法。可是,她学会了八宝炒酱,是他教她的。在她学会之前,他一直做给她吃,每次来,满满一乐扣盒子,里面有牛肉丁、豆干、笋丁、虾米等等,她想像着他一大早起来采买,一一细致做好,心里便升起无限暖意。张爱玲都说过,爱情,要落实到穿衣吃饭上来才妥当。有一阵,她也开始学做菜,想将来有一天,可以伺候他的一日三餐。可是他说,做你爱做的事吧,不要勉强自己,家里有一个人会做菜就行了。
是的,他们都设想过,共同的未来,将来的那个家,是他和她的。
躺在床上时,差不多十一点。她一向早睡,错过了时间,一时反而睡意全无。看着手机,黑色的屏幕沉默无声,按着往日,他到家里会给她发一条微信,而这个时间,他应该到了。信息终于来了,他说,到了,放心,好梦。
她却无法入梦。和每次他来看她一样,这一天,过得与平静的往日不同。早晨,他突然在QQ上说,下班后过来,一起吃个晚饭。然后,这一天都特别明亮起来,只是时间过得特别慢,像失去了弹性的橡皮筋,可以无限延长。终于,他对她说,到了,就在楼下。那时,离她下班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站在五楼的窗台前,她看到了他的黑色奥迪车,也看到了他。他倚在车门上抽烟,天热,只穿一件黑色的低圆领毛衣,卡其色长裤。这一眼,她就看出,他今天和平日不同,但不同在哪儿呢,她却看不出来。
下楼的心情,是许久没有的轻盈与快乐,为了延长这美好的心情,她特意放弃电梯走楼梯。她一出门,他就看到了,然后,他的眼神紧紧粘在她身上,一秒钟也没有移开。她想,幸好今天穿戴整齐,鞋子也是配合他高度的高跟鞋。年纪大了,她不能常年累月穿高跟鞋,一周要有一两天穿平跟鞋子,配休闲的衣服。而今天,一切都刚刚好。
被褥很凉,身体更是冰冷的,再裹紧被子还是觉得冷。她才想起,忘了冲热水袋了。热水袋是她最好的朋友,从初秋一直到暮春,都离不开。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样,一年四季,她的的手足都是凉的。想过很多办法,都不见效果。捏着她冰凉的手指,他总是往身上暖和的地方放;有时,她都能感觉到冷的手指,触到他温暖的身体,他本能地紧一下。
辗转各种姿势,都难以入睡。她想他。想那个湖边上的亲吻,他舌尖的味道,他微微颤抖的身体,自己那种不由自主的贴合,好像要嵌入到对方的身体里去,紧密的,天衣无缝的,生死相依的。
她想,他到家的第一件事,一定去看妻子睡了没有。而他的妻,对于深夜归来的丈夫一定多有猜忌,可是她站不起来了,她只能用毒箭一样的眼神追随他,询问他,他会说什么呢?同学聚会,单位加班?然后自顾去洗澡,上床。呃,他们还会睡在同一张床上么?她瘫痪的身体,还会有欲望么?当她看着这个曾经紧紧撑控在自己手心的男人,现在能够为所欲为,她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像孩子失去了对风筝的控制,她的心情会是怎样?
她心里有一点难过,他说他不能离婚了,儿子高考完也不可能了。的确是,她也不要他离婚。哪怕他们能在一起,纠结于良心的日子,也是难过的,无法真正幸福的。
这无望的结局一一铺展,她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她想,她和他,只能如此过一生了,他们的缘分,仅限于此。命里八尺,难求一丈,无法动弹。她唯一能做的,是对他更好,让这爱情到达极致的美好,让生活的无奈也化作美好。如果一切只是这样,那该多么美好!
果然如女人所推测的那样,男人回到家,先去房间里看了妻子,她已经熟睡,长时间的轮椅,缺乏运动,丰富的营养,让她还不曾衰老的身体在短时间变得痴肥,熟睡时,发出冗长的高低起伏的鼾声。
他在床边坐下来,看着她因为胖而渐渐变型的脸,移位的眉目和气质。难以想象,几个月前,她还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副局长,精致考究,香风细细地穿梭在豪华的地税办公大楼里。
人生真是无常。他与她,是税务学校的同学,一起学习,毕业,工作,结婚,养育儿子,升官发财,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是重合着过来的。应该,也是相爱过的吧,青春年少的时候。裂痕是何时产生的呢?他不知道。结婚后,他们本能地依着个性上的不同,外向的她更加向外拓展。而他,留下来照顾家里和孩子,直至两个人越走越远。
出轨那样的事,当事的另一方总是最后知道的。当单位里谣言满天飞时,他想他必须找她谈谈。可是,像以前所有的事情那样,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她已经约下了时间地点,她总是主动进攻的那一个。
她很坦白,并且说,如果觉得在局长面前难堪,她可以帮他调到开发区的地税上去,收入比市区还高一些,又可以避免三头六面的尴尬。
你就不想回头?你就不怕我提离婚?再怎样,他也愤怒了。
她轻轻一笑,好像很意外,这次,他不满意自己的安排。
终究,一切如妻子安排的那样,他去了开发区地税局,妻子在半年后升了副局长。在江南的这个县级市里,他们的收入属于第一方阵,高而稳定,他们贷款买了别墅,还打算把儿子送出国去。现实很坚硬,很多东西,是你不可抗拒的。
后来,他遇到了她,爱上了她。这个柔弱而不幸的女人给了他太多安慰,无论性情脾气世界观,都那么相近。他想,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一切都相安无事,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不知道妻子知不知道他的事,是否留意过每过两周,他就会晚归一次。也许,她什么都知道,而这正是她想要的结果。
这样一想,他又觉得犹如万箭穿心的难过,不是因为他还爱她,而是心疼那个青春年华里的自己,把全部的感情,付给这样一个女人。他常常会回到旧时光里,拥抱那个年轻的、对未来一无所知的自己,轻轻对他说,对不起。
可人生如行舟,总是向前的,十几二十年时间,累积起来的关系,感情,枝枝节节,砍哪哪疼,这不仅仅是爱不爱面子的关系。他对爱他的女人承诺过,孩子上了大学,会跟妻子提离婚。他知道,她会同意的,因为局长的太太正好得了乳腺癌,年初时去世了。究竟谁在给谁腾位子?这想法让人到中年的他感觉凄凉又可笑。
可是,她突然病了,在酒桌上,举着酒杯,如一只面粉口袋似地软绵绵地倒了下去。所有的未来设计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
忙乱过去之后,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他接她回家,雇了保姆和护工。从身体上说,他比从前省力,家里有人打扫,回家有热的饭菜,可一切都被强行改变了。他以为,以她的脾性,很难接受生命中这样的改变,可也并没有,她已经无法清晰地语言表达,干脆就不说话了。局长来家中看过她一回,带着他的助理,是那种上级看望下级的亲切友好。他仔细看他们之间的眼神,没有任何破绽。他知道,这些日子里,他们或者用手机联系着吧,可想到妻子已经不方便用手机,也没有见到她频繁地使用手机。
总之,有些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无须过多解释。他能从妻子脸上看到这种淡然,他很佩服她的坚强,他也想到自己的女人。如果他因为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而离开她,她会怎样呢?她那么柔弱无依,会不会想不开?这段时间的忙碌,让他不由自主地减少了和她的联络,她的反应也是淡然的,她说,知道你有事,知道你在忙,不会瞎想。
男人回到自己的房间,站在窗口抽了一支烟,然后打开衣橱开始整理。按照妻子的意思,明天,他就要从家里搬出去了,开始他向往已久的新生活。向往已久么?他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特别是刚刚和女人分别,看着灯光下她瘦弱的背影,他伏在方向盘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的女人,他的一无所知的女人,她不知道,今夜是他们的永别。
他对她说的,有一部分是实话,妻子中风了,他不能提出离婚,而且他知道,妻子这个年纪,只要护理得当,只要不再次中风,一般都会活个十年以上。那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十年,他不愿意他爱的女人等待那么久,错失了人生的风景。
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即使是生了那么重的病,妻子仍是这个家庭的主舵手。回家两个月后,妻子就起诉法院,要求和他离婚。看着起诉状的他,站在阳光里,只觉得挨了一闷棍,晕头转向。
以死相逼之外,妻子还做好了对自己日后生活的精细安排,最后,连法官都觉得应该判决离婚。而且她限他一周之内搬出去,没有召唤,禁止探望,自己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
婚,就这样离掉了。或许,他被误解为遗弃了她,可就像他认识她的三十年中任何一件事情一样,他无力反抗,只能遵行。
或许,妻子是对的,他需要新的生活,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余生都徘徊在她的病床边,为该死的道义负责。或者,妻子只是对从前的自己的一种惩罚,给他自由,是一种补偿。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不被加以任何额外条件地自由了,彻底从妻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当重新面对自己的内心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急着去找他的女人,告诉她这天大的好消息。他知道,她等待这个消息已经太久了,本来,他们说好,儿子上了大学后就提离婚,可能否顺利,谁也说不准。可是现在,就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意外之喜里分明包含了别的味道。他听到内心有细小的声音在提醒自己,再等等,你真的愿意和她结婚么?
他觉得,自己并不想和她结婚,尽管难以言说,但他不想欺骗自己。她比他小两岁,可当然,他能找到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至于感情,也能找到更新鲜的吧。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与她结婚,并不会迎来全新的生活,他要重新开始,矫正年轻时的眼光,给自己一个补偿。这些东西,原来早早藏在潜意识里,因为离婚,才真正冒出来。虽然惊讶,但真实。
他还想,幸好,他与她在两个城市,他们之间,一直也单线联系,否则,他真的没有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但他必须再见她一面,真话或谎言,总得对三年的感情有个交待。
所以,他今晚约会了她。
比起三个月前,她憔悴许多,正如她说,他也瘦了。他说了原委,她丝毫不加怀疑,也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不能在一起的现实。没有哭,也没有抱怨,像他了解的那样,她平静的,好脾气的,认命地接受了一切。那一刻,他差点失去了勇气,差点掏出皮包里的离婚判决书,然后告诉她,他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现在,他自由了。笑容会像鲜花一样在她脸上绽放吧,她会扑到他怀里,捶打他的胸口,说他太坏了吧。到底,什么也没有,除了最后的晚餐。连最后的爱也没有做,他没有心情,怕沉重的内疚让自己在她面前失态。
夜深了,人未眠,像往常一样,男人到家时给女人发了个微信,语气和用词也与往日无异,和往日不同的是,女人没有回信,她爱睡觉,估计,已经睡着了吧,男人苦笑着想,这样也好,最后一次,总要有点什么,有别于以往。
男人不知道,女人直到凌晨三点都没有睡着,她把相识以来的所有过往都细细回想了一遍。男人也不知道,晚餐之后,就在他上洗手间的时候,女人接到了一个电话,她急着找一支笔来记录客户的资料,无意间拉开了他的皮包,看到了那封判决书。男人更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这前前后后,他都没有感觉到丝毫异样,包括她面孔上笑容的浓淡。
一百公里以外的城市里,女人终于平静下来,还是像往常那样起床冲了热水袋,用它暖了手脚,渐渐睡去。微笑如一朵苦涩的花,开在她唇边,和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