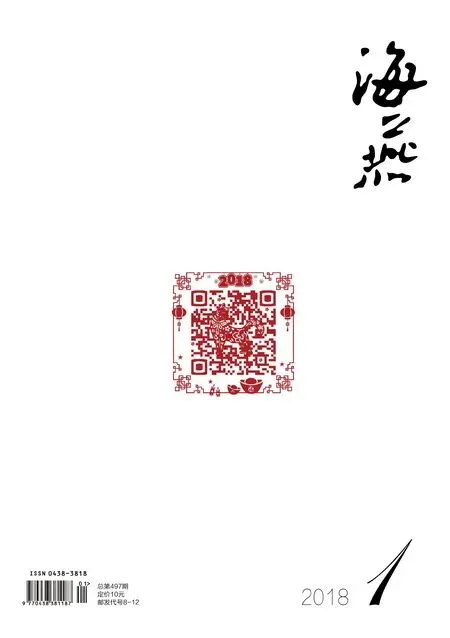面山而居
□程远
前山
前山在205小火车道南,也叫南山。205小火车从沟里终点站到沟外北三家站,蜿蜒十余公里,既拉矿石,也拉人,是小镇独特的风景。小镇,叫树基沟,我的家乡。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出生在小火车道北边的一栋白灰房里,从此,面山而居。
三哥说,你刻一个印章吧,就刻:面山而居。
那时,三哥爱好文学和书法,我则喜欢篆刻。现在想来,印章一定是刻了的,也一定是盖在了三哥买的那些书上,字帖上,那些写满颜筋柳骨的大大小小的纸片上,很像那么回事。遗憾的是,今天,当我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检那本自制的已残缺不全的印谱的时候,却不见这一枚——算了,反正这里也不是谈什么印章,用不着印证的。
这里,说的是前山。
从我家所在的粮站下片居民区,到前山共有三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即通过吴配成家门前的那条可走马车的大道;一条是我的同学王贵富家房后的;再一条就是西边,也就是我家居住的这趟房前的;后两条过铁道都是小道,且方向有所不同。我家门前的这条,过一片苞米地后,几乎是直对着正面的山顶而去。王贵富家房后的那条,走着走着就向东偏移了,直到我的另一个同学贾兆良家门口,再上到一个小山包,与从吴配成家那边过来的大道交汇,不远,又分开了。小道奔山梁,大道通向山腰中的树林——那里是矿山北岔竖井的通风口,建有组扇房。总之,无论是走哪条路,前山都近在咫尺。
记忆中,我是经常一个人去前山的,打柴,采菜,捡蘑菇。前山不仅离家近,而且坡缓路宽。虽走不了马车,但带车子、爬犁绰绰有余,不像后山,陡峭阴森。
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结伴去。那时,我们正念小学,三哥念中学。我说的我们,是指居住在粮站下片的我的发小兼同学,刘波,孙朋,王贵富,韩朝汉,曹大军。也包括铁道南的贾兆良。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但周三周六都是半天课,每每这时,我们就要去前山干点什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走贾兆良家门前的那条道,顺便也问问他去不去(贾兆良家如一个景点,他哥哥将通过他家的那条小道上竖了两个杆子,上横木板,用毛笔题曰:天下第一关)。然后穿树林,过山冈,最后绕到前山最高处,也就是有着几块大石砬子的地方,放下装满蘑菇的柳条筐,或是绑了四捆柴火的架子,脱掉外衣,攀上砬子,望山那边的矿井塔、废石堆和厂房。偶尔,有人影移动,是下班的工人,或是往山沟深处去的农民。那里,有一个叫许家坟的地方,住着几户人家。
孙朋说,许家坟的蘑菇才多呢,尤其红蘑。孙朋是采蘑菇好手。不仅采蘑菇,割柴火挖野菜种地等等,都在我们之上。可往往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只好下山。其实,许家坟我也是去过的,就是比许家坟更远的地方,我也去过,不过是跟哥哥,而非这些毛头小子。这是后话了。
前山不仅是我们这些孩子勤勉帮家的好去处,亦是闲时玩耍的乐园。尤其是秋天,山脚下那片连绵起伏的田地,苞米、高粱、大豆、地瓜、土豆,应有尽有,只要农人不在场,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捉迷藏,玩打仗,累了还时常偷吃地里的地瓜、萝卜、黄瓜,实在不行,就吃乌米——一种发育不良且含黑色素的苞米。到了冬天,这片空地则是打雪仗的战场,如果再玩得野些,还可以背上爬犁,上到半山腰甚至山顶,往下放。当然,这很危险,上片一个绰号叫三老头子的待业青年,就撞在了树上,肠子都划出来了,但没死。我和三老头子的弟弟是同学,我说,你哥命真大!他说,侥幸呗。
不过,我的同学王贵富就没有这般侥幸。
那是一个夏天。黄昏。不知因为什么,王贵富和家人吵架后疯了似的跑出家门,穿过铁道,以及铁道后面的柴火垛,直奔前山,边跑边伸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嘴里呜呜啦啦(他有些口吃)——最后,在山脚下的田地里站定,将手里的东西仰脖倒下。追上来的人,有他的哥哥、爸爸妈妈、邻居,还有我们几个同学,但都已措手不及——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刚喝了一半的敌敌畏塑料瓶。
王贵富是我非常要好的伙伴。他体格健壮,几乎能装下我。我们一起去山上打柴的时候,往往都是他帮我捆腰子、搭肩,翻山梁,也会主动返回来接我。那时,我们的父亲都在北岔看火药库,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送饭,两家相处很近。
谁知,半瓶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那年夏天,我忽然觉得日子寂寞、漫长。通往前山的小道,茅草疯长。
以后,上中学了,学习紧了,去前山的次数也少了。这时,除篆刻外,我对书法和绘画也产生了兴趣,中学唯一的一位美术老师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只是老师住在沟里,离我家远,加之老师擅长的是素描、玻璃画,而不是我喜欢的国画,所以去老师家讨教的次数并不多。相反,与二哥一个青年点的曲贵平联系颇密,那段时间他刚从农村抽回镇上,在家待着。二哥就说,曲贵平也画画,跟他学吧。曲贵平家就住在前山脚下,与贾兆良家遥相呼应,而且,曲贵平的弟弟曲贵友也是我的同学,曲贵平的妈妈和我的妈妈又经常一起捡地,有了这几层关系,去向曲贵平学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曲贵平是自学一路,技法上难比科班出身的美术老师——管他呢!画着玩吧。
于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总往曲家跑。
于是,我看见曲家那三间黄泥小屋的墙上,贴满了嫦娥奔月,猛虎上山,梅兰竹菊。最大的一幅中堂画的是松树,上题陈毅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望着这幅画,我沉默良久。我觉得笔墨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
后山
树基沟镇有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小学坐落在沟里,也就是205小火车站南面的山坡上,坡下是幼儿园、镇政府、俱乐部、医院、派出所和厂矿办公室,属于党政机关中心。中学位于粮站门前的公路旁,是小镇入口的必经之地。
我家住在粮站后院前的一排白灰房里,靠西头,挨着一条水沟。我们习惯叫西壕沟。
春天,几场雨后,西壕沟边的柳树毛子开始泛绿,学校操场上的几株白杨树也吐出了叶子。这时,三哥就会做几支柳笛,放在书包里,上学放学都带着。我却不谙此道,柳笛不仅弄不出声响,往往还要被淘气的同学抢去。更多的时候,我是坐在教室靠近窗子的位子上,望那一天比一天绿的白杨树叶,和那树叶后面囫囵的一座大山。我不知道,山上是否有个庙,庙里又是否有个和尚有个缸。
哥哥说,这些都没有。
哥哥带我去学校后山,打柴,捡蘑菇。
其实,我们很少去学校后山做这些事情。我们一般都爱去前山,这倒也不是就前山柴火茂密,蘑菇鲜美,主要是因为前山坡缓,且离家近,过铁道南那片苞米地就是。后山,则要绕过学校围墙,过山脚下的河套上的小木桥,再从老单家或是老曲家门前的菜园子边过去,上到后山的小道。着实有些别扭。
印象中,我自己只去过一次后山,接爸爸,并且没有翻过山岭,只是在山腰上的松树林边站了一会儿,天快黑了,不见爸爸的身影就回家了。
那时,爸爸在矿上采购组负责买柴火,常去周边的村庄。如果顺着小镇公路出沟,到一个叫大阳壕(四声)的地方分岔,右转是北三家方向,左走是莫日红方向。北三家是人民公社,那里有铁路,不仅通往比树基沟更大的矿山红透山矿,更通往县城、省城,甚至北京。但这个方向很少有柴火出售,虽然其间也经过几个村庄。爸爸常奔的是莫日红这边。莫日红是长白山余脉,也是本县名山,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山下散落着西大林、尖山子、下川子、李家堡、牛肺沟、上二道沟、下二道沟等等村庄。无疑,这些村庄是供给柴禾的首选之地。爸爸往往也是一去几天,谈价,订货,事情办妥后才从学校后山徒步回家。爸爸很少走公路,除非驾驶马车带领工友去拉柴火的时候。
后来,爸爸工作变动,就不再去莫日红山下那些村庄买柴火了。但通过那几年时间,爸爸和当地很多村民成了朋友,其中有小个子张叔,大个子冷疤瘌眼叔。前者爸爸通常叫小张,后者往往直呼绰号,对方也不恼,憨憨一笑。记忆中,他们常来我家串门,顺便带一些土特产,煎饼,地瓜,小豆,黄米,或某农作物改良品种,让我爸试种。这时,爸爸也会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喝酒,妈妈则找出一些旧衣物,包括矿山发的劳保用品,装进他们的口袋。如果是年根底下,给孩子们包去十块二十块钱也是自然的事。
这种交往持续了很久,直到我们家搬离了树基沟。
除爸爸常走学校后山外,妈妈也走过,几个哥哥也走过。妈妈去山那边的村庄捡地,哥哥去莫日红山伐木。而我的发小孙朋,更是往后山跑,割柴,捡蘑菇,采山菜,套野兔,打山鸡,无所不能。这不仅是因为他家有一支老洋炮,还因为他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孙朋没上初中,小学毕业后就待业了。
孙朋告诉我:后山有狼,别一个人去!
这让我有些害怕。
但我还是总想着后山,想着校园白杨树后面的后山,想着站在家门前小火车道上望着的后山。那是一个我所不知的世界。
一天,二哥对我说:明天早点起来,带你去莫日红。
我知道哥哥们去莫日红,为了赶时间,都是起早走学校后山,然后再穿过西大林、尖山子,最后爬到莫日红山上,寻找那些双手难以合拢的粗壮的树木,用铁锯锯倒,再锯成一扎厚的片段,背回家当菜板。这些菜板很结实,一用好几年。二哥送给过邻居,也送给过远在鞍山海城的姑姑叔叔。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天跟哥哥们去莫日红山的情景了,也不知道是否寻找到可做菜板的树木。但那一定是个冬天,寒冷的早晨,我们急行军一般,沿着学校后山的小路,很快就到了山顶,哥哥们抽烟歇息,我则气喘吁吁地俯瞰山底:原来,这是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沟!不仅平坦宽阔深远,而且村庄毗邻,群山相拥,远处袅娜的炊烟,挥手一般召唤我们。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走过学校后山,看到的山后风景。
更多的时候是每天面对着后山,或在它脚下的河套游泳、洗衣、放鹅放鸭,小镇唯一的一条河流,就在它的脚下缠绕。直到有一天,我们转到红透山矿读书、工作,学校后山乃至后山之后的那些村庄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但我从没忘却,甚至几个夜晚都做着同一个梦:自己走上后山小路,爬到山梁上,那山梁又与现实截然不同,仿佛一个大碗的边沿。山下也不是散落的村庄,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无数条鱼儿在海里畅游,珊瑚鲜艳,水草丰美……醒来,感慨不已。再后来,曾和几位初中同学回去看望我们的语文老师。那时,语文老师已经不教语文,甚至已经不在学校工作,而是担任了小镇(已经变为街道)上的派出所所长。我们在老师家喝完酒,就怂恿老师带我们去打枪。去哪?当然是学校后山啦!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学校后山,准确的说是后山脚下的河套。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派出所所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两颗子弹,我们瞄准树上挂着的空酒瓶子,眯着一只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手枪,可惜,没有射中。子弹只在后山的岩石上留下两个白点。
铁道
作为镇上两条交通要道之一,铁道似乎比大道(公路)更胜一筹,它不仅承载矿山物资的运输,还是人们出入小镇最为便捷的途径。那辆只有两节绿皮车厢的小火车,每天两次往返于镇内镇外,逢周一、周六,早晚还要各加一趟,以方便外地职工通勤。
大道,更多的是服务于镇内的人们日常生活。它从镇中心穿行而过。铁道则是沿着连绵的南山脚下,随势赋形,从镇上沟里的北岔(矿山井口之一)一路蜿蜒,直至20公里外穿过一个隧道,悬在北三家后山腰上。
我家住在铁道北边的一栋白灰房里,靠东头。从东往西依次是刘波家、孙朋家和杨柏栋家,我与前两者是小学同班同学,杨柏栋则高我们一届。所以,每天早上上学,我一般都是和前两者一起走,走铁道。铁道快。放学就不一定了,也许谁值日,也许谁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考试没有考好而被老师留下。我们也愿意走大道——热闹啊!如果不是急着回家的话,很是可以玩上一阵儿的。
后来刘波常说,小时候,我总让他背书包。
意思是我挺说了算,当时。
我们吃过早饭,走出家门,从杨柏栋家旁边的小路上到铁道,走一小段,出了我们家那排房的玻璃窗里还在用膳的大人们的视线,刘波说,我就会摘掉自己肩上的书包让他背,且美其名曰:挎双匣子(枪)!为什么不给孙朋挎?理由是孙朋学习不好,一个书包就够他受的了!直到教室门前,我才接回自己的书包。
是这样吗?我也不大清楚。总之,整个小学期间,我们几乎都是沿着这条铁道上学的。而那些发生在铁道上的故事,也远不止此,比如上片和下片半大小子们打架,也往往在铁道进行。上片,指百间房,也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谷守红家所在的居民区,那片的淘气包中好像有三老头子、郭德宝、李刚等;下片,就是我们粮站下片,比较刺头的是王贵福、丁宝五和杨锁柱子、杨柏栋五哥杨柏良。他们经常因一些矛盾而起争端,但他们又不敢在学校里打,而是放学后,甚至晚饭后,约到铁道上,每伙二三十人,相距四五十米,起先是对骂,叫嚣,最后纷纷弯腰捡拾铁道上的石子互掷,不仅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甚至还利用铁道南空地上的柴火垛做掩护,绕道学校前面付存家房后的那条小路包抄等等战术,直到有人肉搏起来,或被飞舞的石块击中头部,溅出鲜血——战斗(对,我们都这么叫)才结束。
作为杨柏良的追随者(他曾答应教我和孙朋练武术),我一定参加过这种战斗,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小屁孩,但起码会捡个石头什么的以示增援。难怪刘波批评我有欺负他的嫌疑,学习也不咋地,比孙朋好不到哪里。
当然,我也不算是坏学生,这种事情也不是经常发生。
更多的时候,我和孙朋、刘波背着炮兜子(矿上一种装炸药的帆布兜)沿着铁道往下走,去几公里外的大地挖野菜,捡拾粮食,或是给家畜弄饲料。这也要是星期天,或周三、周六的下午。平时,除了早晨上学走铁道,傍晚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上铁道玩,如果正赶上小火车开来,就急急地将早已揣在裤兜里的几颗铁钉放在铁轨上,看那呼啸而过的车轮是怎样将铁钉变成一个个弯刀、剑戟的,然后摭拾,然后烫手。没有火车来,我们就坐在瘦瘦的铁轨上,望那道下的白房,看房顶上的烟囱是否冒出炊烟,往往这时,冒出炊烟家的母亲就该站在院子里,面朝铁道,喊孩子回家吃饭了。如果是冬天,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帮着大人把自家门前的灯笼杆竖立,将红红的灯笼挂起,然后跑到铁道上,比谁家的灯笼杆高,红灯笼亮。我们甚至要在铁道上逡巡起来,俯瞰整个粮站下片,挨家挨户地数着,点着,评着,论着,如此一番折腾后才肯回家。
但这些,都不是我对故乡小火车铁道的最深记忆。唯有一事,让我念念不忘。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傍晚,父亲班上的同志(那时不称同事)跑到我家,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物和一些钱,跟他们一起去矿上。我与弟弟懵懵懂懂,母亲的眼泪却流了下来。几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了事故,腿摔伤了。一个月后,父亲也从矿医院回来,却拄了拐杖。原来那天下午,父亲与他班上的同志坐在运矿石的车斗里,从北岔出发,不久,却发现车闸失灵,几节车厢靠惯性行驶。这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它,也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系。如果火车中途脱轨,或一任到底,后果都将不堪设想。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在一个山脚转弯处(距我家门前不远),父亲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车……。
母亲说,父亲之所以选择在家门前跳车,是有深意的。
对此,我确信不疑。
当然,这也是后来的事了。后来,父亲在家休养了半年,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用他仅有的小学文化,断断续续地给我们念(读)家里的两本书:《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听得我直入迷。也许,我的文学启蒙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父亲的腿伤好了以后,就不再下井了,而是调到矿上的火药库当警卫。火药库在北岔附近的一个山坡上,离家很远。为了休班时能多干一些活儿——父亲在火药库周边开了菜地,也在山上砍了柴火,堆成垛,等到秋天,柴火干了以后再用带车子拉回家来。因此,父亲就很少回家吃饭,而由我和哥哥给他送饭。那时我已上小学二三年级了,只要天不黑,我就敢一个人去,有时也叫上刘波或孙朋,沿着家门前那两条铁轨,一直向沟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