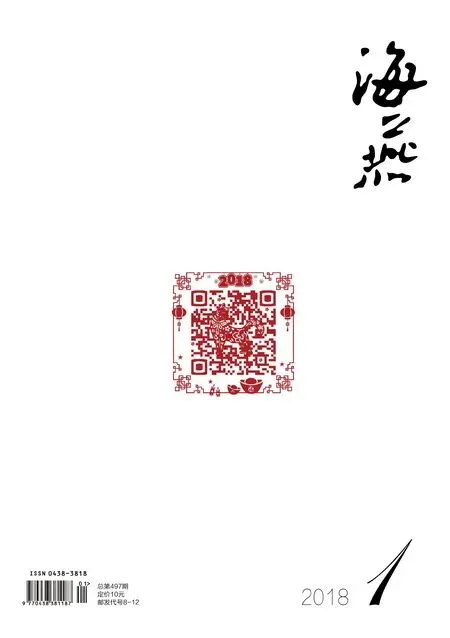旧金山随笔
□刘荒田
野草人寰
早上出门,马路对面一辆旧丰田车后面,一个女子在抽烟。这几乎成了此间的风景“标配”,只要时间对,她和车子必在那里。女子依然妙龄,但身板阔厚,不大 “妙”了。是抽烟使然还是反过来,出于对“豆腐块”体型的仇恨,破罐破摔,大抽其烟?不知道。
接下来,蓝天下的一切,笼统言之,均非第一次所见。电线杆上鹧鸪,垃圾桶上的乌鸦,后院的酢浆草和酸模花。背手迈八字步的清癯书生,是被我没来由地认定为“习易颇具心得”的;总是以幼儿园孩子的眼神看人的老太太,被我猜为丧偶多年者;银行的女柜台员,把车停好,步履轻盈地上班去,一个得体的微笑总会送来,第一次该是20年前。遛贵妃狗的白人老先生,爱听我夸他牵着的调皮鬼。路过一户人家,门开处,又一张熟脸孔,斯大林式的胡子,他每天一早都做一种特殊的功课:给楼上的老太太送报纸——她打开窗子,伸出颤巍巍的玉手,他站在人行道,往上一抛,从多数跌在窗台下到多数命中,花了多少年功夫。教堂所开的幼儿园,带孩子来的家长陆续出现。
天天如此,必然如此。妙不可言的重复,有老天爷的功劳——旧金山的极端天气甚少,一年之间的早上,大多数是这般晴和,搅和一眼到底的蓝天的,只有捏捏扭扭的雾气。于是,大多数早晨,都可以贴上这样的标签:“你看我的一天,就知道我的一年。”
想起这一句时惊觉:这早上的景物似藏玄机。由此,我琢磨“司空见惯浑闲事”的审美价值。如果不是误记,“你看到我的一天,就知道我的一年”一句,最早见于郭沫若介绍诗人鲁拜的文字,在松明的烛光中读它,是在乡村当饥寒交迫的知青的岁月,它教我痛心疾首,面对窗外的绵绵阴雨,长叹:何日挣开腻煞人的死水?每一天都有晨曦一般鲜活的生命力?
然而,今天,我为渺小之极的重复着迷。是典型的老人心态吗?从激进变保守,从愤世到认命,从求变到求“千万不要变”。也许是吧?生命的逻辑谁能忤逆?但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难道我们可因人生过于刻板,平和而厌弃,它的反面是不是我们所要,所能承受?
梭罗是这样赞美“野草”的:“有一万个农民整个的春天夏天锄它,然而它仍旧占优势,现在正在一切路径、牧场、田野和花园上胜利地生了出来——它们这样精力旺盛。我们竟用卑微的名字去侮辱它,例如猪草,苦艾,鸡草,鲋花。”退一步,即使被日复日地拷贝的平淡人生被激进者卑之为“野草”,也以“自在地疯长”为表征,而这正是值得珍惜的“正常”。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失去参照物(何等幸运!)欲求简明答案,且访问叙利亚难民营。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路,为自己的低能感叹。即使承认这就是“近于完美”的人生,也没有矜能的资本。至少,缺乏两种本领:破解“日常”的奥秘,挖掘每一个体生命的人性差异,表现静水的“流深”;以淑世精神,参与点点滴滴的社会改造工程。
风来,远处,海波卷舒。去杂货店买报回来,抽烟女子已离开。我心生愧疚。刚才对她莽下评断,何曾晓得她的经历和为人?也许,抽烟和她的身板并无干系,也许,她的心灵史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诗篇,如果我怀起码的尊敬,和她交上朋友,未必不能发现一个不下于蓝天的迷人天地。
零敲碎打的快乐
与友人约好,去他家喝蓝山咖啡。这种牌号的咖啡,国内遇到多次,但无一不是冒牌。友人所藏,却是他当记者的朋友出差牙买加,在玛威斯邦庄园买的。那里是原产地,因产品由日本人垄断,价格高得离谱,不是送给岳父大人作生日礼物还舍不得买,但岳父病重,无福消受,便送了一部分给这位资深咖啡“发烧友”。友人早就说好,为了让我开开“口”界,他怎么也得忍住诱惑,把最后几盎司咖啡豆留下来,与我分享。我乘地铁前去,一路仿佛闻到中等烘焙度咖啡的香味,兴奋过头,提前一个站出站。
在友人家,他开始操作,先“验明正身”,包装盒上有牙买加咖啡局官方注册图标。然后,他把咖啡豆研磨成粉。袖珍搅拌机的呼噜声,带出悠远的香气。友人在咖啡桌上摆上造型现代的玻璃器皿,他说这是传为制作“蓝山”而订购的。咖啡粉倒进容器,加入意大利产“霹雳加力奴”牌矿泉水。我问是冷饮吗?友人称是,说室温下的咖啡,特有风华才充分呈现。玻璃容器内的管子徐徐滴下褐色液体,教人想起古代计算时间的“铜壶滴漏”,而以咖啡代替沙粒,一滴滴地,把一段光阴切成浑圆、小巧、滋润的等候,无疑是妙不可言的。付出足够的耐心,10分钟后,咖啡倒进白瓷杯。友人送上佐饮的小曲奇饼。
平生第一次喝如假包换的“金牌蓝山”,岂能不隆而重之?入口的第一个感觉,是微咸。我知道,“拟咸味”乃这种带二氧化碳的矿泉水所有,再呷一小口,咖啡的味道慢悠悠地出来。友人以专家的口吻作讲解。我闭眼,调动最敏锐的味蕾捕捉。先是逼向鼻腔的香气,不冲,一阵紧似一阵。再是舌头上的溜滑感,如不加抑制,它会直下食道。再其次是醇厚,不过一茶匙的份量,却能够填满牙齿所有缝隙。不舍地吞下,冒上来的是酸,水果的酸。我张开口,叹一句:“这样的味道,从来没有尝过。”不是没有遗憾,我从来只喝热咖啡,不上不下的室温,口感不能不打点折扣。自然,小遗憾不能透露给东道主。他的理论一点没错。广东人说以“牛吃牡丹”比喻不会品尝美味,“人吃牡丹”亦然,我哪里有品咖啡的修为?总之,一杯下肚,快乐莫可名状。
不管怎样,有了快乐的“第一次”。人生多数东西,如值得纪念,常常首先在于“前所未有”;其次是堪回味的韵致。何止上美国亚马逊网购16盎司75美元的“蓝山”(还不是“金级”),平常日子赋以“生活的主人”的快乐,大都不是零敲碎打的吗?
比如,在键盘上码字,我每成一篇草稿,例必打印。明明知道存在硬盘或“云端”足够保险,无非爱上往稿纸上打孔,放进活页文件夹的习惯动作,咔嚓一下,一如乡村大娘黄昏时把鸡群叫进笼子后,放下竹门。“一件事”不论干得漂亮与否,完成就是快乐。又比如,我平日喝咖啡,上午忍住,宁可喝茶,到下午三四点,有点倦怠,才磨咖啡豆。热气腾腾的一杯,辅以蛋卷或“老婆饼”,无疑是一天之中快乐的高峰。
刚才在微信上,看到一位中断写作有年的作家朋友翻检他自己从前出版的书籍,我想对他说,姑且把汉字比作咖啡豆,蓝山不蓝山都行,须研磨,调制,以它来组成你的生命。敲字盘,就是快乐。
长“眼睛”的梧桐叶
早上,在门前马路边看到一片奇特的叶子,居然如人脸一般,长着一双眼睛——褐色的叶面上,两个黄色的椭圆形,我弯腰捡起。是梧桐叶,辞枝已久,色泽暗哑。
眼下是初春,市政广场上大片的梧桐林,枝条裸露,绿意尚未冒出。想起青年郑愁予的半句诗:“忍不住的春天”,但梧桐还在“忍住”。也有“忍不住”的,昨天路过市场街,一排梧桐步调整齐地坚持不绿,唯排头的一棵憋不住,顶部抽出绿芽。这么说来,手掌中的梧桐叶,该是去年凋谢的,从哪里飘来,移民史有多长,只有风知道。
常言道,一叶知秋。“知”的主体是人。但这一片配上“眼睛”的叶子,具备了“看”的资格。如果在凋落之前“看”,近处有同根的叶子、枝干、筑巢的小鸟;远处有云、阳光、彩虹,地上的万物。鉴于方圆数百公尺无梧桐,它的母枝在何处?
如果在下城中心的联合广场一带,巷子两旁有的是梧桐树。那里如果就是它的“原址”,那么“看”过什么呢?以星期天上午为例,以锁链横过阻止车辆通过的巷子内,专卖摄影作品的摊子刚刚开张,一张张镶框的独具匠心之作——意大利小镇色彩斑澜,七拐八弯的巷子,公园紫藤棚子下一张木造长椅四周,石板地上红得惊心的层层枫叶,与倒影合成一个椭圆的岸边村庄---收款台空落落的,主人不在。时值盛夏,梧桐叶片片丰腴。旁边,一位大肚子把吊带裤襻带腆成大弧的男高音,以录音机伴奏,引吭高歌意大利名曲《妈妈》。最高音处,叶子应声飘落。如果落叶之中有它,便成就了最具诗意的互动。歌唱家唱罢,向人行道上唯一的听众——络腮胡的流浪汉走近,索取廉价的赞美,再走到靠近马路旁,艰难竭蹶地弯腰,捡起小费罐里的两张纸币。这场面叶子看不到,因为被栅栏遮挡了视线。
倘若叶子躺在地上,视野便发生问题。仰视,只有或蓝或灰的天,树和屋子的影子,疾步而过的狗儿,自行车轮子。蚂蚁和云影慢吞吞地从身上爬过。
树叶进化为有视觉之物,可是石破天惊的事件。所谓“一叶一天国”,这“天国”乃是叶子的灵魂。自身枯荣,风雨阴晴,四季嬗递,露注的凝聚和消失,看够了,情动了,便以薄得不能再薄的唇来咏叹。人间多了这么多“眼睛”,岂能不热闹,不多事?窗前如果有梧桐,室内的人怕不怕被偷窥?要不要常常拉上帘子?而秋夜梧桐,雨里摇落,使得无数“眼睛”如流星般划过,许多年前,我写诗,将平卧于地的梧桐叶喻为秋心,“心”加上“眼”,梧桐这永恒的意象多了几重寄托?
我小心地把梧桐叶放在手心,一双眼睛与我对视。我要搞清楚,眼睛是不是天生的?若然,是个案还是带普遍性?如果叶皆如此,那么,为何过去没看到?我可是常常捡起落叶,端详它锯齿般的边缘和太多跌宕所造成的色地的。
我摸了摸,“眼睛”的线条微凸,可见不是刻上去的;再摸,有粉状物散开,眼睛不复成型。我迟疑片刻后,断定这弧线是由泥沙组成的。一连两个星期的雨,教这片栖息在边沿低洼处的叶子沾上泥沙,雨水冲刷,叶子上大部分泥沙离开,但靠近叶脉的残余,顺着纹路凝成圆弧。又一次天作之合!
按我本意,叶子“长眼”最好是自然状态,以便安放我无聊的假设。和泥沙合作也无伤大雅。不是人画的就好,怕就怕它是小学生手工课的作业。自然界的骗局比人间的好。
我以指头往弧线上擦擦,泥沙脱落,“眼睛”遁形。中国古人,有浪漫的“红叶题诗”,如今轮到泥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