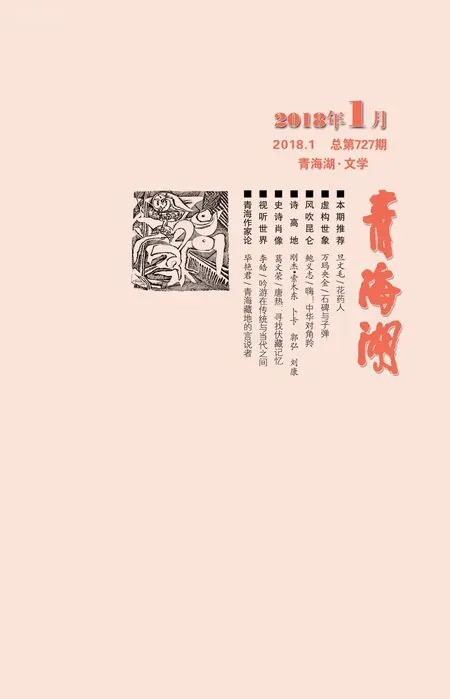刚杰·索木东的诗
所有的山,都是有筋骨的——路过静宁兼致李满强兄
在北方,那么多的山
都这么荒着,不声不响
那么多的人,都这么活着
不卑不亢。每一天的阳光
都会,按时落在头顶
天和地,就一起开阔了
这些年,也走了一些路
那么多的脚印,堆起来
足以,让我们记起回家
那么多的日子,荒废了
却足以,让我们想到未来
——之后,每一个冬夜
无比贪恋的那盘热炕
就成了,此生
无法治愈的疾病
其实,所有的山
都是有筋骨的
所有的山头,都会有
朝向村口的寺庙
所有的山坳里,也都藏着
不事张扬的祖坟
——当我们慢慢明白
这些道理的时候
一缕炊烟,就在午后
安静地升起
最重的雾霾,就来自心底
当蔚蓝的天空,已经成为
偶尔,炫耀的资本
我知道,自己离那片高原
究竟有多么遥远
我们终究是回不去了!
回不到,烈日炎炎下
四野歉收的大地
回不到,白雪皑皑里
冻疮难愈的记忆
——其实,无法丈量的
永远就是,理想
和现实的距离
那么多的暴劣
以道义之名
书写着所有的
暗无天日——
不会驾车的我
只能,攥紧孩子的小手
悄然走过,腊月初八
人迹稀少的黎明
新年晨记
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
在安宁一隅,每天都被
窗外的喧嚣唤醒——
此刻,在静谧的黄河南岸
只想找到,能够证实
自我存在的,那些响动
温润之手,伸进冬夜
却无法触摸,铁马冰河
和所有能够入梦的故事
轻柔之手,伸进黎明
尚能触及,昨夜的
凌厉,今晨的凄迷
和明日的虚妄……
所有的日子,还得这么
继续,向前推移——
静默的夜晚,尚能
看到,有人高举怒火
在夜半狂奔。尚能看到
更多的人,仔细涂抹着
一个堂皇的理由
那么,即便能给
每一个人,敞亮心扉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手握的这盏明灯
其实,并不能照亮
所有人的路程
逐渐明白高度的含义
始终不知道,一个人的
傲慢,究竟来自哪里
——远道而来的朋友
当我们盘腿而坐
天和地,就一起低了
祖母曾经留下遗言:
“遇事要把自己看大,
于人要把自己看小。”
——那年,我十一岁
准备离开熟悉的村寨
父亲辞世的时候,并没有
留下太多的嘱托——
这些年,我远离高原
躬身而行。人近中年时
才慢慢明白,高度
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