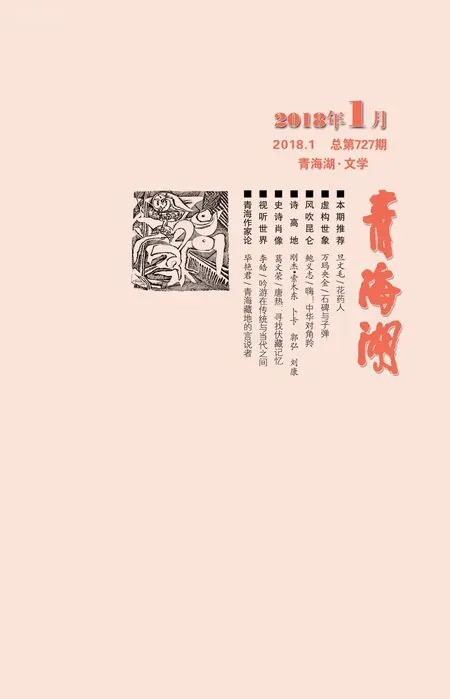青海藏地的言说者
——简论才旦的短篇小说
毕艳君
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自觉追求不断凸显,在激活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中,历史文明碎片在文学叙事中变得真实而又生动。作为富有创作才华的一个整体,藏族文学的发展每每让人刮目相看,一部部具有显著文化标识的藏族小说跃入读者视野并迅速深入人心博得大众的厚爱。阿来、次仁罗布、万玛才旦、江洋才让等藏族作家从不同的藏地走向大众,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可和喜欢。众所周知,藏族当代文学在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中虽然大量借鉴并吸收了来自各方的文化营养,但它的文化根基仍然是深厚的藏族文化。“在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藏族当代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体味到它强烈的民族审美意味与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参考文献:胡沛萍、于宏:藏族当代汉语文学与藏族文化心理浅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 第1期]
时至今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文坛并被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藏族作家所惯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在藏族文学发展中逐渐被新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呈现所取代。但我们不能否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藏族当代文学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多维的透视角度,对藏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的深度透视和反映,使藏族文学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些小说以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展现了藏族独具特色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通过发掘藏族文化特有的神秘现象和深刻底蕴来刻画藏族社会现实生活为旨趣,并宣告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文学流派在藏族文学中的确立。
也正是在这种突破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青海藏地的执著言说者才旦。出生于1953年的才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在《青年作家》《芳草》《广西文学》《山花》《滇池》《小说选刊》等国内众多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五十余部、短篇小说百余篇,计四百万字。作为一名藏族作家,才旦的小说创作,“重在体现生活在藏域大地上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宗教意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参考文献:才旦:《菩提》序,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一
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一个最重要的流派。它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基础上,吸收或运用来自民间或古代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幻想、幻景、夸张、梦魇等特点,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焦虑等观念,折射出制造一种超自然而又不脱离自然的神奇气氛,它并不是回避现实生活去臆造一个幻想的世界,而是面对现实、深入现实去发现人类生活中的奥秘,充分体现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独特风格。[参考文献: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由于藏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及其丰厚而独特的宗教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大量存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展示藏族独特而神秘的文化可谓相得益彰。宗教强烈地构成了藏族人的生活,与他们的生命水乳交融。无处不在的宗教,也给藏族传统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传统文化的神秘与深沉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挖掘,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民风民俗作为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频频出现。而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衬托下,魔幻现实主义也因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得到了完美应用,在艺术特征上呈现出神秘、魔幻、荒诞的特色和风格。[参考文献:徐琴: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评扎西达娃及其小说创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二者既相互依托又相互渲染,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统一,在才旦独立的思考方式下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而又略显神秘却又真实的藏民族生活图景。
才旦的精选短篇小说集《香巴拉的诱惑》[参考文献:才旦:《香巴拉的诱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以表现藏域神秘之象的作品为主,其中《香巴拉的诱惑》《世纪人的风景》《阴阳之界》《皈依》《我世纪的朋友》等作品,无论从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上皆带有不同程度的“魔幻”和“虚幻”的特色。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因民族身份和工作生活的环境,在创作风格上曾一度探索过藏域神秘之象,追求表现神秘、虚幻的创作风格和表达方式,并被文学界所赏识和认可。”
翻阅这本短篇集,我们不难发现才旦对本民族神秘文化的一种运用可谓是得心应手,俯拾即是。无论什么故事、什么事件,我们处处可见才旦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铺展。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他擅长将藏民族神秘的神话和现实、宗教传说和风土习俗交汇在一起,使作品在一种浓郁的藏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氛围中缓缓展开,继而在神秘的宗教生活、古老的历史传说、传统的风俗习惯、怪异的自然现象中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而这思考,就不仅仅是对故事本身的思考,更多的是对这种文化形成背景的认知与思考。同时,它也是作者本身对藏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宗教意识、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独特生活的着力表现。
在《世纪人的风景》中,怀孕的女人“吉”是在天空橘红的云飘到自己头顶时,在一阵剧烈的腹痛中生下了儿子“皮”,而这个不同寻常的场景注定了儿子皮将来的非同一般。果不其然,儿子皮竟然是尼家族大老爷子的转世,就在那片橘红色的云在天空流动时,注定了两个生命在前世今生的一来一回。而在《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中,边巴加央作为琼布夏大头人的转世,也是在母亲超月份的怀胎中在一片吉祥红云的笼罩下出生的。只有他,敢玩赶头人的游戏,也只有他,即使是个孩子也在享受着头人能享受的一切。生命的轮回在藏民族的信仰中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生命的消失与重现却又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们在才旦的描述中,看到了皮脖子上吊的小葫芦般的肉铃铛和边巴加央眉心里的红胎记,在看似迷离的渲染中用真实显现的东西印证了轮回的存在。
《香巴拉的诱惑》和《红色袈裟》两个故事历史背景虽然不同,但故事内容同出一辙。讲述的是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几十年乐此不疲绝不动摇的西行之路,带出了这个家族神话传说一样的一段历史。无论是索玛尔家族还是太阳家族,无论是没有结局的遗憾,还是70多岁的“我”和128岁族长爷孙式相依为命的离奇结局,才旦都在他熟悉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用了然于心的别样叙述给我们展示了藏民族深厚的一种文化底蕴。他们是在一种不容撼动也不可能被撼动的信仰下坚持着他们的生命,生命不止,信仰不息。于是族长生病,所有族人都不可能健康,他们要与族长同呼吸共命运,却从未想过要背弃族长。也许,这是神奇而荒诞的,也许这是扑朔而迷离的,但在才旦的文字中,我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背景的挖掘下看到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坚持与执著,从而加深了对藏民族的认识。明白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信念,这片从古海崛起的高原,这块中国西部的巨大高地在历史星光的照耀和雪域光芒的照耀下散发着它无可比拟的魅惑。
《藏獒》中,4岁的阿甲从不吃母乳却一直在吃藏獒的奶,4岁还不会走路的他却因为藏獒的假死而开始了奔跑,似乎他今生的到来就是为了等待与藏獒和某人的相遇,直到遇到前世做部落王时的管家华烈,大家才明白他就是部落王的转世。然而造化弄人世事难料,阿甲又因为屁股上那个公章印上的一点错误又失而复得回了家,却不知,这一回,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因为突然而降的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生灵都不复存在继而整个部落都悄然消失了。本以为是圆满结局,谁料才旦笔锋一转却让人长久回味。似乎阿甲的降临于世,就是为了完成转世的使命,一旦这个使命破碎,阿甲的生命也即结束,甚至于这片草原的一切也必将结束。也许“死亡不过是生命之旅中的一个驿站或一道门,推开它,开始了另一段生命”。在《蚀了的太阳和月亮没什么两样》中,36岁的老光棍瘸郎布因为在六月十六这天看见了神奇的蛇塔后,结束了自己的光棍生涯娶了漂亮的汉家姑娘美丽。属蛇的人遇见蛇就是遇见了自己的保护神,于是郎布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而同样属蛇的达拉却因为自己与蛇塔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与美丽的失之交臂而耿耿于怀,结果生出邪念,想用这些蛇来赚钱,却不曾想到一切自有天意,命丧他地,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这种种看似神秘与离奇的故事叙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活在青海藏地上的藏族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烈的宗教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才旦离奇的叙述中真切感受着藏民族的生存历史和生活体验。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才旦作品中涉及转世、保护神以及前世今生等等看似虚幻却又不得不让人感觉真实存在的种种言说。因为他给我们叙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在用不同的内容和情节浓缩着藏民族深厚的传统与宗教文化,荒诞、夸张、神秘、魔幻都只不过是他艺术的表达。它们打破了生与死、人与神的境界,把现实的事物与非现实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体现魔幻现实主义“将神奇的描写与现实的反映奇妙的结合起来,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这一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其作品在创造具有民族性特质的文学方面所作出的有益的探索。
二
才旦曾说:“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还是运用非现实主义的魔幻、虚幻的表达方式,我历来的主张是视题材而定。所以在面对现实题材时,我遵循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风格。《妻母的故事》《从此走向无奈》《藏獒》等,皆属于此类作品。”因为深谙本民族的一切,因此在表达方式上,才旦做到了现实与虚幻中的自由穿越。而这种熟稔的驾驭,不仅仅是他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与魔幻题材的不同表达,即使是在同一篇小说里,他也做到了现实与虚幻的自由穿越,构成了自己活泼明快尽情言说的叙事特征。
在《阴阳之界》中,才旦描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巴”和虚幻世界里的“兹”,同一个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命运。现实生活中的巴是个“穷得连阿爸阿妈这起码的家产都没有”的放羊娃,因为穷,就连恋人也不能朝夕相处为他而疯。而在虚幻的世界里,他来到了阳光灿烂的城市,受到了许多女人的欢迎,因为在她们看来,他是这个城市难得一见的童子。两个世界,一个真实,一个虚幻,他却在不同的世界有了不同的享受。现实世界里,他穷得一无所有,穷得被人看不起,为了爱,最终只能携已经疯了的恋人远走他乡。虚幻的世界里,他走到哪里都是受人欢迎的童子,带着他的丫走到哪里都会因为他而骄傲,可最终因为他不是童子而被抛弃。看上去这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也在传统与现代的文明交错中折射出了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带给人们的思想变化和冲击。
《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城市的对话》同样在看似荒诞离奇的故事对话中引出了一段真实的故事,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中显现了才旦对现实的一些思考与诘问。主人公妲一出场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漂亮女人,而她的死却又与这个小城的市长自己的丈夫紧密相关。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没有几个人是能抵挡诱惑的,即使是她优秀的丈夫,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宰这个城市命运的人也未能幸免。在他特批修建城中心河坎里的娱乐城并顺带修了属于自己和对手的别墅时,他的结局似乎就早已注定。因为在这同时,他还为了政绩特批修建了一座水库,如果他知道,正是这座水库将来会吞噬他和六百三十多个无辜的生命,也许他会停手,然而,当他正在仕途之路顺风而上出政绩的时候,他是无法预料如此悲惨的结局的,更何况这里还带着他对情人的爱意。只可惜,事与愿违,政绩是出了,随后却遭了大难。一对夫妻在阴间与阳间的对话,带出了人们对现实最深刻的反思。
《皈依》的故事更是扑朔迷离,主人公“公羊”因为卡嘉颇章寺的活佛在梦里给领导打过招呼而被请去写《佛典》,报酬竟然是兑现他20年前的一个祈愿。不管公羊愿意不愿意,佛的意愿不可违背,于是公羊一走就走了大半年的时间。而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不在家的时候。20年前他祈愿的无论10年、20年、50年、100年都希望离开自己与人私奔的恋人蛾儿回来的愿望实现了。蛾儿回来了,虽然她不是以蛾儿的身份回来的,但她毕竟是真的回来了,回到了公羊居住的冈巴拉的皮尔布拉巷,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可是这个心里早已装着别人的女人,像谜一样的要了另外3个女人的命,最后在公羊戳穿了她的真实身份后自杀身亡。谜一样地故事,谜一样的案件。才旦在他流畅的表述中给了读者并不流畅的思维,荒诞、离奇中隐约让我们看到了佛前的某个祈愿。《从此走向无奈》中的作家强嘎因为对酒无法控制的迷恋,而导致深爱自己的妻子自杀,这是个悲剧,故事中穿插出现的假喇嘛以及朋友娶朋友遗孀的事件却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为了一个嘱托,在这个民族生活的这片大地上,人们可以完全不顾及年龄和身份,心中长久地只存感念。也是为了一个嘱托,《妻母的故事》中段波成为了比边巴小两岁的丈人。才旦不仅在虚幻和荒诞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铺展,而且在现实的描述中也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与现代社会的某种冲突。故事看似离奇,但在这个民族充满神性和幻想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红色袈裟》中,当70岁的“我”和我128岁的爷历经一段神奇历史之后相依为命生活时,爷企图越过沼泽地的愿望只因他看见了河对岸如隐如现的一个现代化都市,一个既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又有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与现代人在广场上休闲的场景。现实与虚幻交错展现,神奇与真实并肩存在,128岁的爷甚至还想做个载人风筝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飞到现代都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犹如梦中。但这就是作为现代藏族人所要面临的抉择,保持传统一成不变还是寻找出路与现代文明接轨,古老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故事的演进中闪现着它的光芒。
作为青海高原这片雪域藏地上的言说者,才旦虽然现居城市,但从小耳濡目染浸透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他,是在历经两个藏区的工作生活之后站在藏文化圈内,切切实实以一个藏人身份进行言说的作家,因而在他无限的眷恋和热爱中,也有着对这个民族深刻的反思与期盼。他既反思本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不能和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同步前进的现实与冲突,也期盼着古老传统的藏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转型。因此在作品中,无论是插入神奇、怪诞的幻景,还是具体描述现实的故事,他都通过描写同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情结和心理状态,在似真非真、似明似暗、虚幻相间、难辨真假之中让人长久回味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文化。
三
一说起藏地,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寺院、经堂、佛像、转经、磕等身长头的佛教徒、顶礼膜拜的苦修者、色彩斑斓的嘛呢堆、遮天蔽日的猎猎经幡以及虔诚专修的红衣或黄衣喇嘛等等这些每天每时都有的景象,这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天笼罩在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即使不是当地的信徒也常常会被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著所深深打动,内心常会被一种强大的神圣感所充盈。因此,凡是走过藏地、深切感受过藏民族生活的人,都说每走过一次藏地,心灵就等于有过一次净化。“在藏地,纵使我见过万千座经幡,也不能不为下一座而感动”。这里有所有人期待的庄严场面,也有热情奔放勇敢豪迈的民族性格和优雅端庄高贵虔诚的宗教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藏地寺院,与那些虔诚的、善良的、五体投地磕着长头的信徒相遇时,无一不会为他们时刻在为众生祈祷祝福之心所触动和感染。
因为有着这种文化底蕴的浸润,也因为20世纪30年代欧洲最初的魔幻现实主义来自于绘画的评介,因此才旦在他富有特色的故事表述中也处处展现了一种大写意式的描绘。在他的笔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我”和“他(或她)”的对话,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而不是故事中人物之间你我分明的单纯对话,也许是我也许又不是我,人称变换交叉,对话却又不用引号,有时又穿插进人物的内心独白。这种看似陌生化的叙述不仅渲染了整个故事的审美效果,而且大大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景物的描述上也是如此,没有细腻的刻画,只有写意的涂染。在《世纪人的风景》中,尼家族大老爷的转世“皮”出生的时候,“起初,东天上出现了苍蝇似的一个橘红的小点,后来,那小点开始渐渐地洇大……再后来,那渐渐变大的橘红的云就循着白天太阳所走的轨迹,横渡中天,朝西的天际飘来,飘时,愈加地在放大。”《阴阳之界》中又这样描写:“草原被野季里没有色光的太阳涂染成了一幅色彩含混的拙劣画,无限朦胧,无限辽远。”当某种预兆出现时,景物的隐喻也是有着几多的蕴含。在《世纪人的风景》中,当知道尼家族大老爷的转世是“皮”之后,草原下了一场大雪,整个草原被覆盖了。而在《藏獒》中,阿甲死去的夜晚,“草原也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雪,大雪像一床厚重的棉被,把部落的草原捂了个严严实实”。藏族人对天空、湖泊、大山都是赋予了灵性的,在他们看来,青藏高原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宝贵家园,雪域高原上的一切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而雪的降落与否,也与他们心中某些隐秘之事是密切关联的。又如《皈依》中:“下雪的夜夕是靓丽而纯净的,猛乍间给人一种没有太阳的白天的感觉,这使人的心情不由得从沉夜的压抑中变得轻松起来。”《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中:“午后的太阳依旧像一张失血过多的产妇的脸,白惨惨地从阴空里鸟视着空寂寂、冷飕飕的琼布夏大院。”在着墨不多近于写意的描绘中,往往暗含故事发展的趋向与结局,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尤其是在他描写一些离奇事件或重大事件时,那种大写意式的挥毫泼墨与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一气呵成与酣畅淋漓。
作为熟悉本民族文化的才旦,作为青海藏地藏族生活的再现者和言说者,像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才旦在语言上也广泛地借鉴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大量使用本民族的方言俗语,使表达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像故事中一曲忧伤情歌的反复出现,就在以歌传情的曲调中让人感受了藏民族的民族特色。例如《阴阳之界》中“天上的云彩黑下了,地上的雨点儿大了,想起心上人哭下了,说起了你走时说的话了”。除了情歌,还有许多藏族同胞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与谚语都在不同故事的演绎中频频出现,熟悉得就像一个家里的两兄弟在日常对话。这种表述,即使是作品中出场的人物恍若是梦中人,他们来之蹊跷,去之迷离,或者是作品中常常出现似死犹活、鬼魂与世人对话等等一类的荒诞怪异的情节,整个故事也不会存在任何阅读上的障碍。
才旦的创作是成功的,在他历经三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做到了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再现独特的民族生活画卷,在夸张、象征、荒诞、意识流等的艺术表达中使作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他是禀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游弋于现实与虚幻中的创作代表。他的作品不仅传达了本民族丰厚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心理,而且在现实与魔幻的自由穿越中实现了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他大写意式的泼墨涂染中给读者勾勒了一幅青海高原藏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而更令人欣喜的是,相比于以《危地马拉的传说》《玉米人》《这个世界的王国》《深沉的河流》《百年孤独》为代表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普遍弥漫着孤独、消极、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来看,我们在才旦的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消极悲观的失望与落寞。
自古以来,各民族作家壮美、深情的创造感动和陶冶着各民族人民,文学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而少数民族文学更是这纽带上不可或缺的环节。藏族当代文学所走过的发展历程虽然短暂,但藏族作家在关于藏地的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关注脚下的土地,在力图展现藏文化的内核的同时,他们又以开阔的文化视野,主动吸收外来文化营养,从不同层面展开了文学写作创新的探索。[参考文献:道吉仁钦: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才旦在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历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在创作中不断地探索与表现题材的神秘气象相适应的文本形式,建构一个个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文本实属不易,令人尊敬。千百年来,雪域大地上斗转星移、春夏秋冬的生活提炼出了藏民族仁慈、神性的光芒。在这样一种弥漫着神话、传奇、宗教层层尽染的神秘而深沉的文化背景中,尤其是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面临多元文化背景的今天,相信藏族作家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与凝重的历史感的作品将会走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