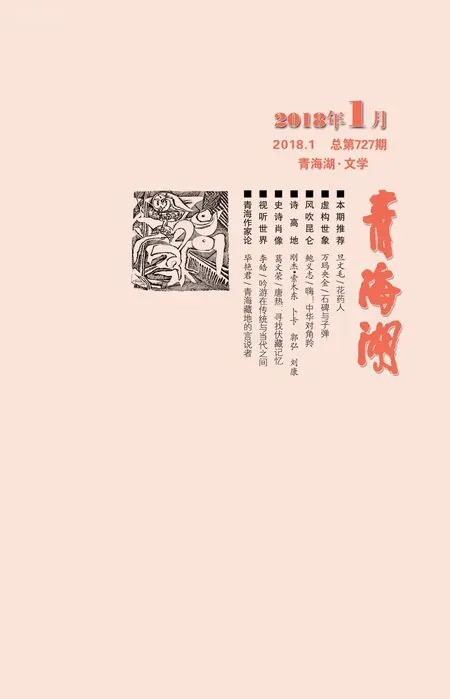战将与烈士(随笔)
祁建青
这是一组令人难忘的镜头。2016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当晚,中央电视台第六和第七频道分别播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王久辛愿做警世敲钟人》两部专题片。远隔大洋的两位作家在这个特殊日子进入公众视野,以才华、心血乃至生命铸就的宏大叙事告诫世界,人道的捍卫和正义的伸张,传世不衰的控诉发声丝毫不能空缺偃息。令人想到的还有更多,比如谢罪之追索无期,比如冤魂之祭奠永恒……
——题记
我至今不敢相信这一幕:2004年11月9日,美国旧金山市南的乡村小径上,张纯如在车内饮弹自尽。短促的枪声,震惊的世界,熟知她和她作品的人无不猛然顿悟而痛心疾首:在对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史实的书写中,张纯如的心魂也一次次被凌辱屠戮而无法自拔,她毋庸置疑是南京大屠杀血案又一位被害人、遇难者。
时间推至14前,1990年3月的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宿舍楼,一只空酒瓶被作家班学员王久辛上尉愤然摔碎在楼道。白天教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讲述在他眼前愈发清晰,三更夜半,尖厉刺耳的炸响令人心惊肉跳!一时间,如诗神附魂而文思泉涌,一句撕裂一句、一段突破一段,啸傲狂飙一气呵成,数日后长诗《狂雪》横空出世。
“为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军民招魂”,副标题使得诗歌主旨一下子高拔起来。我们意识里会随之隐约浮现,有关这场人间祸难的语言符号系统里,一个主祭司式的角色姿态,可以追溯至楚辞表达祭祀的《国殇》《大、少司命》而找到艺术源流及其原型。彝训鼎铭而降魔镇妖,魂兮归来30万,在当代中国史诗的名义下,《狂雪》不啻是一次“泪飞顿作倾盆雨”的诗歌公祭。或许可以这么说,一场等待已久的灵魂维度的追悼与昭雪,就在军旅诗人王久辛穿射历史的激情歌咏间上演了。
仿佛灵犀相通,数年后,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加州首次看到南京大屠杀资料,尽管童年时在父母处早有听闻,但还是被令人发指的暴行震惊了。她得出结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由此开始,遍及有关国家地区的采访与夜以继日的写作,整整历时3年。1997年12月,她的长篇专著《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时间正好为南京大屠杀发生60年。
“如果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她曾说过的话,就当她还活着我们在听——
“我将奉献一生,让你的真相昭示”;“我会把声音带给失语的人。你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如果你愿意把痛苦托付给我,我会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来承受”;“我会为真相而战。我的笔墨就是我的武器”。
现在我们认识到,很早关注南京大屠杀,以文学书写在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力,迄今莫过于这两位作家。作品完成时,王久辛刚过30岁,张纯如29岁。正值青春韶华、幸福生活的每一天该当怎样轻松惬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文学现代潮流甚嚣尘上的时代,作家诗人却没有痴迷攀爬所谓象牙塔,而真正沉下心俯下身,重拾这个老旧题材,以拒绝任何麻木遗忘的历史警觉,沉潜到事件真相里,去打捞抢救沉埋甚久遍体鳞伤的百姓关怀、民族正义和人类尊严。
调查记录和分析论述,一切都是事件史实的复原和呈现,这甚至要比一位审判官对于一个个证据梳理的要求更细致入微,而且更会侧重于感性体会的拆解陈辩。张纯如眼前就如同一部恐怖惊悚片循环播放,截然不同的是,恐怖惊悚片的心理预设只在影视虚构,作家面对和接触的却完全是一个接一个情节的真实。在这个真实里存在另一个真实:她已经将自己全然置于南京1937年末及随后那血腥绝望的六周之中。
“她在看资料的时候,经常泪流满面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丈夫的回忆,证明她发指眦裂到了何等地步。好友芭芭拉·梅森说,“她从知性和感性两个层面,真正了解那些情况、那些人所带给她自身的双重摧残伤害,太钻心彻骨,也太让我们伤心了……”年轻的姑娘,你太善良、太纯洁了。多年直面自己所概括的“日军酷刑百科全书(砍头,活焚,活埋,挖心,分尸,强奸,奸杀)”,安能承受得下?惊悸的细节、窒息的场景一次次割剜她的心,毛骨悚然的神经与惊恐万状的灵魂,向谁诉、与谁哭?日军的法西斯暴行就这样两次三次无数次摧残着这位既坚强又脆弱的女子。
有位心理医生分析描述,深度的抑郁症距神经分裂就差那么一点。患者会从环境到身边一事一物,产生对自己最具威胁伤害的心理神智错乱,这就是“被加害”幻觉。如此,张纯如最后的驾车出行,是在“逃离南京”?她生命的最后决绝,是看见一群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自己的必然应激反应?合理的推理只会印证结果的残酷,烈士之死,怎说不是为我们再现了那一可怕场景而訇然敲响了和平天空的警钟。
书出版不久,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张纯如要求立即跟他辩论。电视辩论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日本政府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相比大使的蛮横,她这话胜过许多外交辞令,又何等心平气和。这自然是对牛弹琴。日本极右翼分子多次打电话到她家,扬言要杀了她。试想,深夜你突然接到这样一个恐吓电话,还能安然入睡?
青海的红十字医院院内,有一尊张纯如汉白玉半身雕像。这大概是青海也可能是中国唯一的烈士雕像(据我所知,别的城市如南京是没有的),与张纯如并不认识的原院长张建青介绍,“7年前医院在全面打造优秀医院文化过程中,建有两尊塑像,一是张纯如汉白玉半身像,一是彭德怀全身铜像。一般情况下,会有很多人疑问,张纯如和彭德怀与医院文化有什么关系?”听他这么讲我也摇头了。多么简单个事儿,该医院前身为志愿军野战医院,纪念彭总关系自没得说;张纯如的雕像矗立在医院里,并无丝毫违和之感,她的写作伦理与医者医道不仅有关系而且存在更深层面的联系。立雕像的同时,张建青还撰写了文章《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人》,文中写道:“张纯如付出了青春和生命,当时她的儿子只有2岁3个月。学习民族英雄捍卫人类文明的那种坚忍不拔、不怕牺牲的思想境界和实际行动,能让我们了解真相,激发起民族责任使命感。”他大概也是我省最早关注张纯如的书写者。而此刻让我想到的是,天下不乏有志之士,天下亦不乏有识之士。
生存从来就是一件严肃甚至严峻的事情,天道人心有法则,公理良知须安在。所谓和平自由亦绝非某种一厢情愿,有时需要英勇搏斗流血牺牲方能为继。而文学上的波澜壮阔可歌可泣、英姿勃发壮志凌云、大刀阔斧横扫千军,在人类奋进的过去、现在和明天,在紧要的时刻和关头,必须引吭而唱响,必须时不时吹响“集合号”。这就是文学高原中期待隆起的高峰。没错,在存与亡、善与恶的对垒中,需要战士,需要战将,需要“真的猛士”。
20年前即1997年初,《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读者调查,结果显示,10多万被调查青年读者中83.9%认为,“日本”两字最容易使他们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居15个选项之首。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怎么样”,最高一项选择是“残忍”,占56%。为什么对“大和民族”会有这样的整体定性?恐怕原由只在日本政府众所周知的一贯表现中。
上世纪90年代,东西半球两个大国文学平台上,两位中华青年以其大才情践行了大担当。王久辛凭《狂雪》而折桂首届鲁迅文学奖,长诗多种文字版本远行海外。有人评述“他是以诗歌的尚方宝剑对阵恶魔的屠刀”。2003年12月13日,一座长39米、宽1.2米的铜质诗碑落成南京。镶嵌于墨色大理石壁的金灿灿诗碑,永久凝铸和彰显着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集体记忆与复兴梦想,而诗人亦无愧为中国当代诗歌方阵中一员“战将”。
大洋彼岸的掌声鲜花一样热烈灿烂。她的著作被赞誉是“一部轰动世界、震撼人心的巨著”“一部令国人流泪的书”“所有中国人都要看的书”,被称为“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书序作家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说“她改变了一个世界”。这些评价凸显作品的文献意义和品位分量。
他们的作品注定要载入史册。王久辛曾坦言:“我一定要成为‘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我要成为我,成为我自己都不可能重复与复制的诗人。因为我看到了那一星若火,它就在前边;我看见了那召唤的声音,细若游丝,却清晰入心。我必须奋力前行!”他告诉笔者:“26年前当我写《狂雪》的时候,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对国人来说还非常陌生。紫铜诗碑运抵南京的纪念馆时,当时只有十几个馆员,而且一切非常之简陋。如今纪念馆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馆了,忘不了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成山馆长。”你看,诗人谦虚了。没有《狂雪》力作,何来紫铜诗碑;而有了诗碑庄严坐镇,骤然放慢的脚步,导引沉吟的哀歌,将使人们在祭拜和垂问中秉持那一份清醒与坚定……
早在第一个公祭日实施时,王久辛撰文认为,国家正式设定公祭日意义是极其深远现实的。说深远,是讲对子孙万代的一个提醒,一个法定的对死难同胞的怀念时光,不容易变更;说现实,表明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对所有百姓生命的尊重、爱护与关怀。有了这个法定公祭日,就有了一个与文明国家相符的形象。
此言不虚。突出普通公众百姓这个对象主体,着力推进民间与社会各界的参与,以求最大最有效地覆盖普及和互动,第三个公祭日落幕之际,人们对这项国家活动内涵、形式的认识和理解也在持续深化,从中亦可见出世道人心的建构和滋养。荣耀加诸作家身上,而力量则源自人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