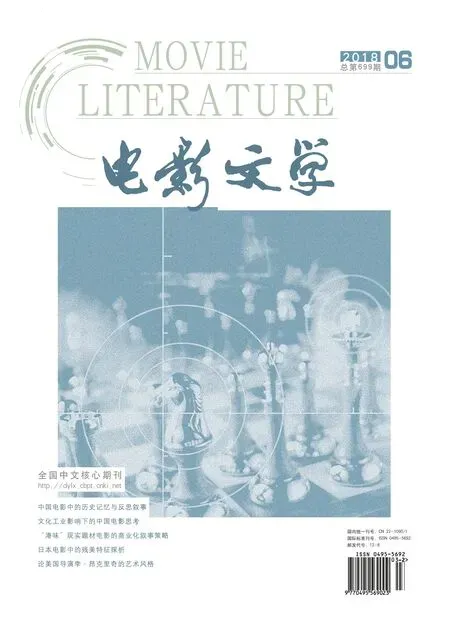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武侠亚类型典范
——以《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为例
王 健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在20世纪的欧美学术界,后现代语境所催生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了文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最初,新历史主义是为了阐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与社会环境、权力关系、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到后来扩展到了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正式提出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作为一种产生于多元、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思潮,其所带来的后现代性和泛文本语境下建构的历史时空颠覆和解构了传统历史主义的一元论和历史总体性的发展观,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大胆地质疑权威。
一、武侠与历史的指涉:文本性和历史性的互文关系
新历史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了旧历史主义的主张,即在对文艺作品进行历史的阐释,探讨作品和历史的关系的同时对历史加以选择性地修缮和微调,不是由历史本身来叙述,而是由现代人去叙述。另外,对旧的历史主义忽视文本的结构分析进行了修正,将形式主义美学融入进去,亦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学所提出的“形式”与“历史”的统一,用形式来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奥妙。因此,可以求证出新历史主义与“西马”有很大的渊源。而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由此可以看出,形式主义把艺术看成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世界,文艺作品并不是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工具,应该去研究作品的形式结构,这难免会有孤立、静止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而新历史主义则将形式美学放逐于历史的语境中,用文本去书写历史,同时文本又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蒙特洛斯将其定义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新历史主义是一种重新建构化的能指,旨在对已经书写了的一元化的历史重新颠覆和解构,在新时期的古装片改编中,历史本身的话语权被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小人物在历史大环境中大起大落的命运,以边缘人物的视角去查找历史的破绽和间隙,重新审视历史。
《绣春刀Ⅱ》与上一部相比历史语境更加浓厚,不再如同上部一样对官场腐败的批判裹挟武侠类型元素,而是上升到历史的维度。从萨尔浒战场到崇祯皇帝与阉党势力之争,权力关系、政治势力的角逐成为影片的主题,个体只是在竞争中的一枚“棋子”,传统东方诗学下的“侠客”精神已然渐次淡化,片中沈炼、裴纶以及北斋成为历史书写的一个叙述视点,传统正史的书写方法被重新建构。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完全不承认作为客观事实的历史,认为由事实产生的只是事实,不是思想,当然不是历史。在这里,克罗齐的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肯定有片面性,但是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是通过个体的书写从而达到的一种被导演阐释了的历史,用虚构的艺术真实去体现历史的真实。信王在剧中甚至向魏忠贤“下跪”,这在正史中甚至是不可能出现的,另外丁白缨、陆文昭作为信王权力斗争的工具,则完全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影片也正是通过明末“基层工作人员”去书写这段黑暗史,去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即使它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和隐喻的关联,此谓之历史的文本性,总结下来就是想象和虚构,用恰当的电影艺术形式,包括镜头语言、节奏、叙事策略、类型元素对历史进行阐释,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文本性。
另外,文本同时也具有历史性,文艺作品在创作出来的同时必定要受到意识形态、社会环境、政治氛围所制约,也可能给予了作者个人主观的某种政治立场和诉求。例如,法国电影《戏梦巴黎》是“五月风暴”下体现法国青年政治诉求的隐喻;《战狼2》《建军大业》就是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族身份认同的语境下,体现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神话;另外,还有2017年7月上映的被共青团中央官微批驳为“充满恶意的政治隐喻”的PG-13动画电影《大护法》,便是作者站在精英立场的激进自由主义的体现。所以,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应该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归根结底,《绣春刀Ⅱ》几个主要人物的诉求无非就是“自由”,片中北斋的那句“我梦想有一天不再是阉党当道”所对应的英文字幕是“Would have the freedom of speech”,在目前的意识形态下,这句翻译多少是值得玩味的,而字幕的解读无可避免地就具有一种社会历史性了。此谓之,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把文本和历史联系起来,用作品去解释历史,结合历史语境去创作或者批评。《绣春刀Ⅱ》作为一部武侠的亚类型,“亚”的一重含义,就是对历史的自由书写,寻找历史的缝隙以及不为人知的所谓“黑幕”,而正是对于历史的“任意消费”,也使之具有商业类型的特征,包括流行性、娱乐性、猎奇等。新历史主义善于将“大历史(History)”化为“小历史(history)”,它总是将视野投入到一些为“通史家”所不屑或难以发现的小问题、细部问题和见惯不惊的问题上,成为“专史家”。再完成了对“小历史”充满虚构的阐释后,也就使得影片具有一种“亚类型”的元素:正史的信王(History)和电影里的崇祯(history)、历史上信王与阉党的斗争(History)与电影中纳入了恩怨情仇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斗争(history)。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历史、文学不断被解构,例如,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中“尽皆过火,近似癫狂”的表演完全是对名著的颠覆,这也体现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后人可以随意地涂抹——凡人皆有七情六欲,神仙亦是如此,在片中代表强权势力、权威象征的观音大士竟也会像平常人一样怒斥唐僧太过喋喋不休。近年来,衍生了大量基于名著改编的IP电影,热度最高的就是以《西游记》为蓝本改编的西游电影,譬如《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还有暑期上映的《悟空传》都体现了创作者重写文化史、重述神话的新思路,而这种类型化了的被解构和颠覆的神话故事,也成为票房的卖点。这种“亚类型”化对历史维度的重构,对新时期的武侠电影的探索也是值得借鉴的,同旧武侠电影只是将历史背景作为陪衬相比(有些甚至模糊了年代背景),《绣春刀Ⅱ》甚至将行动人物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因素,如果沈炼杀了信王,历史将怎样改写?武侠片的商业卖点就不再是视觉奇观了,而是更形而上的思想博弈、天人交战了。
二、权力话语的角逐:意识形态下的多重政治势力
权力的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就意味着历史的书写是由谁来掌控的,文艺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不仅影响了创作方式,还影响了解读的方式。
作者在文本建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于复杂的人际社交网络之中的。格林布拉特说过:“没有什么纯粹的时刻和没有约束的客观性,确实,人类主题本身开始似乎就是非常不自由的,不过是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因此,创作活动既是作者与当时的历史的交流,又是与当下语境相交流。我们已经在上文中举了几个电影创作受当前语境影响的例子。
除此之外,文艺批评也和文艺创作一样,同样也会受到当下的意识形态影响去解读文本,一部文艺作品在新的时代,结合新的历史要求可能会焕发出不同的生机。在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中,按照批评标准和批评方式,将中国电影批评史划分成了九个不同的时期,电影史不再是编年史,而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去进行电影批评。电影批评受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深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在电影批评领域里的体现。因此,批评家或者是读者、观众在解读一部作品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加上去,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反映,也可能是批评者自己先入为主的文化习惯。例如,在“十七年”和“文革”时候的电影批评,意识形态就比任何阶段对电影批评的影响程度还要深;但是,在当前的消费语境下,一元的意识形态渗透程度就没有那么深,电影批评体现出了“现代性”,呼唤个体的独立,追求自由、解放的诉求,各种政治立场、思潮涌现。另外就是电影批评的媒介渠道也日趋多元,豆瓣、时光网、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普及实现了“零门槛”影评,观影群体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但是,由于个人智识、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得电影评论中所显现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同。以暑期档上映的《战狼Ⅱ》为例,影片在一线城市的票房就没有二至五线城市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更高学历、高素质的人群对于一元的意识形态渗透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的。不同群体政治立场可能是保守主义,也可能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
所以,新历史主义中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书写,一个是文本建构中的“作者论”,另一是接受美学的“读者论”。在《绣春刀Ⅱ》中,我们不讨论作者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历史观,我们着重讨论“读者论”。
“读者论”主张“从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接受、理解、阐释中显示出文学文本在历史上的生命力和种种传奇性遭遇和冲突”。一部文艺作品只有被读者、观众欣赏到,在脑海中产生意识,文本的传播和消费才能完成,文本已经不属于作者了。《绣春刀Ⅱ》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同时也体现了观众是什么立场,即使观众面对故事情节无动于衷,对任何势力都不表现出立场,这表明观众已经处于某种意识形态中了。
陆文昭代表的是激进主义势力,他想协助信王铲除异己,夺取皇位已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影片开头,萨尔浒之战后,陆文昭的那句“要换个活法了”,可见他是一个有着理想抱负的革命者,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代表的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势力;沈炼则是属于一种随波逐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乱世中他只是想谋求自保,可是恻隐之心却令他身陷囹圄。在这个修罗场中没有对错,他们只是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势力,陆文昭和沈炼能在萨尔浒之战的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但是却逃不过权力话语角逐的腥风血雨,在这个修罗场里面,生存比死亡更难。而观众也正是这个“修罗场”的建构者,观众拥有自身的政治立场,他们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填充到内容里面,罗曼·伊尔加顿指出,某些文学作品只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的空白点有待读者去填充、充实、丰富、深化,甚至“重建”。观众会在这个明末权力斗争的复杂纠葛中,选择自己的阵营去挑战权威、权势,而片中人物的主体性也是由观众去建构的,主体性就在于自身为了实现某种欲望而产生的行为动机,陆文昭作为革命者有自己的抱负,他想换个活法,他就具有主体性。沈炼亦是如此,他对北斋动了恻隐之心杀了凌总旗,使他陷入了本该不属于他的政治纷争中去。观众个人的话语权凌驾在了历史的话语权之上,历史是观众书写的,他们可以把自己先入为主的历史观、阶级立场带入片中不同的政治势力中,或者是支持陆文昭的激进革命之路,或者是同情沈炼的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中随波逐流,抑或是期许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使清朝入关结束明末的权力斗争。如果说《绣春刀》系列出了第三部,时间的坐标放在明朝覆灭,那同样是“读者论”,观众选择的结果,是观众意识形态、权力话语选择的结果。
《绣春刀Ⅱ》的权力关系的书写不仅是导演驱动的,更多的是观众合力推动的结果,这同时也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历史的书写是多重政治势力进行权力话语角逐的产物。福柯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总结为两个词:权力与知识。”知识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智识,它与权力关系有很大的关联,获取知识就是追逐权力的手段,而作为产出知识的主体,人并不具备超验的能力,人的主体性是通过各种权力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陆文昭、沈炼、裴纶的行动选择不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而是由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去选择,矛盾力量塑造了他们。
武侠与历史、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在《绣春刀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主题不再是快意恩仇、金戈铁马,侠客的身份被消解,在片中沈炼、陆文昭、裴纶都不算是侠客,好人和坏人的界限被模糊,他们只是政治博弈中的一枚“弃子”罢了。和传统武侠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人物类型相比,《绣春刀Ⅱ》中的人物明显的“亚类型”化了。新时期武侠片或多或少对传统武侠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和颠覆,比如,徐浩峰的《师父》已然不能被称为武侠片,称为武术片更合适,因为影片更多的是将“武”视为一种“武馆文化”,武术成为一种行当。但这种“亚类型”化毫无疑问是对武侠片的革新,传统的东西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三、探索历史的缝隙与偶然性:类型元素对宏大叙事的消解
武侠电影作为商业类型片的范畴,不同于拥有宏大叙事的历史正剧,这就意味着抱着既固守又创新态度去创作的武侠电影在具备历史内涵的同时,也要大胆去探索历史的缝隙,触发历史的偶然事件,采用碎片化叙事书写个体成长史,悬疑、惊悚、黑色幽默等这些类型元素都可以作为武侠电影的养料。
新历史主义强调的历史的偶然性也正需要通过这一系列类型元素去表现。
一方面,是新时期武侠电影艺术形式创新的内在要求。旧武侠不大重视文本的多义性、暧昧性处理,而悬疑元素正好弥补了这一点,使得武侠片不再是“视觉奇观”从而使观众与文本产生互动;另一方面,是商业类型的必然要求。郑树森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一书中说,类型电影是一种“带有文化性质的工业制作”,或者说是一种商业化生产的产物,它是生产者按照消费群体的口味精心制作的商品。观众早已厌倦了旧武侠电影的打打杀杀,武侠电影的“亚类型”化是大势所趋,前几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影片上升到了儒道释的哲学高度,它并没有通过故事性和视觉效果去博人眼球,而是去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情感问题以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赢得了国内外较高的赞誉,这就是“亚类型”的成功尝试。所谓亚类型,就是在过去的武侠电影里加一些观众没看过的或者是期待的东西,《绣春刀Ⅱ》这部集悬疑、惊悚、爱情于一体的武侠电影就诞生了,悬疑的处理一环扣一环,场景的设置颇具黑色电影意味,武戏扎实,还有人气明星张震、杨幂的加盟,使之成为武侠亚类型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一)悬疑“亚类型”与历史的偶然性的融合
新历史主义喜欢去收集处于历史边缘化的奇闻逸事,“探究这些奇闻逸事背后丰富的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现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绣春刀Ⅱ》中信王为了力挽大明将倾的江山集结了一批武林高手来与阉党进行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围绕着那本《宝船建造志》,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在历史上信王和万历皇帝的感情非常好,但是在历史的最边缘,信王却成为间接导致万历“命不久矣”的罪魁祸首,使之与阉党的权力斗争更富有传奇色彩,放在历史的维度上,使得传统历史被颠覆,历史的最边缘浮出了水面,这一历史事件,“沉船事件”、信王与阉党斗争的始末,则是以沈炼、陆文昭、裴纶等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视角去叙述的。
大历史的书写,是由处于权力中心、正统地位的统治者书写的。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登基之后的信王,大笔一挥将沈炼的名字抹去,而“沉船事件”的始末也终将被抹灭,明史也会对此事件只字不提。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的话语权交给了边缘化的、受到权威镇压的、受排斥的小人物,剑走偏锋去探究历史,而建构起整个影片叙事框架的也正是这些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偶然性的行动却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导演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中,更加侧重于艺术真实,在历史的框架中采用艺术虚构来自由书写,使权力角逐显得更加残酷,但也并没有将历史扭曲,因为当时的斗争程度可能会比电影中的剧情还要血腥。
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合规律的,个别偶然事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起作用。影片中的历史框架也正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去构建的,导演将行动人物置于情景中用“悬疑”的手法将迷雾层层拨开。
全片围绕“沉船事件”展开,沈炼为救画师北斋杀死了凌总旗,他一方面要摆脱裴纶的调查,一方面要在丁白缨的要挟下纵火烧了锦衣卫经历司,沈炼由此展开了对此事件的调查,最后得知幕后黑手竟然是信王。影片在悬疑的氛围营造中,颇具黑色电影的意味,人物正义邪恶的身份被模糊,陆文昭暗害裴纶、追杀沈炼,北斋,只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所处的社会也是弊端丛生、内忧外患,人物在现实中陷入自己的欲望无法自拔,沈炼对北斋的爱慕之情、陆文昭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北斋对信王的一厢情愿……都使得主体处于一种失望和悲观中。“修罗战场”也正是象征这一阴森、诡异的梦魇世界。
(二)传统二元对立叙事向多元的碎片化叙事转向
在《绣春刀Ⅱ》中和第一部同样不再采用传统武侠电影所推崇的线性的二元对立叙事,即起承转合,叙事是围绕“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去展开具体行动的,人物的动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亦如电子游戏里的通关升级,是一个封闭的、严谨的叙事空间。
而碎片化叙事则更加多元,文本中的人物不再有共同的驱动目标,而是有各自的行动指向,性格特征也已不是“扁平化”的善恶对立类型,就像片中每个人都不能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充其量只是有各自立场的时代弄潮儿。影片的叙事策略也更像是拼图式的、琐碎的,它打破了时空的、逻辑的界限。比如,萨尔浒之战、中元节金陵楼郭真被杀之谜、追捕东林党“北斋”“沉船”事件、魏忠贤追杀沈炼三人等。叙事模块是支离破碎的,是呈碎片化的,观众在接收到某一叙事模块的讯息时会戛然而止,然后又重新架构时空,萨尔浒之战后剧情立即辗转到数年之后的“酒楼谋杀案”。而影片中的核心——“沉船事件”根据叙事逻辑推理是发生在酒楼案之前,这一部分时空并没有直接呈现在文本中,而是以第三方沈炼、裴纶的视角去揭开迷雾:信王为什么让陆文昭灭郭真之口?为什么命沈炼杀北斋?为什么反过来求魏忠贤灭陆文昭口?
影片试图让观众在一堆看似无序的、零乱的碎片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秩序的叙事框架,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而碎片化叙事本身对观众心理的引导作用所带来的多义性,也为故事的新进展,即影片结束后观众期待的续集,做好了心理铺垫。第一部讲述的是信王登基后的事情;第二部是信王登基前夕的事情;第三部,基于第二部、第一部的叙事逻辑,观众肯定会将所期待的历史坐标放置在明朝覆灭,清朝入关前后的这段时间,朝代更迭中沈炼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碎片化叙事,使得叙事单位缩小至碎片,而正是碎片所带来的开放性、不确定性以及思维盲区,使观众得以发挥想象填补空白。根据剧作的“召唤结构”的提出者伊瑟尔的观点,一部作品的空白点和不确定点越多,读者便越能参与到作品的二次创作和审美意蕴的挖掘中。在片中的最后一组镜头,崇祯烫去了沈炼的名字,沈炼免去一死,才有了第一部的故事,而观众也会从第一部想到沈炼在清朝入关后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也为续集的剧情走向做出了暗示。
四、结 语
《绣春刀Ⅱ》作为新时期武侠电影亚类型的典范,它将武侠和历史缝合在了一起,用新历史主义建构起了整体的历史观,同时也颠覆和消解了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用悬疑、碎片化叙事去书写历史的偶然性。
在武侠电影创作中既要继承也要有创新,本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对历史观的重构,将个体的成长史放置在重构的历史当中,另外就是其他非武侠片的类型元素的融入,包括悬疑、推理以及对黑色电影的借鉴所形成的武侠“亚类型”;电影对于传统武侠的继承除了干净利落的动作视觉外,最大的亮点就是服饰道具、武器装备,例如,丁白缨使用的倭刀、裴纶的夹刀棍,还有锦衣卫的飞鱼服,剧组的用心、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受新历史主义思潮指导的武侠电影不应只是制造暴力形象的工具,而应注重精神思辨,注重人文情怀,注重个体的表达,要敢于去质疑历史,打破权威。另外,新历史主义具有的反叛意识也使得武侠电影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创新,“亚类型”的融入、拼贴、戏拟等手法的运用,都为武侠电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