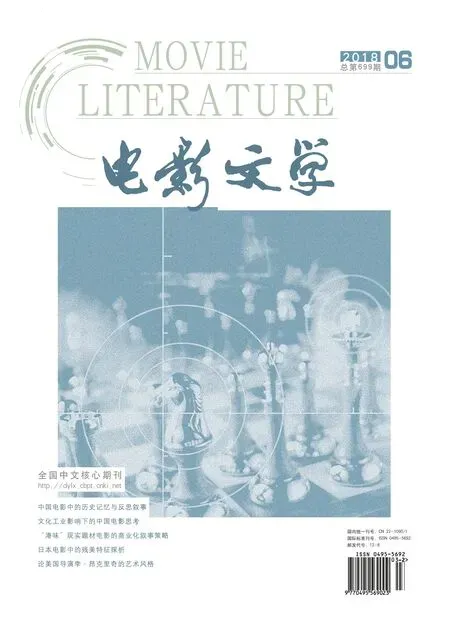中美电影中的消费文化对比
林 娜
(海南医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
电影自诞生起,就与消费文化难解难分。所谓“消费文化”,按照鲍德里亚的经典解释,意即以制造消费符号为目的的逻辑话语系统,其价值符号的确立首要在于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区隔,大众对于商品的消费不只是行使价值的获取权,更核心的是对于价值符号的消费。中美影像中的消费文化对比,是当代这一现象学景观其视觉空间展现的典型图式之一。因为电影作为一种现实反映,是对人类、社会做出动态化、情景化描绘的特殊形式,其整体上具有某些“民族志”特征,其所呈现的生活世界必然与该民族、国家特定的文化思维定式与地方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同是消费文化的影像视觉呈现,具有东西文化分野样板意义的中美双方话语实践乃至指涉系统,基于各自的文化习惯和意识形态制约,便有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而其消费文化所互相呈现的话语表达的同异分野,是揭示国族文化深层结构的有力证明。
一、都市经验的分化:“感性美学”的纪实话语与“现代性”的另类谱系
都市经验是消费文化展示最集中的场域。现代都市日益强化其商业消费与资本运作为中心话语的形态,从而为消费行为,包括电影消费给予生存环境。可以说,都市的经验呈现是人类消费文化的凸显,更是大众消费文化构建环节中最具意象的链接。因此,当中美电影作为消费文化的公共文本对自身的症候做出映射时,其都市经验的传达直接所指涉的将是文化共同体的意识结构,其分化也是各自社会显性结构的表达。
在中国电影中,消费文化的艺术格局与观念生态显现出一种“感性美学”的纪实话语。电影作为反映本民族社会生活状态的综合艺术,其独特的影像记录方式,在深层因素上受到特定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经济结构的限制。中国电影中都市经验凸显出既感伤又纪实的话语基调,这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起步阶段多必然携带的消费文化基因。从早期的《神女》(1934)、《渔光曲》(1934)到《林家铺子》(1959),到后来的《秋菊打官司》(1992)、《手机》(2003),再到的《杜拉拉升职记》(2010)、《使徒行者》(2016)等片,无一不呈现出一种感性美学与纪实方法并存的状态,所展现的都市不啻为一个建构与摧毁并存的空间,其消费文化意识也是一种受到眼花缭乱刺激的感性表达和震惊体验。比如导演娄烨,被誉为中国城市化时代社会变迁、都市景观及消费意识流变最著名的观察者之一,他的作品诸如《苏州河》《浮城谜事》《推拿》等,所凸显的都市景观都是始终处于调整与变动之中,而人的命运、价值观、心理状态都伴随着消费文化的甚嚣尘上和都市人间的翻云覆雨中陷入“动荡—丢失—不安—寻找”的循环里,那种都市人生的生存困惑与精神困境如影随形。影片之中的街头、霓虹、熙攘的人群、高耸的大厦,都在敏锐观察和诚实表达的镜头中弥漫着一股清晰可闻的感伤情绪。可以说,这是中国电影惯性的、普泛化的,对于都市经验和消费文化蔓延中的当代中国现实质感的影像解读。
而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中,在传达都市经验和“社会指称性”的消费文化浪潮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择取一种光怪陆离的、幻觉荒诞的、奇特扭曲的“现代性”表述程式。这是因为美国后现代式的社会发展,已然使得电影、都市、消费三者完全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谋同质的关系,其消费过剩与过度都市化现状,都赋予了影像艺术特定的灵感、独特的视角及惯常性的呈现。因此,无论是早期的《城市之光》(1931)、《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还是后来的《魔鬼代言人》(1997)、《罪恶之城》(2005)、《惊天魔盗团》(2013)等,其视角几乎永恒地停驻在绚丽奇幻的华灯、压抑高耸的群楼、急促怪异的人群、犹如虫蚁爬行的汽车……此际的都市乃至生活其中的人,仿佛都只是影像中的机械布景或者是衬托式的舞台道具,电影的语言与内涵本身存在着无尽的荒凉与无助之感。在这里,都市表现谱系中,电影已然是现代性的“事物之表”,是消费至上的场域,又似乎是忧郁的热带,人类的恐惧、疑虑、困顿、疏离、抵抗、虚无都以一种群体性的症候状态,聚集在了消费主义主导的都市影像图式谱系之中。
二、视觉见证的歧义:立足现实的实用理性与娱乐至上的狂欢化图景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费文化时代的视觉见证。消费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表征着一种注重商品文化精神特性、符号价值与形象价值的观念样式,而电影正是透过观众对声画呈现的体验来完成其特殊的消费主义意向活动的。因此,从电影视觉现象学的角度而言,中美电影中的消费文化景观,必然有各自的背景、空间和样态的指涉,呈现出差异性的审美实践。
在中国电影对消费文化做出的视觉重构中,始终潜隐着一种立足现实世界的实用理性趋向。这是中国文化和大众心理积淀而来的实用主义所决定的,这种深层的情感使得中国电影即便在表现消费文化的震惊景观时,其视觉立场乃至叙述姿态都可以超越感性的本能,在有关传统、现代的冲突对抗中最终倒向传统,从而在画面营造乃至情绪凸显上都有着温柔敦厚、注重实用的文化心态。作为讲述消费文化盛行下当代中国现实景观标志性符号的导演,冯小刚的作品就是绝佳例证。冯氏的电影,无论是《不见不散》《大腕》,还是《手机》《非诚勿扰》等,都是消费文化弥漫下都市中国人的现代传奇:北京人刘元洛杉矶闯荡时不断引发的乡愁式的回忆;尤优穿行在都市繁华楼群中“乡村式”的人际关系处理;作为著名主持人的严守一无聊空虚的视觉化表达……在这些对消费文化时代事物和人群渲染的视觉表象背后,几乎都是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有关实用理性生活姿态,“东方传奇式”视觉图谱的刻画。这种视觉见证的方式、视觉记忆与其所见证的图式本身,其所触及的其实是一套转型中国的复杂观念体系。
在美国电影中,有关消费文化的视觉内容早已成为娱乐至上的视觉审美的附庸,展现出消费主义狂欢化的图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西方世界迎来了消费产品、消费观念及影像消费意识高涨的图像时代,此际最突出的消费文化特征就是影像、视像消费成为大众狂欢式参与的文化盛宴、精神快餐。伴随着这种消费文化至上的语境,在此后的美国影片中,消费行为呈现为符号化,人与人之间、人与客体之间的行为关系被建筑在后现代消费文化氛围之中。当下美国社会中的商业广场、博物馆、街道、购物中心、游览设施、主题乐园等景观,都在电影中表现出消费符号与消费体验的共同特征。
这种消费文化至上的狂欢化影像语境,在奥利弗·斯通的作品中即有着经典的呈现:《华尔街》里的现代美国城市,完全被梦境一般的视觉冲击画面所涵盖,股市大亨戈登更像是一个消费主义欲望膨胀的影像符号,无所不在的摩天大厦、非现实般的车水马龙、光线摇曳的高档会所、图腾式的购物中心及在视觉背景下各类人等生发的扭曲人生被娓娓道来;而《天生杀人狂》里展现的美国社会景观,更像是一幅消费文化弥漫下癫狂的人类群像和图景,其中的主人公米基与自小遭遇父亲性骚扰的梅勒莉在梦境与现实中完全混淆,不断开车闯入的异域空间,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在视觉刺激的积累中完全丧失了现实边界。可以说,美国电影中的消费文化世界,在视觉想象上也几乎被一种奇特的世象、诡异的梦境、扭曲的图谱、狂欢的魔幻影像所占据。可以说,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其美学观念、艺术形态也完全为消费文化所侵袭的例证。
三、反抗策略的差异:本土化自觉的重组与现实指涉缺失的重构
经济需求和商业主体社会不断蔓延所形成的直接动力,使得消费主义呈现全球化蔓延。中美两国的电影,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电影生产观念已然成为时代主潮流,创造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宏大的消费文化景观。与此同时,部分电影人仍执着地与现代消费主义抗争,意图回归人文的、理想主义的电影传统。将电影艺术从消费文化主导的泥潭中拯救出来,成为部分中美电影人的共识。由于中美的文化形态不同,因此其抗争行为、策略本身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电影中,本土化的重新定位,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空间,开掘本土资源成为抗击消费主义浪潮的一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在国产电影实践中,盲目地追求大片效果,唯消费文化为导向,忽视微言大义与人性光辉的表现,让中国电影频频遭遇滑铁卢。这种失败本身即是消费主义观念在电影艺术中渗透的后果,导致中国电影出现了对于电影的文化语境及其理应承担的文化功能的盲视,盲目追求商业、消费的美学原则。如,2016年上映的《封神传奇》,以颇具票房号召力的李连杰、范冰冰、黄晓明、古天乐、梁家辉、文章、杨颖等明星阵容为依托,以夸张的视效为宣传点,向暑期档发起了冲击。但电影的浮夸视觉和虚无的故事内容饱受诟病,历史感和文化感的欠缺,使电影沦为“资本捞钱的游戏”。新主流的国产电影开始致力于积极承载本土文化意识形态,构建本土主流价值观的银幕表达,充分尊重本土文化和本土观者的欣赏趣味与观看经验。作为“新主流大片”出现的《集结号》,以及作为“本土类型化”获得成功的《投名状》被视为此种趋向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整合范例。此后蜂拥而至的诸如《捉妖记》《老炮儿》乃至眼下广获赞誉的《战狼2》,都是中国主旋律抑或主流电影最大化地扭转电影沦为消费文化意识形态输灌场域的努力体现,是以本土化抗击消费文化所展现的集体想象与认同机制构建。
在美国电影中,抵御消费文化冲击,重建电影艺术格局的实践,主要是依靠弥补现实指涉缺憾来完成的。一直以来,美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组建的动力之一,不仅是作为商品存在,同时也在传递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当消费文化的冲击损伤美国电影作为媒介的有效性时,回应也成为必然。在这些电影中,类型跨越、批判态度、社会问题揭示成为有效扩展电影艺术功能和影响力的主要路径,意图回归电影拟象式的具有保存个体及群体记忆的储藏库的功能,回应和修补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视觉创伤。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雨人》《纽约故事》《此刻与日出之间》等片,孜孜探索着生命和哲学的主题,张扬自我与艺术个性,极力避免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同质化文化;昆汀·塔伦蒂诺的作品诸如《低俗小说》《被解救的姜戈》等片,有意扭曲消费文化下对世界认知感受和体验方式,并做通俗化、扁平化处理,以反中心主义、反权威、反经典的逆向姿态反讽、抵制、戏拟甚至嘲弄消费文化的迷思,成就了特有的后现代风格。可以说,这些电影是美国电影人对消费主义有意识的抵抗,是对美国的民族性格的再吁求。
综上,电影作为一种话语权力的表达,不仅是一种大众消费的商品,也是传达大众文化的有效媒介。而中美电影中对消费文化的各自表述,可说是当下世界范围内带有国家、民族区域特征的电影秩序与文化诉求的自我更新。在消费文化冲击的当下,这不仅关涉电影产业的命运,也影响着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对其进行考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