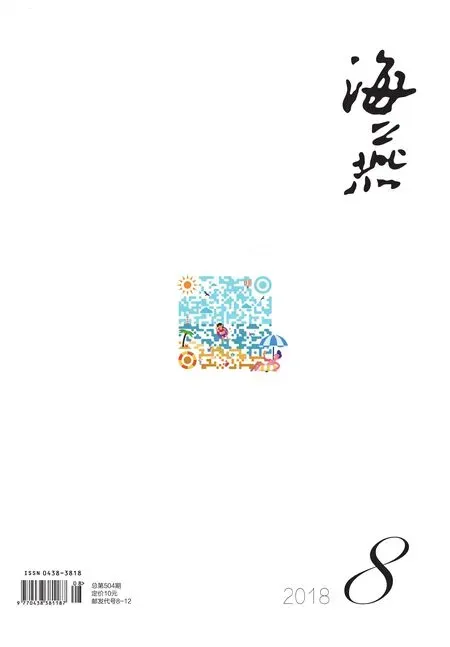凝视深渊后的被凝视
——浅析李犁评论集《烹诗》
□刘伟
福柯于1990年发表的《什么是批判》一文中如此定义“批判”:“批判是主体对权力的质疑,是主体的反抗和反思,是对主体屈从状态的解除。根本上说,批判是不被统治的艺术。”
如果从该维度来反观李犁的《烹诗》评论集,他践行的刚好是福柯所言的“不屈服统治”。
但是,李犁的目的又绝非反抗那么单纯,在本书中,他绕到评论的侧面,对诗歌(诗人)“应当如何”展开了论述,这凸显出李犁试图对诗歌“立法”的隐秘野心。
为何要对诗歌“立法”,这是个古老的命题。
借用英国社会学家边沁的“立法”概念——为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幸福——对诗歌立法,其根本目的是让不属于诗歌的作品退出诗歌,以保障诗歌的幸福。然而,梳理语言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有个奇异现象,公众很少怀疑那不是小说,那不是散文,那不是杂文。
但公众会说,那不是诗歌。
即便是哲学家海德格尔于《依本源而居》已将诗歌明确地定义为“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但是触及诗歌本质时,众人仍显露出为难的神色,只能靠比喻来说明。像诗人瓦莱里在《文艺杂谈》中将诗歌比喻为“舞蹈”,进而阐述“它是一种行为体系,其目的在于自身,它不朝向任何地方。如果说它追求某种东西,那也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目标,一种状态,一种快感,想象中的鲜花,或者某种心醉神迷,一种生活的极端,一个顶峰,一种巅峰状态。”
由此可见,诗歌作为高级的语言艺术,它缺乏明晰的规则体系,这导致大量非诗作品混进诗歌领地,并以诗歌之名义破坏着诗歌的荣誉。这让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有的诗人牺牲了道德原则和艺术标准换取廉价的掌声。
所以,为诗歌画一条线,为诗人画一条线,以保证诗歌纯度是必要而迫切的。而李犁于《烹诗》中所暗藏的,正是这种“企图”。他言语直接,有些话甚至伤害了诗人的颜面——当下诗坛的现状,首先是诗歌的村落成片成做,巍峨的大厦却少得可怜——然而,立法便如此,是场残酷的斗争,必然会在语言的群落中发生“冲突”事件。
1.形式之余李犁
既然是系统的诗歌“立法”工程,便有立法精神、立法构架、立法方法等存在。而李犁在书写这部“法律”时,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获得了不少帮助,起码在其《美学》著作中,保存了些许线索。
黑格尔说:艺术作品……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所发出的呼吁。
参看李犁的诗歌态度,他在《拓术》中这样表述:“诗歌是对我们智力与智性的开掘与提升”。
在《高度:远方就是爱就是家》中说:“远方就是诗化了的人生,把生命写成一首至真至诚的诗”。
而在《恰好与本然》则说:有种诗歌能听懂大自然的呓语,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通灵。
通过两个人的思想比对,李犁在诗歌立法的精神层面与黑格尔的观点是契合的。而在语言结构的设计上,李犁将两个命题合并到一处的做法——如诗歌-情感,诗歌-智力,诗人-生命,诗歌-自然,这种二元形式,也看出黑格尔对李犁的深刻影响。
但是,李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只是借用了二元论的形式,在内容上他需完成自己的批判事业。为此,他引进了一种工具,以保证在吸收黑格尔哲学有益部分的同时,又不被他的强大逻辑所吞并。
这就是康德的哲学方法。
2.内容之余李犁
李犁在《烹诗》中采取了多种写作形式交叉的方法,既有直接的诗歌评论,又有纪实文体的运用,既有忠告式的随笔独白,也有提醒式的杂文陈列。但无论手法如何多变,有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李犁对诗歌与诗人的立法是通过“作品-评述”这种固定路数来呈现的。
他所推荐的作品并非随意抽取,而是有着精密的设计:或代表一种风格,或代表一类主题。总而言之,李犁在对原作再度阐释时,是有计算的。
如,他在《种族地域与诗歌的原型和气质》中说:越是偏远小众的民族越接近于诗,在他们的诗里,我们常常读到一种惆怅跟悲凉。再如,他在《淬火: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中说:读这样的诗歌,很多人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这是一颗单纯的心被冷硬的工业齿轮啃噬的呼喊,是一个无产者为了谋生甘愿被资本家榨取生命的控诉。
……
这些结合着诗歌点评的个人论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别仓库,当诗人面对李犁所排列好的作品结构时,可按需支配。而这,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然物分类法。
叔本华在《康德哲学批判》中分析:康德并未发现自然物的规律,他发现的只是思维的运行规律,这就是著名的“范畴”。
康德将范畴数学化为四大类,每类下又有三项。
分别为:
量(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
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
关系(依存性、原因性、协同性)
模态(可能与不可能、存在与不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
当这些网状铺设完成后,万事万物属于哪一类,自动进行分组,然后被思维所识别、使用。
回到李犁的写作,他是以怎样的设计生成立法章程的呢?
李犁将作品分为“诗之源”、“诗之术”、“诗之味”、“诗之境”、“诗之见”五大类。而在这五类中,又分割成四至五项。同时,他将诗歌类型细化为民族诗、抒情诗、爱情诗等。
就这样,在“类—项—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引用诗人的作品做例证,完成了李犁的诗歌主张。
以民族诗为例,李犁开宗明义:“故乡和源头就是诗歌中的彼在,是人要超越此在而去的地方,这意味着起点就是终点,超越就是回归……所以,源头就是诗。
接着,李犁释义。诚如吉狄马加写的:“假如命运又让我/回到美丽的故乡/就是紧闭着双眼/我也能分清……《日子》。”
以此模式,李犁像只勤劳的蜘蛛,在编织诗歌立法体系的同时,以猎物跟猎取方式举例比较,生成清晰的、可解读的“司法”条文。让从事此类创作的诗人有了根据,找到理由。
3.立法的悖论结果
李犁是写作上的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反严肃、呆板。他在《烹诗》中用了大于诗歌但小于散文的语言形式,让语感产生了有别于通俗又近于学术的味道,使得他的主张充满了趣味。
像《伤感即美感》中说,“伤感的时候读伤感的诗歌,心灵会获得一种少有的宁静跟美感。”
在这里,他本意是要讲“语义”跟“语境”的关系,即语义在不同语境中可发生改变。但李犁并未选择学术式的表达,而以他个人的叙述习惯阐释二者关系。这种写法在书中随处可见,闪耀着灵动的光芒。
发展至此,李犁的诗歌立法已经完成。然而,对他来说,立法却派生出一个新的悖论。
当诗歌法形成后,其目的在于保护诗歌,以防止诗人与诗歌的双重泛滥。然而,立法的潜台词却是“你不能像我写的那样写”,这宣告诗人无权再去创作李犁已点评过的那些诗歌形式,否则便是重复。《烹诗》立法后的悖论便在此:尽管李犁是想保护诗歌,但在无形中,他也把诗人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他提出了更为严格创作要求,诗人、诗歌必须再上层楼。
是的,李犁是《烹诗》中的立法者,但也是肇事者。他给诗歌带来了问题。以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的话来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将凝视着你。
或许,这个命题本身更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