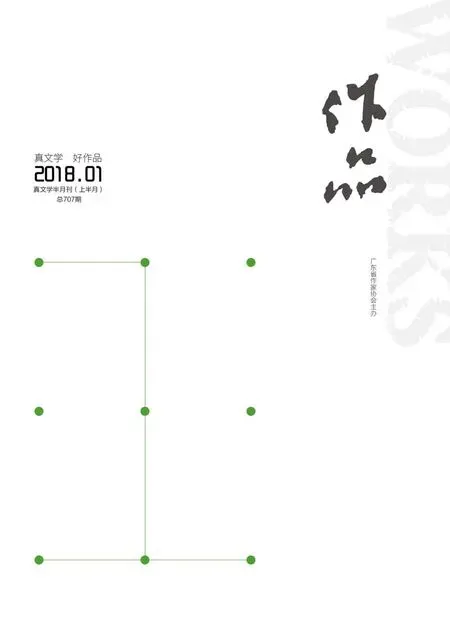梦 蝶
文/靳 朗
庄生疯了。
他疯了,他的母亲抱着他,他的妻子喊着他,他的女儿哭着他。
他疯了,在三十八岁的黄昏。
让他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女人,一个寻常到掉色的女人,潜藏在意识最深处的女人……
在一个忧郁的秋日清晨,他醒来,看到镜子中的脸,便疯了。
如果说世间众多的疯癫,都是见怪不怪的,可以堆砌一个精神病院的大楼,那么庄生驶入这片孤岛,便是始料未及的。
他是太过正常的。太过正常的,把生活与工作过成棋子。太过兢兢业业的,案头上一个错字不放过。太过老实的,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不肯说。倘若你说了,他定会谦卑和蔼地让你吞回去。他觉得这样是为你好。他脑子里充满了条条杠杠,但心是空的。
他善于湮灭自我的本性。写得不到位的一撇,像是犯了极刑。他善于一切的操作事宜。做菜,几时几分放第一克盐,水芹的茎干切成几厘米长,五花肉的厚度控制在几厘几毫,必须比火箭发射还要精准。打方向盘的姿势时刻与驾驶指南上保持高度一致。任何一次放松在他看来都是不道德的,站就必须站得笔直,坐就必须坐得端正,睡觉时每一次侧卧都是罪过,必须直挺挺地贴在床上,不然第二天早晨起来非得悔到肠子青了不可。任何涉及本能的事都使他不快,他都应该杜绝,比如少年时代初次勃起,是他记忆的污点。他曾为一个女孩儿在黑夜默默撸动包皮,过于不道德的!他的脸一下子羞红,灵魂像是上了极刑。
对于生活,他总是过于谦敬而平和,对于工作的一切不顺利,他丝毫没有怨言,即便是发奖金,他也毫不欣喜。正如他女儿的降生,他毫不欣喜,毫不悲伤,像是一切没有发生。他也抱着她那柔软的身体微笑,赞叹生命的柔软与神奇,可总像是抱着别人的女儿。这种情感正如,他结婚的那天,他看着穿着喜服的妻子,在红色的映衬下,觉得她真美,可只是觉得美,像是觉得别人的新娘很美一样。其实在结婚之前,有两个女孩儿追求他,他也觉得,她们俩都真美,都善良,都可人,都温娴,他觉得他跟她们其中一个过日子都能把日子过成那么一回事儿,可他总是不能抉择。最终帮了他大忙的,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喜欢更加温和的那一个,他就跟她结婚了。
他是最不可能疯的,也最终是疯了的那个。在三十八岁的黄昏,一个忧郁的秋日清晨,他醒来,看见镜子中的脸,便疯了。
他在镜子里看到那女孩的脸,黄皮肤,不甚优美的模样,穿着白棉布裙子,咧着嘴巴畅快地笑着。他想看清那女孩,那张脸在镜子里渐行渐远,只剩一只蝴蝶,他想握住那只蝴蝶,那蝴蝶也一下消逝了……
那张脸不仅出现在他的镜子里,还附在每个人的脸上。他看不清她的面庞,想要看清时,那张脸便消失了,只有一只蝴蝶飞越眼帘……
他行在路上,街上的人们便幻化成那张脸,咧着嘴笑着,呼喊着他的名字,待他缓过神来,便只剩下蝴蝶,幻化而去。
他呆在家里,竟看到妻子也是那张脸,甚至女儿、母亲也是。他们一贯是谦和相处的,如今这平衡关系算是被打破了。他的脑子里一团糨糊,除了恐惧与晕眩,别无他感。甚至是对他的女儿,虽然不甚欢喜,却还是待她温和的,这下子,便对她大吼起来,“走啊走!”“滚!”……甚至有关这个“蝶”的字眼,都令他发狂。一日,他伏在写字桌上,一丝不苟校对文稿,看到“蝶”这个字眼,便恐惧了起来,“走啊走!”,“滚!”“快滚!”……不幸对面走来的是他的总编,对他说了一声“滚!”,他便失了业。
他以往大概从未想到,会有这么一日。他虽永远都是个小编辑,但是由于老实与谦和,几番裁员过去,出版社还是把他留了下来。事实上,这件事已经传遍了整层办公楼,大家都谈论着,最不可能走的人如今被开走了。
令他疯癫的那名女子,叫作伍蝶,同她羸弱的名字一样,她只是人海过于微渺的一只。就像是庄生的疯癫,疯不疯癫,其实是一样的,像生死,一样飘忽。终究是芸芸众生中过于微渺的一分子。
小说的女主角似乎总要有点过人的能耐,而使我们这个故事得以发生的这个女孩儿,实在是平凡极了,如果硬要找到某点过人的品质,那便是这点平凡。平凡的极致就成了特色。
关于伍蝶的记忆,其实潜藏在庄生的意识深处,在厚重而褶皱的大脑皮层里,有这么一块地方,神经是如此的活跃,不过不久便被遮掩了起来,沉寂在意识的深处。
那是属于青春的地带,被文明所遮掩的隐秘地带,在青春的芳华里,禁果般绽放。
事实上,十六岁的庄生显然有这么一种偷尝禁果的冲动。像是他每天早晨都要偷偷剃去的胡须,这冲动最终被压制、沉寂。最终成为一个如此沉寂的人,不得不说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如同每天早晨压抑下去的勃起一样,初见伍蝶的时刻,他也是如此归为平静。
那是在北方夏日的一个傍晚。河岸边。太阳微染红鬓。
庄生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每天下午,他都要来岸边微坐,吹吹凉风。这一日也一样。
只不过,与往日些微不同的是,这日来了一个女孩儿。那女孩便是伍蝶。那日,伍蝶穿着一袭白裙、花青色布鞋,在河岸散步。白色的裙裾衬出她那亚洲人健硕而硬朗的黄皮肤,漆黑眼眸比棋子还要精神。比起同时期的女孩来,她算是发育得比较好的。虽不甚细挑,但曲线还是能够勾勒得出来的。
庄生转过脸来,看到她黄皮肤的脸,漆黑的眼眸,咧着牙的笑,便停不下神来了。直至焦点凝聚在她稚嫩的微微颤抖的胸部,脸上的红晕便再也遮盖不住了。
那天晚上,他多次梦起她那灿烂纯净的笑,以及微微颤抖的青春的胸部。他在梦中痴傻地笑着,透过月光,还能看到他绯红的双颊。在那尘封青春的夜晚,他不止一次地梦遗。
他接连几日地在岸边等候那个女孩。
他想着,自己就静静地看着。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女孩不停歇地出现,他都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的表情是如此平静,内心是如此的波澜。他白天极力压制的,在夜晚倍加释放,那女孩不停地造访他的幻梦,层层叠叠的青春的液体在夜晚释放。只有在月光下,倍加压抑的才得以释放得如此自然。似乎只有在梦中,他才有权追求那真切的生命。
那女孩游走在河边的身体在他脑海层层叠叠地浮现着,像是软绵绵的层云袭击他的梦魇,那青春的矫健的亚洲铜般的胴体,在梦魇中轮回。在白日压抑下去的冲动或是渴望,在梦魇中是那么真切,仿佛日暮中那近在咫尺的距离永远消失了。在梦魇中他再也不是祟祟的远观者,而是真真切切的肉体,黄泥般的肉体。在层层叠叠的梦中,他是大地的孩子,重回孩童时代。那亚洲铜般的肉体,其致命的吸引力,不是在白日绽放,而是在这月光不垂的夏夜,像肿胀的青春河水一样迸裂,时有洪水决堤的危险。可那堤坝,或者说苍白的近似于道德的东西,始终不开闸门。待到黑夜逝去,庄生照旧穿上板板正正的衣服,人流如棋子,他是万千黑点中寻常的一只。昨夜梦到什么,跟新的一天无关,那样层层叠叠的肉体的愿望,在白日的太阳下,连作祟的动机都没有。
一日一日,那愿望在白日与黑夜间挣扎、上演。
在梦中,伍蝶那亚洲铜般的胴体是那么真切,而在白日,即便是日暮时分,那近在咫尺的距离像是个异度空间,他只能是个祟祟的远观者。对于那黄皮肤的胴体,他永远都是远观者。这愿望在生理上是如此的急促、自然,急速的呼吸、肿胀的眼睛以及蠢蠢欲动的下体。而那思维上的闸门,却是如此的稳定、恒常。那青春的河水沸腾呼啸,那沉重的闸门铅球一般沉重,横亘在那儿。
那涌动的欲望如同雨季的到来,在酣畅淋漓的夏夜大雨中,终于穿破陈旧的闸门,蔓延到凝滞的白日里。那是早八点的书页,生物课本上,他翻动到女人的胴体。那属于黑夜的,亚洲铜的梦魇,漫过闸门,降临白日。她那健康的黄皮肤,在日暮的霞光中是如此的诱人,那稚嫩的曲线在日暮下与河岸上的水草皴擦。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是河岸边一丛水草,与那青春的胴体蹉跎!日暮下骄人的影,打在岸边的野草上,也打在他的下体上。那青春的愿望迭动,这是清晨八点十五分的中学课堂,而他沉入日暮的梦。
只有在梦中,生存才是如此真切,他再次堕入日暮的迷梦。“伍蝶,伍蝶,伍蝶……”,他甜蜜而急促地呼喊着。一阵讥笑使他回到白日的世界,端正坐姿,又是机械而正常的一天。他大概没有意识到,他将以此坐姿度过一生,直到驶入幽深而隐秘的异轨。
在接下来的日月里,这女子青春的胴体在他脑海里层层叠叠地浮现。在青春的梦魇里,在白日的打盹中,在司空见惯的一切中,他都能透过生活的纷尘,看到伍蝶那亚洲铜般的胴体,微微颤抖的胸部,稚嫩的曲线,笑咧咧的面庞……他的生活已经被这幻想占领!
他日复一日地去那河岸边等待,像是早已约定好的一样,那女子准时出现。她在河岸边漫步,在日光下舞动白裙,在火红的霞光中咧着嘴笑着……这胴体的诱惑力是那么大,似青春的河水冲破堤坝,头颅里的网终究束不住他。他实在难以抑制那幽深而隐秘的冲动了,他扔掉书包,把自行车摊在河岸边,小兽一般跑过去,想要抱住那女孩,那青春的胴体。而他跑到河岸边,站在那女孩面前。她对着他寂寂地笑着,葡萄般的眼珠亮晶晶地映衬在他的眼眸里。那闸门瞬间上升,他觉得自己是多么地罪恶,那美好的欲望是多么地赤裸与苍白。过于不道德!他在心里呐喊着。所有的畅快都是罪过,人生来就应该学会克制。作为社会人的他,一下子疲软了下来,像是一只衰颓的兔子,寂寂地退了回去。
夏夜是幽深而静谧的,只有夜晚,那些幽深而隐秘的愿望才得以像泉水一般汩汩流淌,穿越沉重的闸门,在绵软的云层中稳稳地着陆。他再次堕入迷梦。在梦中,他紧紧地抱住那亚洲铜般的胴体,只有在夜晚,活着才是这么真实。
而醒来的时刻,人就必须进入层层叠叠一望无际的网。那些幽深而隐秘的愿望注定成为孤独的记忆,压箱底的愿望,沉积在意识的最底层。即便是波澜迭起,在层层淘洗下,也最终化为一潭死水。
前一日的失败尚未阻挠他对鲜美胴体的渴望,那白玉兰般纯洁的胴体,那百合花般含苞的纯净的隐秘情感。如同他日渐坚实的臂膀,这隐秘的欲望流淌着生命矫健的芳香。
这一日,他照旧来到岸边,风在晚霞下是如此的温润,流淌在他那日渐坚实的身体上。这青春的渴望不再是夜幕下下意识的呼喊,而是变成一种愈加坚实的欲望,他想要抱住那黄泥般的胴体,这欲望是如此的坚实。
而梦,总是太过轻盈……太过轻盈的,来不及触碰就要碎裂。
那女子朝他走来,他铆足了勇气,要抱住这青春的胴体时,这女子朝他笑了笑。那笑容虽不甚优美,却是淳朴而自然的,如同她亚洲铜般的胴体,是一种原始的、青春的生命力与美好,沾染着黄土的气息。他渴望留住这笑容,想要摸一摸这日暮下绯红的脸蛋儿。那女子一如既往地笑着,随即,幻化成一只白蝶,遥遥地去了,消失在水天之际。
日后,他依旧做着那些层层叠叠的梦,有关伍蝶的记忆,最终幻化成一个个迷梦在梦魇中复现。而随着时间的蹉跎,渐渐地,模糊、模糊、模糊……直到他三十八岁的黄昏,堕入异轨的疯癫,那潜藏在意识深处,在大脑皮层中极为蜿蜒的,残旧的青春记忆才得以复苏、爆发……
疯癫是世界的真相!那些压抑的、隐秘的、藏匿于意识的幽深的巷道里的、不见天日的、蠢蠢欲动的,终将一夕爆发,披着疯癫的壳,捣毁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些镇压千年的非理性,终将一夕爆发。而庄生,不过是如此浪潮中极为微渺的一只,不足一粒沙沉重。
那事关少年时代的记忆,在他之后的人生旅程中时有浮现,但日益被层层叠叠的新生记忆遮盖。偶尔也显现那张脸,或是那亚洲铜般的胴体的某一个部位,稚嫩双峰中的一只,微微咧起的笑唇,随之日渐模糊,被如流涌来的校对工作冲刷,被白菜蒜头的价格湮灭,被女儿的啼哭声与母亲脆弱的坐骨神经抢风头……这过程发生得缓慢而和平,极为合理,任时间宰割,不知过了多少年,也不知曾经发生什么事……终究渐行渐远,这年少的愿望,注定穴居在那幽深的意识巷道里,不见天日。
就在那三十八岁黄昏的前夕,那个秋日清晨前不久的日子里,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再次堕入海水,静静地,静静地下陷,毫不恐惧,毫不挣扎,回归阿诗玛的怀抱。他觉得那一刻真是幸福!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淌着。其实他每天都在做这一件事,只是他的时间不是自己的,是被雇佣的,被谋杀的,分给金钱、分给房屋、分给街道、分给计程车司机、分给母亲、分给女儿、分给妻子……他的时间不是自己的。如同十六岁时的蠢蠢欲动的青春愿望被这苍白的头脑拒绝,他的身体再也不是自己的了,是被雇佣的校书郎、被雇佣的儿子、被雇佣的父亲、被雇佣的丈夫……他看到自己被这躯壳吞噬,像是平静地堕入海水,毫不挣扎,毫不痛苦……
梦醒的时刻,他浑然失去力量,冰冷的汗水简直快让他的最末端的毛细血管凝固!他竟相信了世界上果真有“鬼压床”这一说。这世界上果真有如此沉重的鬼,让人窒息,噬人灵魂,不图尸身,只图灵气。只不过这鬼是分身的鬼,他是写字台旁的印刷机,是女儿的学杂费,是沉重而透明的信用卡,是妻子打了折中折的过季款……这鬼还无影无踪,在他十六岁时拒绝那青春的愿望时这鬼首现真身,在他拒绝妻子午夜时分的呻吟时这鬼隐隐作祟,在他高歌某某万岁时这鬼微启丹唇……
他的生活被这鬼占领了,这鬼是母亲、妻子,也是女儿,还是把他一脚蹬出出版社的总编……一切一切!十字路口上形形色色的人流。他实在难以想象,少年时代健美的青春愿望如今被这苍白的生活压制。若无疯癫,他便一切照旧,在这充满鬼的世界里苟延残喘。的确,疯癫是可怕的,任何背离常轨的事物或是行径都必然陷入群体的惩罚,他以前是如此清楚这一点,如今更是清明。在疯癫还未造访他的生命之前,他是一切既定规则忠诚的遵循者,如今的疯癫倒是使他看透了这一切,他曾经唯恐打破的,如今是多么想从这层层叠叠的逆网中探出头去。他觉得不是他疯了,而是人们疯了。而在这集体性疯癫中,人们又是无辜的,这背后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力量,而他搞不清。只是知道,在集体性疯癫中的清醒,本是就是一种疯狂。
不久之后的某个秋日清晨,他看到那张亚洲铜般的脸庞,便堕入了永恒的梦魇……
在梦里,他再次看到了那张脸。那张脸如此真实,它以幻想附着在每个人的脸庞上,却比那一个个苍白的胴体真实得多。
他行在路上,那张脸附着在形形色色的人流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颓败而苍白的胴体跟那张鲜活的脸形成鲜明而滑稽的对比。他们的身体是僵硬而机械的,关节是麻木而冷却的,双脚像是上了发条,好像不是自己的脚一样。而那张亚洲铜般的脸却是黄土的色彩,它不优美却笑咧咧的是苇草一般倔强的生命力。只不过,那张脸附着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他们用着那颓败的声音呼喊着他,像是梦魇一般轮回,随后又幻化成蝴蝶,翩然而去,只留下一具具颓败的躯壳。他们在小区超市前的小径上,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在老城区古旧的巷道里……那层层叠叠的脸幻化成蝴蝶,翩然而去,层层叠叠的声音呼喊着,“庄生,庄生,庄生……”,随即湮灭在人海中,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人们该买东西的买东西,该过马路的过马路,古城区的巷道里叶子一片片落,像是许多年前一样,也像许多年后一样。
而这人海中有一张脸,在那层层叠叠的假面中,保持着其一贯的姿态。那张亚洲铜般的脸在每个人身上幻化成蝴蝶,唯独在那人身上失效……
那便是伍蝶的脸,若干年后的伍蝶,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的伍蝶,体态臃肿的伍蝶……她的脸一如最初的模样,鼻子、眼睛、嘴巴、眉毛,一贯的黄皮肤,一如最初的模样,不过却像个被岁月蒸发掉水分的苹果,层层叠叠的皱纹被岁月深深地卡进肉里。那曾跃动着的青春的胴体,如今如同她身上挂着的那两只干瘪的乳房,像是抽瘪了的水袋,低沉地垂在那儿。她那漆黑而温润的秀发,如今有些苍白,几根白头发横在头顶上,发梢也开始枯萎,像是干燥的树根。
她在人行道的另一头,双手推动着一辆陈旧的自行车,在人海中蹒跚着。那车筐里的重量,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使她推得很吃力。那筐子里装的什么呢?我们看看,其实也不是什么格外沉重的东西,无非是些西红柿、卷心菜、胡萝卜之类的瓜果。而它们像是碎石一样,砸向她……那双漆黑的玻璃弹珠般的眼,如今已然干涸、枯涩,在赶鸭子上架的生活面前丧失了它的最后一丝光芒。她的双脚像是别人的,在拥挤的人流中机械地拨动着,也不管绿灯亮没亮,只要人群向前涌动,她的双脚就随之前移。
那张脸本是鲜活的,如今渐渐枯萎、枯萎,庄生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狠狠地擦亮了眼睛。那曾经鲜活的胴体如今像是一个肿胀而干瘪的水袋,这过程占时十余年之久,而在庄生看来,这过程却是一瞬之间的事情,甚至不如化蝶的那一瞬之长。我们漂浮在人生的沧海,不曾以一瞬。而寄生在世间上微如浮萍的人们,最朴实最广大的愿望不过是活得快乐些,如今却成了干涸的尸槁,行尸走肉地生活着。庄生跟着她操动着机械而颓圮的步伐,走近,走近……
穿过一条条狭窄而颓圮的街道,庄生跟着伍蝶走进她的家。与其说是家,不如仅仅说是住所,那是北方常见的四合院,不合时宜地伫立在二十一世纪的老城区里。唯一一点阳光,也被半里之外的摩天大楼遮蔽了,整个屋子在阴影中苟延残喘,似乎它也知道,不久之后,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之后高楼迭起。
屋子里坐着伍蝶的男人,红棕色的皮肤,挺着个圆圆的将军肚,摇着太师椅,哼着小曲儿。本来不错的心情,看到伍蝶似乎变得不好了,用北方男人一向厚重的嗓门不耐烦地叫喊着“买个菜买到天黑,孩子都饿得哇哇哭,什么娘们!”伍蝶没有搭理他,瑟缩着走进屋子里,抱起摇篮里的婴儿,掀开衣服,开始喂奶。她喂着自己的孩子像是喂着别人的孩子,听着男人的骂好像觉得在骂着别人。把婴儿喂饱之后,她像是装包装袋一样把孩子裹在小包被里,动作迅速、麻利、整整齐齐,像是她在车间当包装工的时候,给一个个啤酒瓶贴标签一样,面无表情、态度严谨,把他放在摇篮里,似乎感觉像是解决一条流水线。
一想到那青春的胴体就在这婴儿的一次次吸食中奔向坍塌,庄生便踉跄了一下,一种不知名的痛苦渗入心肺,随后蔓及全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在痛苦地颤抖。他从未想到,他的旧梦竟如此碎裂。对于少年时代的怯弱他毫不遗憾,而今看到伍蝶浮肿而机械的躯体,他倒是忏悔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凶手,杀了自己,也杀了伍蝶。她像是一只坠落的蝴蝶,堕入生活的泥沼里,而他明明可以伸出手挽起她,却跟众人一样,成了无名的凶手。“我不过是疯了的众人而已!无能为力”,他想着……
这时,伍蝶的大女儿跑来,拿出作业本让她签字,她大字不看一个,就在最后签上了“伍蝶”。写的一笔一画,简直像是两个方块儿。她抚了抚额头,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便想起了前天买的馄饨皮儿,再不吃就坏了,便跑到厨房里包馄饨儿。他的脑海中那青春的胴体,如今却像是被肢解一般,像玩偶一样被生活的提线控制着,像是一个淌着血的机器人。那龇着牙的、不甚优美的笑脸,如今成了两道凹陷的法令纹,深深地卡在面部僵持的肌肉上,不合时宜地停留在双颊上,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这个人,曾畅快地笑过。
她的丈夫坐太师椅上喝了点小酒,便想起来今天在单位时,领导不明就里地骂了他一通儿,便不明就里地气了起来。在单位自是不敢生气的,跟孩子们生气还怕把孩子打坏了,便开始骂起老婆来。骂的理由也很简单,别家买两块五一斤的西红柿她买的三块钱一斤,昨天买的生菜没有吃今天蔫了……总之想骂总有理由。仅仅是骂还不够撒气的,还得再来上几拳几脚,便朝着她的右腿狠狠地踹了几脚,这才满意地去了。她倒在地上又起来,把几滴泪擦干净,便回到厨房里煮馄饨儿去了……
他觉得这一切似乎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打骂她的那个男人的错,似乎一切的背后有股神秘的力量、隐秘的凶手在,这凶手的温和之中掺杂着一股邪气,让一切的谋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让那曾经鲜活、健美的生命如今坍塌在颓圮而有序的生活面前,让曾笑咧咧的脸颊如今面如死尸。他的脑袋昏涨,搞不清楚终究是一股什么力量,他觉得眼前的一切越发模糊、模糊,他听到有一阵阵的蝴蝶挥动着翅膀,朝他耳际扑朔而来……
他迅疾走到她面前,抚了抚她横皱迭起的脸颊,她那衰颓的面颊与凹陷的双眼让他不寒而栗。
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似乎要将他带走,便急忙问道:“你过得好吗?”
“没什么好与不好”,她说着,双眼盯着锅里打着转的馄饨。
“你的腿还疼吗?”
“疼不疼我也觉不出来。”
……
庄生觉得这下他的梦真的碎了。那鲜活的亚洲铜般的胴体在此碎裂,血流满地。
年少时期的愿望,并不以所谓婚姻的坟墓而终结,而是,你想在这个世间发狂地爱着,那鲜活的胴体却被生活活剥了。而这生活本身应该是健美而自然的,像是年少时期的愿望,初次勃动的下体,睡梦里流溢的爱欲的体液......而所有的人却告诉他,他疯了,在三十八岁的黄昏。他却觉得应该反过来,疯了的是人们。而究竟是为什么,他不知道。耳畔的群蝶越舞越响,他昏厥了过去……
翌日,他醒在秋日的清晨里。那张脸在镜子里朝他笑着,那笑容越是鲜活而明媚,他的脑海里就越是浮现那张颓圮而枯黄的脸,他就觉得越是可怕。在那镜子里,他同样看到十六岁时的自己,渐渐变得干瘪、枯黄,没有一滴血色。他看着自己的脸也如此化作蝴蝶朝远处飞去了,不觉陷入一种莫大的惊慌与恐惧中,瑟瑟发抖。
他的母亲抱着他,妻子喊着他,女儿哭着他。哀悼他的疯癫像是哀悼他的生命。他只觉得,像是三只蝴蝶在“嗡,嗡,嗡……”。
所有的人都说他疯了,他只知道自己没有疯。他走在街道上,看着人们一张张的脸化蝶而去,令他哭笑不得。他坐在工作台前,一个个文字扑面而来,像是蝴蝶挤满电脑屏幕……他在幻梦的世界不可自拔。
而梦早已被击碎,那青春的胴体坠落在地,像是他的心,堕入迷沼。
那张脸附着在母亲、妻子甚至女儿的脸上,笑着,喊着,唤着他的名字。
那笑容在女儿身上格外鲜活、健美,他抱起女儿稚嫩的脸,抚摸、亲吻,想要圆那破裂的梦,却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张脸化蝶而去。在那张脸之下,潜藏着一张颓圮而枯黄的脸,刺入他的夙梦。
那层层叠叠的青春的胴体在他脑海中蜂起蝶涌,随即坠落、破碎,那碎片旋即化茧成蝶,朝窗外飞去,他想追,却赶不上。
这下,他想起伍蝶那肿成水袋般的胴体,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像是十六岁的时候,他看着她的脸,一股隐秘的道德湮灭了他的旧梦。而如今这股力量,比那刺骨的道德还要隐秘,他愈加无可奈何。
他看到妻子也曾有那样花一样蓬勃的笑颜,像是母亲当年,像是河岸边日暮时分不甚优美的微笑,如今却行尸走肉般地在生活的囹圄里行尸走肉般延续着苟延残喘的生命,而他也曾如她们一样。他紧紧地抱住他的妻子,在这光怪陆离的二十一世纪痛哭失声……
而他的妻子,终究承受不住这痛苦,堕窗而去。
他想要伸手挽住他,而她如同蝴蝶般飞走了。
他喊着“蝴蝶蝴蝶飞走了”,狂笑,大哭,弃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