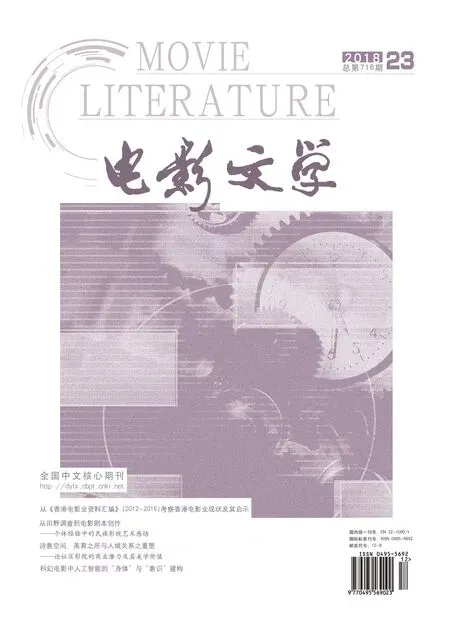抗日题材电视剧抗日主体构建的思考
李金兆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在近年来抗日题材电视剧的主流叙事中,共产党人的抗日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小人物或草根成长为共产党抗日英雄的影像构建更是迎合了消费主义语境下人们娱乐化的审美需求。以小人物和草根为代表的民间抗战主体在受众的接受和认可上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其鲜明而富有张力的人物个性能够吸引受众的审美惊奇和欣赏偏爱。
这些富有原生态色彩的民间抗日主体是千千万万平凡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侵略时的自发抗战和精神成长的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突出抗日主体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在一方面弱化和嘲讽了具有坚定革命意志和高效行动能力的共产党人的抗日实力;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草莽习性和遗风陋俗不可避免地在这些草根和小人物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则会无意识地将其理解成共产党人的共有品质,最后往往会导致这些所谓的“江湖匪气”取代了应有的革命正气,进而偏颇地将共产党人的出身和习性狭隘地定位在了“草莽”或“土匪”等负面的概念上,这最终只能消解共产党人的抗日实力,并混淆人们对于共产党抗日的认识和理解。
尽管此类剧作表面上强调的是平凡个体的蜕变与成长,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可和接受,但其缺乏对信仰、意志和战斗能力的拔高和升华有可能使得主旋律的意义产生动摇。因此,以小人物和草根为表现主体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显性层面上表达了共产党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来源和平凡个体对于先进信仰和立场的认可,但无法避免隐性层面上对于共产党人出身背景、抗日能力和抗日实力的怀疑。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另辟蹊径地将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抗日主体聚焦在了女性身上,这是对以往男性意识当道的抗战剧的题材创新。剧中王大花在精神和战斗能力上的成长过程是编剧集中刻画与书写的对象,王大花如何从一个经营鱼锅饼子店的老板娘蜕变为具有强大抗日精神和坚定共产主义革命信仰的斗士是剧作想要突出的主题,由此必须放大王大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却使得编剧在无意识中夸大了王大花的战斗能力,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消解了以夏家河为代表的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的抗战实力,使得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人的抗日实力产生怀疑。
剧作的前10集都聚焦在王大花和共产党对于电台的争夺上,两方无休无止的纠缠让受众直观地感受到了王大花这样一个见识浅薄的农村妇女是如何把一群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人耍得团团转的。夏家河、老韩和小货郎三个共产党人都对付不了一个王大花,最后还导致了与日本人的正面交火和无谓牺牲。第八集刘署长和小警察的一番对话说出了王大花行为的不合逻辑性:
小警察:咱们、共产党、日本人都让她给耍了。
刘署长: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让我越琢磨越糊涂了,你说她有电台吧,她居然不是共产党,还抱着一个随时会要命的炸弹不出手,为什么呢?你说她没电台吧,可共产党还老打她的主意。要么她就是个大傻瓜,要么大智若愚。
王大花拿着电台不放让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受到了这是由于一个农村妇女的浅薄无知而导致的闹剧,但最终被戏谑的对象却指向了共产党人。面对这么重要的一部电台,有着成熟战斗经验的共产党人根本不会和王大花讨价还价,也不会为此一再退让而最终导致时间和人力的损失。这前10集在对于电台争夺的描写中透露出的王大花的无知是正常现象,毕竟她对于电台的重要性和革命的意义没有多少直观清晰的了解,但是共产党人面对王大花无理取闹时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却是对其自身抗日实力的一种消减和否定。
此外,王大花与日本人青木正二以及大连首富邵登年的人际关系让共产党将所有重要的任务都压在了王大花身上,而受众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连党都还没有入、缺乏革命认知和革命斗争经验的普通农村妇女来说,共产党放心将这些重要的任务交到她手上吗?每次被送上任务前线的都是王大花而非共产党人夏家河或老韩,而观众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夏家河一次次地利用王大花对他的感情让其为组织完成任务的心理动机,但一个男人怎么会多次将自己心爱的女人送上革命和危险的风口浪尖呢?
所以在剧中,每次共产党人没了主意,都会第一个想到王大花,尽管夏家河每次都以危险或不合适为借口进行搪塞,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王大花一个人去完成任务。由此,两个疑问接踵而来:一是每次一有重要任务,组织上真的会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使命交到一个根本没有入党、没有斗争经验的王大花身上吗;二是大连的共产党仿佛就是王大花一个人撑起来的,王大花承担和包办了共产党的所有重任。这在夸大王大花战斗能力的同时并没有升华共产党的抗日价值,共产党甚至已经完全沦为王大花通过抗日展现自身卓越能力的附庸和陪衬。共产党本身的抗日价值和抗日能力何在?受众在剧中找不到答案。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为了突出王大花在革命中的成长和蜕变,却无意识地在隐性层面弱化了作为抗日主体的共产党的实力和价值,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形象塑造和人物关系与《亮剑》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刻画的都是一个有着江湖匪气、草莽出身和性格缺陷的小人物,同样都建构了国共在抗日中既对立又合作的人物关系。这使得《永不磨灭的番号》也和《亮剑》存在着一样的问题,即粗陋短浅,具有江湖匪气的草根英雄是否能跟共产党的形象画上等号?
《永不磨灭的番号》将抗日力量的主体移植到了民间,关注了游击队伍这只被边缘化了的草根力量。既然其中的抗日主体出身草根,那么他们必不可少地带有草根的习气特质,甚至是一些具有负面价值的性格特征。其中的主人公李大本事是一个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古灵精怪的游侠形象,尽管他以前曾经有一段红军经历,但是长期被放逐乡间村野的经历也让江湖习气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李大本事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将自己自比刘备,将其他的兄弟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总能够把大家收服得服服帖帖。李大本事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他油嘴滑舌的本领常常能够将死的说成活的,剧中第四集的一段旁白解释了李大本事的这种独特本领:
旁白:就这么着,所有人又被李大本事的一通白话给说服了。这家伙似乎天生有种讨人喜欢的本事,不管犯下什么样的过错,总能让你很快原谅他。
李大本事带领的这些弟兄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了这样的油腔滑调和民间陋习,后来这支队伍和民兵被收编进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中,那这是否能够解释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力量的构成正是来自这样一支简陋的民间游击队伍呢?共产党的抗战实力是否仅仅是游击战这么简单?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像民间的那么简陋?同时,来自民间的性格缺陷会不会在共产党战士们的身上留下痕迹?从宏观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在初期是处在边缘化状态的,尤其是军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兵力、物资、番号等都十分有限;在微观上,共产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人员杂、装备差、松散混乱,状况更加边缘。尽管《永不磨灭的番号》显在层面想要表达的是一支地方抗战游击队伍对于身份和名号的诉求与向往,但是其隐性层面最后将这支队伍划归到共产党的队伍和阵营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党与这支队伍画上了等号,这支队伍中存在的武器战略和人物脾性等特点自然也会被当作共产党的一部分进行认知和接受。而对于李大本事这支来自民间草根的县武装大队的描写在隐性层面上揭示出了当时八路军地方武装的真实境况。
《永不磨灭的番号》表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身份诉求,李大本事多次在共产党领导面前要求给自己的县武装大队一个正经的番号和名分,这是剧作想集中刻画的一个主题。但是李大本事的虚荣心却不时暴露了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李大本事表面上参加抗战是为了打鬼子,实际上是封建思想在他的脑海中作祟,抗战的更多目的是占山为王,壮大自己的队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一个正经的番号。
主力意识和名号意识在李大本事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渴望得到他人尤其是共产党八路军内部对于自身的认同和接受,李大本事在打响队伍名号的时候总是想要打出和打响自己的名字而忽略了队伍,这暴露了他骨子里的自私和虚荣心。包括李大本事的队伍和孙成海领导的九路军在武义县对于谁是抗日主力的争夺,让两支队伍的目标已经不是抗日这么简单,抗日已然沦为他们占山为王和打响名号的手段。抗日主体由于自身目的不纯而弱化了抗日的价值,李大本事队伍和九路军的争斗和帮派斗争或土匪打架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尽管李大本事的队伍已经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和弊病,但是八路军指挥部的领导们还是经常仰仗这支边缘部队进行战斗。剧中刻画得以谢二狗为代表的八路军内部的主力部队还不如李大本事这支简陋的民兵武装有用,突出和褒扬李大本事队伍的同时,弱化和质疑的是共产党作为抗日主体的实力——难道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不如一支民兵队伍吗?正如第20集中司令员在表扬李大本事部队的时候怀疑的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实力:
司令:政委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处在敌人的咽喉位置,那比其他部队凶险得多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几个胜仗,牵制住敌人,就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也不一定能干得这么漂亮吧。
因此,尽管《永不磨灭的番号》试图在显性层面上突出一支民间游击队伍在抗日斗争中的蜕变与成长,但也正是由于刻画主体的局限与桎梏,使得全剧让抗日本身成为李大本事获取身份认同的手段,抗日的地位和重要性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受众对于李大本事的理解不是出于其在抗日上的英勇卓绝,而更多是其如何带领一群草根壮大和成长的艰辛历程,对于李大本事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也在隐性层面无意识地展现了当时八路军抗日的驳杂真实境况。
抗战题材电视剧在塑造抗战主体时必须时刻秉持谨慎的态度和意识,而不能让抗日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让位和消减于小人物和草根抗日的游戏化和娱乐化叙事中。小人物和草根的身份刻画与抗战行为尽管拥有极强的大众审美接近性,但其并非成熟理智的抗日主体,小人物和草根在抗战中的成长和蜕变更多应该由先进而成熟的抗日主体来对其进行引导,而不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存在价值便主观夸大其在抗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用其替代先进成熟的抗日力量或弱化这些先进主体在抗日中的价值,这样可能会把抗战剧的意识形态功能带入一种危险的境地,从而使得受众对于抗日主体的理解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与歧义。
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意识形态化育功能毋庸置疑,因其是主旋律和政治表达的重要载体,抗战剧文本中的抗战主体构建必须时刻心怀谨慎。近年来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大众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文化语境中出现了许多“去政治化”的倾向,剧作对小人物和草根出身的抗日英雄所给予的人性关照,以及文本中所渗透和包含的现代价值在获得受众审美接近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政治意义与功能属性。
在抗日主体的构建中,小人物或草根成长为共产党抗日英雄的影像构建不过是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语境下人们娱乐化的审美需求。以小人物和草根为表现主体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显性层面上表达了共产党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来源和平凡个体对于先进信仰和立场的认可,却无法避免隐性层面上对于共产党人出身背景、抗日能力和抗日实力的怀疑。传奇化、浪漫化和戏说化的创作特点不应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宣教功能的抗战剧的创作主流,通过抗日题材电视剧获得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深刻认知并启发受众对于当前政治选择的正确理解,才是抗日题材电视剧意义生发和主体构建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