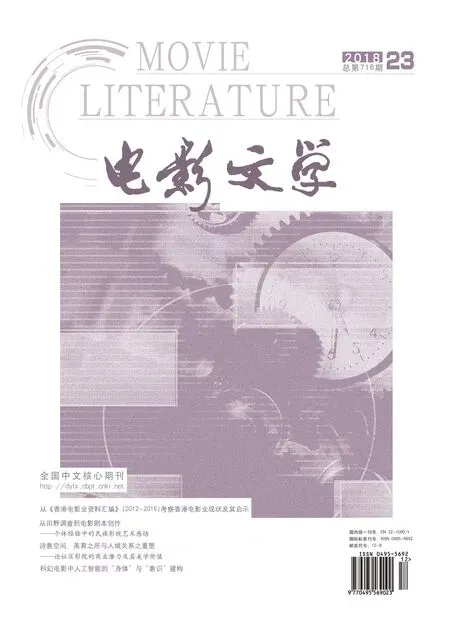从田野调查到电影剧本创作
——个体经验中的民族影视艺术感悟
颜 亮 坚 斌
(1.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2000;2.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田野调查与剧本创作,“一是已经空间化的空间,二是正在空间化的空间”在现实界域进行思想艺术空间的生成,两个空间、两种述行(象征物/符号),就在同一黏着性的思维平面上产生了视界融合,成为一种“本体上的平等”艺术,也有了“变动不居的复杂互联性”。从2015年伊始,笔者数次进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拖拉村,从一个陌生化的个体到融入当地藏族家庭,多元化的视角,使得本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观察和思考田野调查点所遇见的人与物。在完成田野点学术性调查研究的同时,创作完成了取材于拖拉村的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
一、剧本概述
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设置时长90分钟,人物设置为江小北:20多岁,民族学在读研究生,由于一本魂牵梦绕的西藏著作和调研项目前往德钦进行田野调研。古江丽:20多岁,哥哥在多年前突然失踪,一个一直在寻找哥哥的北京女孩儿。疯行修行者:一个迁识转世的活佛。旺杰大喇嘛:拖拉寺最年长的僧人。喇嘛格玛具米:拖拉寺寺管会主任。喇嘛达瓦次里:拖拉寺喇嘛。喇嘛扎西江初:拖拉寺喇嘛。喇嘛安吾格茸:拖拉寺喇嘛。嘎玛:德钦人,跑旅游的个体户。贡嘎:德钦人,面包车司机。培初:拖拉村村长。永初拉姆:拖拉村妇联主任。故事场景主体为拖拉村,故事为复线叙述,存在悬念与情境描写,语言对白以云南方言、藏语为主。
故事讲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灵童转世的活佛,一个汉地出生接受迁识重生的仁波切(意指“珍宝”或“宝贝”,是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最亲切、最崇敬的尊称),一个举止癫痴疯行的成就者,这一切看似不可能,却真实地存在于拖拉村——一个供养酒神护法的高山藏族村落。主人公江小北的田野之行,充满了光怪陆离,却又经历了人世的悲欢离合。拖拉村人嗜酒如命,只因为追随卡瓦格博东征西战的狮子三兄弟,幻化成了拖拉的护法神,演绎着美丽动人又不失戏谑的传说,也塑造了拖拉人直爽淳朴的性格以及种类丰富的酿酒工艺。酒与酒神成了拖拉人脱不开的干系,成为女人放纵自我的斗酒节,也成了一代拖拉寺高僧旺杰与众多藏族师兄弟顿悟的根本之源。主人公江小北的考察,横生枝节,遭遇古怪的藏族葬礼、惊心动魄的驱魔仪式。在一场拖拉寺盛大的法会中,疯行成就者的妹妹千里寻亲,找到兄长,完成心愿,而主人公也在田野地拖拉,找到了情感的归宿以及精神的寄托。
二、剧本元素与生态媒介
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强调主体是“人”,所谓环境系统是人类生存空间环境下的体系,所包含的动态文化艺术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外在力的影响,从而促使环境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通过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这种空间环境上的平衡,在笔者看来是以文化传播的潜在/显性过程为主体,大量的符号与信息相互交错,在文化资源与物质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与自然生态、人口现状、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并相互作用。不管差异性的系统对人的影响是有何种区别,其共同点在于一个敞视开放的空间,对于个体经验者的艺术创作,尤其是电影剧本的创作,具有多向度、多元化的可能。
燕门乡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腹心之地。笔者所进入的拖拉村为其所辖七个行政村之一。澜沧江东岸,属于山区,海拔2520米,村西有通往维西县公路穿过。辖区内有10个自然村,216户,1144人,有藏、汉等族。原为乡名,1988年撤区改乡中,由乡一级行政单位,改降设为行政村一级单位(办事处),1998年又由行政村改设为村委会。以驻地拖拉村得名。藏语,拖为松树,拉为坡,意为松树坡。电影作为最终以影像画面展示于大众的一种艺术形式,田野动态变化的气候环境为其画面变动与差异性提供了可能。拖拉村辖区境内山川密布、河流众多,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横断山区垂直地域分异显著,一山有四季。冬少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干湿分明,年平均降雨量650毫米以上,年平均气温14~15摄氏度,降雨集中在每年5月至10月,7月和8月降雨最多。拖拉村村民与生态媒介构成一种技术上的架构,技术包括一个族群借助生态环境场域,将其建构到自我原生性文化基因上,族群在生态环境中的“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这个新技术往往把此前的技术变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人类的新环境几乎都不是‘硬件’,也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信息和编码的数据”。这些信息与数据恰恰是田野调查者,在电影创作中需要观察与把控的关键。笔者在数次进入拖拉的驻守中,一天之内的天气变化,周围景色变动,以及在不同季节进入后的体验,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一是激发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使得自然与创作主体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通过生态资源这一媒介,与个体的“人”的感官展开密切的互动关系,运用多种记录形式,保持生态媒介的基本样貌,以此促发人与自然审美性关系的长久性,持续电影剧本创作的快感;二是以视野首先进入思维的外在景象,形成视觉的主观意识,也是一种个体经验中的画面形式,这在完成以文字符号为主的剧本之时,创作主体会有意识地以生态化的景观画面为对应物,进行有效的创作。
地形呈V字形的拖拉村,南北长,东西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山区、河谷、高山、水坝区各具特色的地理地貌。澜沧江由北向南贯穿全境,两侧高山对峙,村落田地、牧场散居于澜沧江沿岸及二半山区。丰富的农牧生态资源塑造了拖拉村民农耕与放牧的生活场景,与以往表现草原主体的电影剧本不同,山区、河谷、高山、水坝等差异性的藏族生活、生产场景,更具一种共在性场域上的视觉冲击,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共生异质性存在。客位观察:藏族人依附于田地、牧场的感情与实践互动,促进了一种有关生存“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这种超真实存在,使得创作主体本身打破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使得富含民族文化艺术的审美“元”无处不在。更为关键的超真实存在,却是从当地民族元农牧史异延出的情势表现,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又有意识地颠覆了真实存在的根基,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反映之物,而是融入个体情感经验的人为再造、升华的艺术行为。主位参与:拖拉村动/静生态元素的生成,建构了一个富有想象和情感空间的场域,自然成为人与物之间的媒介,并且影响创作主体所处的时效心理。当创作主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渗透到场域的各个角落,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就具有偏向性,与所谓的陌生化,仅仅通过感知事物、增加新奇、忽视对象的艺术手段不同,偏向性是在熟知对象的状态下,不断破立的过程中完成真实解构与重建,取决于剧本功能特征,吸取田野生态元素的最终影像,是意象对真实的再现,而且遮蔽了创作主体真实性的缺场,万物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如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当涵义并非产生在两幅画面的冲击之中,而是蕴藏在画面内部时,这就是象征,这是指某些镜头或场景,它们始终属于剧情本身,但是,除了它们的直接涵义外,还拥有一种更深广的意义”。作为创作者意识思维上的偏倚,这种田野过程中的生态媒介,引导创作者使用自身机能、感官、情操,构建电影剧本中的内涵与象征。
三、剧本创作与地方性知识
与宏大叙事、史诗性民族电影艺术不同,混杂地方性知识的电影剧本的创作,其出发点与民族志、田野作业紧密相关,具体细微的个案考察,避免了宏大叙事结构的建构,不仅涉及特定场域,少数民族地理空间上的艺术表达,以一种动态的、非二元对立的、异质的和立体的思维方式,经过真实体验,展现强大生命力。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剧本创作,双向度形成的特定语境,包括具体田野点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特定结构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多向度、多元化、具体化、情景化的艺术表达,成为浸染地方性知识电影剧本创作的风格特征,与以往那些少数民族封闭、偏远地界的神秘习俗文化,潜在隐形地给予少数民族影片丰富的艺术奇观和悬念不同。通过田野调查创作的电影剧本,更具微观的艺术表现性,也成为一种电影艺术,地方历史文化景观的奇居效应,也就是电影剧本的艺术创作,其创作灵感按照系统化原则和层级差异性原则,在特定地理空间上,以少数民族文化景象、少数民族的艺术范式等,来组织关于现实电影剧本的创作,当然剧本最终形式,依然是通过镜像来表达一种经过艺术过滤的文化书写,而这些真实的知识或语言存在形式,则都扎根于地理空间上的少数民族坚实的文化基础(根)之上,属于一种内在和外化同构的存在。这种形式创作下的电影,实际上有一种类似于“自然化”的效果,田野点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对环境所进行的这种“自然化”,这就是在现实界域中,把外在自然改造后再把它当作文化符号、艺术象征来重建,例如拖拉村依山而建的藏式民居,经幡白塔,藏族人为自然环境中的场景构建与重组,意味着通过村落族群对民族文化进行集体再循环式的传承,从而造成的是一种对本初生活状态的“模拟”的现象学。
参与是田野中表达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关键概念,而对于电影剧本的创作,参与同样是考察与体验少数民族村落族群生活、风俗习惯、宗教图腾、节庆艺术等的特质。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中,拖拉藏族妇女的斗酒节、疯行喇嘛的事迹、神山狮子三兄弟的传说等,都是在实质性的参与中获取的创作信息与灵感,这就需要创作主体以内在眼光和外部视野,双向度地进行观察与体悟,来完成电影剧本中的景观构建。其艺术化的景观空间,可分为具象与抽象,具象空间是实体性存在于现实界域的生态媒介,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存在。少数民族通过地理空间来展示服饰、语言、建筑、日常器具,以及诸多的社会生活物象。抽象空间一般在少数民族电影剧本创作和电影影像中,创作主体以文化艺术的承担者身份,一种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即使不能感知当地人所拥有的感知心理,也要尽可能地与之相似、近似,穿行于局外人/当地人双重身份,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信仰、民俗甚至人的行为,有所含义与象征地去把握,少数民族族群社会中的人,如何在他们自己人之间表现自己和独立表现自己。文化和艺术的相对主义是田野调查到电影剧本创作的关键,因为最终文字与影像,都要运用背景音乐、矛盾情节、电影角色等,复杂勾连的关系来展现一个民族潜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象征,这也是一种电影文化的深层次表达。
四、剧本情节与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本源性讨论中,历来处于一个关键位置,其外在的语言表述往往隐含着繁复的艺术内涵以及差异性的表述形式。如英国学者哈特曼和斯托克所述元语言:“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对象语言)的语言或一套符号。”这套系统化的符号背后是事件,事件需要构拟来显现逻辑性,而我们通过构拟的模式认知具体事件。电影剧本中所涉及的田野点神话传说事件中,是一种人为的认知决定,是通过陈述事件和不确定性事物(神话)本身关联,隐射出的一个事件忠实,系列化神话传说元素的逻辑构建,成为神话传说主体,也成为电影剧本情节的重要来源,两者同样都在历史时间中,以普遍性形式、艺术形象、历史意义不断得到绵延。“虚拟性并不对立于真实性,它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现实。”
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中的诸多情节都涉及了神话传说,所涉及的神话以其神山信仰下的狮子三兄弟为主,其神话中所涉及的酒神神性表现在世俗空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拖拉村酿酒工艺的历史传承,也成为拖拉人将酒视为精神,嗜酒如命的地方性风俗。其衍生出的剧本故事情节就成了藏族女性盛大的斗酒节与喇嘛戒酒顿悟的事件,整个酒神神话的“元”书写,在拖拉村在场性的现实界域,得到了一种再生产或二次书写,最终又以剧本情节予以展现。杜赞奇曾经指出:“为了承认自己是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现在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自我的可信形象,即在新的变换了的现实中找到自我。”少数民族电影影像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质,往往要以民俗化、民间性的节庆仪式、丰富多彩的绚烂歌舞来进行展示,这也一直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标榜族群身份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是现实界域对想象界域的真实反映。而剧本中的传说,包括香巴拉传说、活佛灵识转世传说、疯行成就者事迹传说等,都是借助田野调查中的真实性访谈,进行艺术加工而形成的故事情节。电影剧本涉及神话文本的转向,也就是指作为一种神话世界的符号构成,无论是口承历史,还是现实存在,异质性的神话传说表达,在同质性的剧本情节的塑造上,隐含着“元”文本创作主体与村民群体创作主体以及电影剧本创作者,三者多向度的视界融合,这种视域上的融合本身就是电影剧本创作者心理上的吸收、理解、运思以至最后的符码输出,每一主体都在选择性状态下生成文本,具有纵向性的历时表现,比如从最初民间酒神神话经过长时间的衍化,又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佛教思想的浸染形成新的文本,并且深刻影响拖拉村民的生活习惯;同时神话传说表现在电影情节上,又具有共时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上,由于目的性,一种文本生成后,被异延成另外一种现实情景,所有过程在同一现实层面发生。作为电影剧本的创作主体,此时所运用的现象学移情是发生的关键,就是将心同此情此景的经验现象与文本现象移情植入。正如涂尔干学派对神话研究得出的一样,在神话文本的转向中存在创造性的想象。电影剧本的想象成分,更多的是创作者对神话传说的剧本情节转向,不可避免地涉及神话量素的增缩和分异,也是创作过程中书写形式、神话寓意、故事情节上的有意设置和安排。
作为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者,需要“在手头资料所能证明的事情中发现隐藏的故事;他的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揭示故事的技术上和叙事结构形式”本身,既是发现者又是创造者,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中,开头以画外音处理,用时间为顺序,罗列的探险家吉尔、戴维斯、金登·瓦尔德、亚历山大莉亚·大卫·妮儿的经历和文本游记以及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探险家游记创作的名著《消失的地平线》,这些都是剧本创作者资料收集的发现,而田野作业过程中遭遇的拖拉村藏族丧葬仪式、参与的拖拉寺时轮法会,又是剧本创作者发现故事人物旺杰大喇嘛、疯行修行者以及他们背后故事的关键。如克里斯蒂娃所述“文本的产生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其他文本材料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就完全取决于剧本创作者的艺术加工与情节塑造能力。通过剧本创作者的艺术运思,以文字符号将神话传说予以故事情节再现,表征多线情节的错综复杂,表意复调式的情节推进,创作者的这一创造性的实施过程,具有敞视的结构性,田野中所收集的文本资料、现实观察、地方风俗、建筑服饰……所有资源的使用都是一种述行,剧本情节的创作就是一种嵌入和参与田野点地方社会文化的生成过程,它塑造现实也被现实所塑造,是整个地方生活史的,艺术化表现形式和构成部分,其电影剧本情节并非独立于田野点的系统,并不外在于当地生活,而是只存在恰当与否的差异。剧本情节中的语言恰当性,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时间和空间场合,也规范与推进情节发展。创作者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有能量去拒绝组成故事中各存在物的不可穿透性与孤立性”,同时田野取材创作的情节也是“一种可能的历险。一个符号和一个意图的交遇”。
五、结 语
从田野调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民族地区,差异性的个体村落都蕴藏着丰富的、可以用于电影创作的素材,这些素材不同于以往的纪录片影像的展现,通过以符合电影形式的艺术加工,即可具有情节、矛盾冲突、反映他者生活状态的电影剧本,也具有后期影像表现的可能。而田野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具有象征和隐喻色彩的创作元素,这些人为以及自然的景象,通过深描式的挖掘,组成了电影剧本的构成要件,也可以适时激发创作者灵感。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获取,包括民族风俗、仪式节庆、神话传说等,通过一种创作者的思维转向,可以利用电影手法予以深层次的表达事件,并且以历史的厚重感来附加创作对象,这样的艺术思想的展现,往往可以产生出美学意味上的绵延与自由,并且打破时间局限,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也最终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出现,甚至成为真正的电影。
注:电影剧本《坛城中央的香巴拉》(原名《拖拉村的酒神》)为第二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剧本单元参赛作品。
注释:
① 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概念,“述行”引申为一切符号现象的根本属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塑造与被塑造。
② 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巴什勒的本体平等概念,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是宏大的还是微观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
③ 共生异质性:来自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共生异质性概念,指差异性诠释过程和文本格局在书写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所导致的同时异变。
④ 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在1976年出版的《象征性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一书提出的概念,1981年《拟像》(Simulation
)中进行具体阐释。⑤ 异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著《写作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6)中异延思想“异延”代表一切差异的根本特征,也包含全部差异。它存在于一切在场、实在与存在之中,在颠覆现有的结构中呈现自己的存在,与播散一起成为一种哲学意味上的变体存在。⑥ 情势: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核心概念,情势为显性结构存在特征,包含两个多元性质:断裂的多元和连续多元。
⑦ 源自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概念或译为视域融合,代表理解者对对象理解的视界同历史上已有的视界相接触,形成了两个视界的交融为一。
⑧ 来自范德莱乌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改造所形成的神话宗教理解思想。
⑨ 王治河在其论述中认为与异延概念等同,笔者认为分异表示一种在“元”状态下的变化及差异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