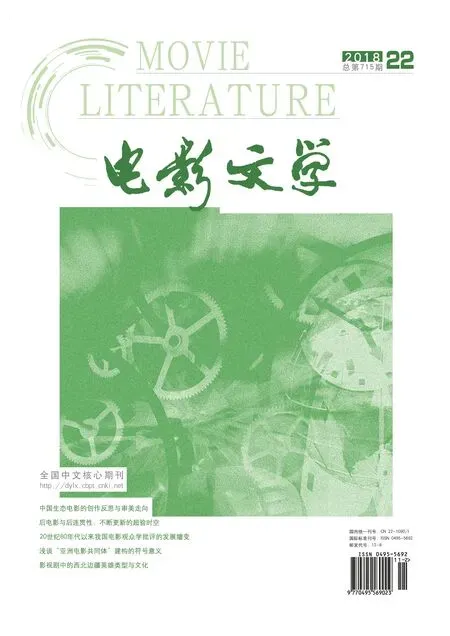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妖猫传》的主体间性理论阐释
李沁叶
(平顶山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无极》等多部电影都给观众带来过强烈的间离感,《妖猫传》也因这一倾向颇受讥评,有学者称其为“难以入心的盛唐气象幻灭图”,或认为其情感表现力差、现实透射度低、视觉奇观流于刻意,究其原因,是陈凯歌的作者表述意向超越了对电影产业规律尤其是对类型电影制作规律的遵循意向。他把大众熟知的《长恨歌》情节组织为个人的言说材料,对其进行了现代演绎,以延续自己对主体性问题的表述习惯。
一、主体性问题与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
主体性(Subjectivitl)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人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时,便成为独立的主体,“这时他作为主体在同客体的关系中所具有的性质就是主体性”。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逐渐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自己视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
但主体性思维本身蕴含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依托于理性的主体观念急剧膨胀,进一步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人与人的异化和西方的理性危机”。学者们尝试以主体间性的构建来解决主体性的这一自有痼疾。其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倡导的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为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布伯认为,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利用关系构成“我—它”(I—It)关系,当人视外在之物为与自己相同的主体而非对象时,人与外在世界建立了“我—你”(I—Thou)关系即对话关系。哈贝马斯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于两性中处于客体地位,女性及其生存困境成为电影导演表述主体性问题的常用载体。
二、陈凯歌的主体性问题表述传统
针对电影的集体创作机制与传统对导演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特吕弗和巴赞倡导“作者策略”,支持具有个人风格的电影导演。安德鲁·萨里斯将其美国化为“作者论”并提出了导演作为“作者”的三个标准:具有娴熟的电影拍摄技术;能形成鲜明而统一的个人风格;其理念和老板交代的剧本间会产生冲突。孟君等学者倾向于用“作者表述”概念来研究中国电影文本。“作者表述”指导演通过作品进行自我言说,“这既是一个‘作者’将自己从各种‘成规’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也是‘作者’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表述,建构和表述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
在中国,“真正以‘作者电影’的基本宗旨从事电影创作,并由此而形成一个创作群体的,当属第五代导演”。转型之前,陈凯歌着意在《黄土地》《孩子王》等电影中表现人主体性的缺失。在转型过程中,陈凯歌倾向于“通过影片表现人物在困境之中的抉择、挣扎、反抗甚至反叛,进而表现人物主体性的异化甚至幻灭”,如《荆轲刺秦王》与《霸王别姬》。从《无极》中的鬼狼与昆仑开始,陈凯歌致力于描述人主体性的萌芽与成长,故《梅兰芳》中的梅兰芳、孟小冬、邱如白有了艰难但清醒的选择。陈凯歌的思考与表述在《赵氏孤儿》中出现了飞跃:程婴在主观上并不想牺牲自己的孩子,也未将赵氏孤儿当作复仇工具来培养,他给予孤儿充分的爱与独立的价值。程婴不仅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还具备了主体间性意识。《道士下山》中如松表示,“慈悲”与“淫邪”等对立的概念只是不同主体对同一行为的不同价值判断,在此陈凯歌尝试以中国的道家、禅宗思想为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指导。
在对其个人表述传统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陈凯歌对主体性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并逐渐成熟,其成熟的认知在《妖猫传》中被充分展现。
三、《妖猫传》描摹的主体性困境——“他人即地狱”
白龙主体性的萌芽、成长与异化是《妖猫传》的重要线索,其中是贵妃激发了白龙主体意识的萌芽与成长。但贵妃被以玄宗为代表的权力阶层符号化、工具化并成为其用以消除社会危机的“替罪羊”。陈凯歌以贵妃的殒命与白龙人格的畸形发展展示主体性面临的困境。
(一)白龙个人主体性的萌芽
在见到贵妃的一刹那,白龙便被吸引、被感召,其身份意识即“我是谁”的疑问被最大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自卑、孤傲、敏感的白龙桀骜不驯地向贵妃陈述身世,将伤口直接撕裂给贵妃看,其行为中潜藏着他对不幸命运的孤傲反抗,对人伦情感的愤怒拷问,对贵妃的隐蔽试探与无声求救。贵妃听到了白龙内心的呐喊与呼救。她主动走向白龙并将自己置于同等的高度,启发他积极面对生活,使白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白龙对“我是谁”的问题有了初步的答案,对自己、对人本身有了信心。他视贵妃为人间至美的象征,以贵妃为参照和偶像,开始了对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
所以之后贵妃罹难时,白龙敢于怒喝玄宗与师父;即便已经被打断一条腿、面临被灭口的危险,白龙仍义无反顾地返回陵墓;因不忍伤害一只猫,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此时的白龙具有利他精神、有坚定清晰的个人意志并能以个人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其思想与行为中已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二)异化后的绝境
1.个人性主体的膨胀与贵妃的殒命。电影中贵妃被以玄宗为代表的权力阶层彻底符号化。玄宗将贵妃置于云梯上供万众瞻仰,赐其华丽霓裳,为其举办奢华的极乐之宴。被万众凝视的贵妃具备了物的典型特征,是大唐盛世的能指、玄宗作为盛世帝王的标志符号。玄宗给予她宠爱与地位,只是在娴熟地运用符号的能指功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享受权力与成功带来的快感。
贵妃还被工具化为化解社会危机的“替罪羊”。法国哲学家与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指出,社会危机出现时群体常选择具有“异常”特征的人作为替罪羊,通过迫害这些人来化解危机、恢复秩序与和谐。电影《安史之乱》的背景早为大众熟知,而统治阶层普遍趋向于用万众瞩目的人物贵妃的私生活来解释社会危机的产生原因。“替罪羊”最重要的作用是替选择他的人群赎罪,最终贵妃认同了自己的“替罪羊”身份并实现了自己的救赎功能。
陈凯歌着意表现了将贵妃工具化的思想与行为中潜藏着的个体性主体高度膨胀的事实:贵妃是金吾卫与玄宗权术角力的砝码;黄鹤的出谋划策、高力士的制造假象行为都只是玄宗意志的具体执行;精通权术的玄宗统辖了这些力量,指挥了这场集体暴力,是谋杀贵妃的真正主谋和迫害者群体的最高代表。
2.主体性困境:“他人即地狱。”对于白龙,贵妃的死意味着真善美的毁灭,置贵妃于死地的阴谋与阴谋背后的丑陋人性使白龙对人、对生活的并不坚定的信念全部破灭,他内心向往但在行动上放弃了贵妃指引的方向。白龙异化为“妖猫”,开始了自己的血腥报复与杀戮行动,使整个长安城被恐怖氛围笼罩。他视自己为长安城的绝对主宰力量,其行为与玄宗等人的行为在性质与后果上已殊途同归。
除了玄宗、白龙等人,电影中的春琴、陈云樵、丽香等人也有类似的倾向。
在将他人对象化的过程中,拥有更多权力或能力的个体(如玄宗与白龙)给更多的人带来了不幸。电影中的众生一度置身于“他人即地狱”式的生存境遇中,陈凯歌借此描摹出了主体性所遭遇的困境。
四、主体间性与救赎
但《妖猫传》其他人物的行为多次实现了对个人主体性的超越,所以,尽管不遗余力地展示了主体性困境,陈凯歌仍在电影中表现了自己对人类突破困境的乐观态度。
(一)客观并乐观的表述者
陈凯歌对主体性问题的表述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他充分肯定了人主体性的固有价值。除了贵妃,他并未使李白、白乐天、空海、惠果(丹龙)等人工具化,而让他们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与鲜明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陈凯歌还让他们超越了个人主体性并具备了主体间性立场。李白拒绝将美工具化;他桀骜不驯却并不妄自尊大,在见识到贵妃的风采后能真诚称赞她“云想衣裳花想容”。白乐天并不简单利用贵妃敷衍自己的故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坦言“大唐的陨落不是她的错”,竭力调查其死亡真相。惠果发愿将消除人性之恶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空海远渡重洋、不畏艰险来到大唐,为的也是寻找使人类解脱痛苦、获得幸福的无上密。
将角色与其他人的接触概率考虑在内可以发现,拥有更强主体间性意识的人给予更多的人幸福,他们个人正面影响力的大小即“我—你”关系的构建行为只与其主体间性意识的强弱有关,而与其拥有的权力、能力无关。这些人形成了打破主体性困境的潜在力量。
(二)对话中的救赎
电影对白龙内心世界的表现非常富有张力。在为贵妃复仇的过程中,白龙偏执而绝望,并没有获得心灵的慰藉与宁静。报复行为中潜藏着白龙对贵妃所代表的人类高贵品格的信仰和固守,绝望中蕴含着白龙对救赎的强烈渴望。
《妖猫传》故事展开时贵妃已经殒命三十年,所以她事实上始终不在场。贵妃之所以能成为电影的核心人物,是白龙、白乐天、空海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贵妃是典型且极端的被沉默者与被言说者。白乐天、空海等人不断努力与贵妃进行对话,最终成功地使逝者发出了声音。贵妃的代言人白龙的愤怒因此平息,惠果等人实现了对白龙与长安黎庶的救赎。在此基础上,白龙被度化、空海求得无上密,白居易定稿《长恨歌》,丹龙得到了传播无上密的机会,他人不再是地狱。
陈凯歌以《妖猫传》描述理想人性,致敬李白以《清平调》歌咏理想之美。与李白写就《清平调》后才与贵妃谋面相似,陈凯歌的理想世界在大唐衰落后、电影结尾时才初露端倪,于是盛唐气象的奇观表现与导演的理想表述间出现了断裂与错位,受众尤其是部分研究者对此表示了不满。但从作者表述这一维度考量,《妖猫传》体现了陈凯歌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