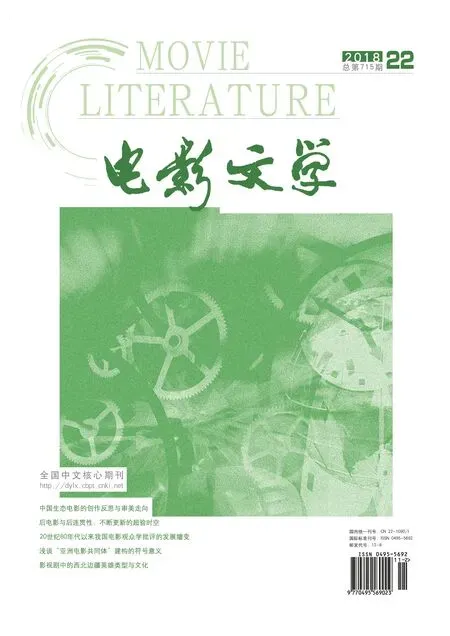浅议卡梅隆科幻电影中的女性观
姜 研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宜兴 214200)
詹姆斯·卡梅隆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好莱坞的符号性人物,在作品数量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在当代导演中拥有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齐名的地位,这是与卡梅隆电影浓郁的人文意识紧密相关的。电影对于卡梅隆而言,不仅是商品,更是其关心人类生存境遇,宣扬人类精神的载体。而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卡梅隆的女性主义意识。从卡梅隆的科幻电影不难看出,他有着一套可圈可点的女性观。
一、两性关系: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疑全方面地处于被动地位,是被男性所侵害、束缚的对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现象被要求得到矫正,女性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卡梅隆的科幻电影也揭示了这一点,即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性别秩序并不平等,男性总能以各种方法伤害女性,而这种情况是人为构建的,它有可能,也有必要被改变。
卡梅隆执导的《异形2》(1986)延续了雷德利·斯科特在《异形》(1979)中的女性观,蕾普莉是《异形》中飞船上唯一从异形的攻击中存活下来的人类,她是人类的希望。在《异形2》中,蕾普莉依然性格坚毅,身手不凡,智勇双全,可以说在能力和心智上完全不亚于男性,但是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并没有在一开始给予蕾普莉信任,以至于蕾普莉在向当局汇报异形的危害性时,诸多男性官僚都视蕾普莉为精神失常者。
蕾普莉并不是唯一一个因精神失常的理由而被限制发声者。在《终结者2:审判日》(1991)中,莎拉·康纳也因为他人不相信她曾被“天网”追杀而被视为精神病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居住,被迫和自己的儿子分离。莎拉只有不断地自我强化意识,提醒自己“我没有疯”,保持思维的清醒。更为恶劣的是,莎拉在精神病院还一度遭遇强暴。与之类似的是在《阿凡达》(2009)中,杰克·萨利在酒吧里也见到一位男性公然霸凌女性,双腿瘫痪的他为了给女性打抱不平而被连人带轮椅扔出了酒吧。如果说,在《终结者》(1984)中与莎拉为敌的还主要是“天网”派遣的机器人杀手,那么在续作中,人类也参与到了对莎拉的迫害当中。
两部电影在展现两性关系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女主人公在从险象环生、九死一生的境遇中脱离出来后,男权社会并没有对其表示出足够的理解、关爱和信任,而是视其为需要隔绝或提防的异类,以男性为主体的当局尤其显得颟顸、短视,但他们掌握着比女性更大的权力。而现实很快就会证明,蕾普莉和莎拉是对的。一旦危险出现,整个男权社会又依赖女性出来扮演救世主,而女性也都不计前嫌,为人类的命运而战。在《异形2》中,移居异形所在星球的人类很快遭到了异形的攻击,此时地球上的人都对异形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又找到蕾普莉,让她加入营救小队。《终结者》中,莎拉则为销毁机器人的资料而全力奔走,并且孕育培养了未来的人类领袖约翰·康纳。人类因为对女性的忽视和缺乏尊重而遭受了巨大浩劫,这正是卡梅隆对男权社会的态度。
二、社会定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
男权社会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依附者,而男性由于充任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职位,因此他们希望女性满足于家庭生活,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或是在社会工作分工上只能从事边缘性的工作。只要对《终结者》系列稍做留意便不难发现,女性除了家庭妇女,往往只能担任服务员或护士这样的角色,而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如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等,几乎都是男性。这种划分绝非是女性在能力上天生不适合于成为科学家、企业家或警察,而是一种长期的性别歧视带来的职业固化现象。以至于连不少女性也都认可了这种分工,电影中人类的社会思想是要远远落后于科研水平的。
在《阿凡达》中,纳美人所在的潘多拉星球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美好存在,人类在这部电影中成了反派,在这部电影中,卡梅隆就表达了女性应该成为更多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女性能负责更多的社会利益的女性观。电影中的纳美人公主妮特丽是一个美貌而坚强的女战士,在后期纳美人和人类进行对抗时,妮特丽始终起着领导作用并身先士卒。并且有别于在《终结者》中,女性还是男性拯救和保护的对象,势单力薄的莎拉先后被凯尔和T-800保护,在《阿凡达》中,女性是男性的拯救者和启蒙者。当杰克来到潘多拉星球时,是妮特丽从狼的口中救了他的性命,也是妮特丽带领杰克慢慢认识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妮特丽不光挽救了杰克的肉体,还挽救了他因为自己的残障而一蹶不振的精神。女性在卡梅隆的电影中,既非只有美貌的“花瓶”,更非“红颜祸水”,而是对维护社会稳定有所贡献,积极参与到家园保卫战中的女英雄。
三、个体成长:不让须眉的自我完善者
如果说,为女性设定社会角色,是一种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向外扩展,那么刻画一个女性个体的成长历程,表现她心灵上的逐渐成熟,则是一种对女性向内的探索。也正是在这种探索中,卡梅隆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越发丰满。波伏娃曾经指出:“男人判定女人是简单的,她被称作‘性’,意味着她对于男人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性感的尤物出现的。”而卡梅隆电影中的女性则不然,她们会自我完善,让自己成为更强大的个体,这在《泰坦尼克号》中尤其明显,在科幻电影中亦然。
例如在《异形2》中,卡梅隆特意完成了斯科特在《异形》中没能完成的任务,即塑造一个完整而非完美的蕾普莉形象。在电影中,蕾普莉的内心对于自己当年遭遇异形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她还经历过女儿去世的痛苦,这使得蕾普莉有时极为脆弱。而电影中蕾普莉与异形产生冲突并战胜异形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蕾普莉克服阴影的过程。又如在《终结者》中,莎拉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女,在遭遇危险时不知所措,然而在和机器人的对抗中,莎拉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终结者2》中,观众可以看到,莎拉早已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女战士,她会开车,会开枪,能够冷静地处理危机同时时刻注意保护好儿子约翰,她的坚强和勇敢鼓舞了约翰,她的温情和善良也感染了原本没有任何情感的T-800。这些角色都在彰显女性的力量。
应该说,卡梅隆很难被认为是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作为一位男性导演,他也还不能完全从女性的立场来审视、把握外部世界,同时在电影必须向商业妥协的情况下,卡梅隆也还不能全面展现女性的生命特色,但是他的科幻电影确实将一个个优秀的女性形象引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思考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可以说,卡梅隆拥有着进步的、值得肯定的女性观,这种女性观与其电影艺术互相成就,卡梅隆科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他的女性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