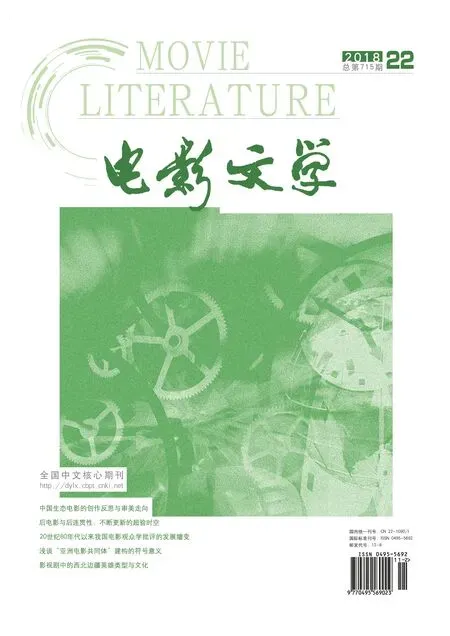浅谈“亚洲电影共同体”建构的符号意义
张 鑫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一、引 言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看,电影——作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5年被正式纳入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使命。仅当年,在世界电影380亿美元的票房中,亚洲地区内:中国就达到67.8亿美元(约占总票房17.8%),韩国13.72亿美元,日本约20亿美元,印度约15亿美元。两年之后, 到了2017年全球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06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地区贡献最大:中国总票房达到了79亿美元,韩国约16亿美元,日本约20亿美元,印度约16亿美元。依然赶超北美110.7亿美元的总票房,仅中国一家就比欧洲的英国(16亿美元)、法国(15亿美元)和德国(12亿美元)的票房总和还多得多。
但是,在亚洲电影票房井喷式增长下,反观近年世界电影市场,北美、欧洲、亚洲各地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依然鲜有亚洲电影的身影,总是无不充斥着好莱坞《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等系列科幻电影的续写,《美女与野兽》等动画片的青睐有加,《速度与激情8》等动作片的情怀回溯种种。更有甚者,2018年刚刚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截止6月9日,内地票房已破23亿元。西方影片高票房的背后更多的是好莱坞主流文化的渗入和亚洲本土文化在影像表达和接受程度上的缺失危机,即便是本土本民族文化,在影像表达中往往也只是好莱坞基调上的昙花一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符号已经深深根植于世界观众的内心,并进一步影响和发展了影视产业。据此,笔者将结合“电影符号学”来探讨亚洲文化中共同共通的影像符号表达,希望通过亚洲各国彼此间相似的美学、文化和沟通日益紧密的人才、产业要素等,共同构建东方的“电影共同体”,在全球化西方主流电影语境中找到亚洲电影的专属符码和名片。
就像汉语言一样,自从有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稳定的语言文字,中国就有了世界上最丰富、最详细、从来不断线的历史记载。电影也应如此,只有通过相似的审美体验和知识认同,形成了基于东方电影符码对 “亚洲电影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亚洲电影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走得更远。
二、电影符号之于西方电影
(一)电影符号学
符号学是由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在他看来,符号学“是一门研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生命的科学”。20世纪60年代,克里斯蒂安·麦茨运用语言学、符号学进行分析,就电影的意指系统进行分析读解,揭示作为表意系统的内在规律。“麦茨认为,影像作为电影的核心要素,没有类似语言中音素、语素那样的最小单位和离散性元素; 同时,影像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距离太短,没有语言中的第二分节,具有现实化的特点和不可分解性,因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即不是语言学定义上的语言。同时,镜头在意义和功能上类似语言中的陈述段,在这一层面上具有类似语言的系统和结构,因而电影又是一种类语言。总之,电影是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电影符号的意指应该由电影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来构建。电影符号的“内涵”包含万象,一千个读者所给予的解读会产生一千个不同的含蓄意指层,用“外延”一词来表述这个无限的集合更为恰当。“相对于其他艺术,电影艺术所使用的符号是最复杂的,包括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语言符号等多个符号系统,这是由电影作为多媒体艺术的性质决定的。……这些符号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影响文本的意义构建”。
(二)西方电影中的典型电影符号
首先来看,风靡全球的电影业巨无霸好莱坞也不是一口吃成的胖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电影在世界上能有今天的成就,或许正是通过“西部荒漠、二战战场、百老汇歌舞、自由女神像、华尔街、高科技等”一个个代表性强的文化符号积累和灌输,配合以精美绝伦的电影技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才构成了今日异彩纷呈、备受世界瞩目和认同的好莱坞大片。“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字音字形是能指,字音字形所指向的概念是所指。电影符号也同样地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不同的是电影符号的能指远比语言符号的能指丰富,图像、音乐、对白,甚至包括摄影机的角度,都是电影符号能指的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电影符号甚至促成了好莱坞电影类型化的发展,这一点从“西部片”这一最初的类型化电影发展就可见一斑。1903年美国导演埃德温·S·鲍伯特拍摄的影片《火车大劫案》中就已经具备接下来西部片的一些影像、人物符号元素,例如歹徒、警察(或牛仔)、山谷、策马追逐、戈壁等。继鲍伯特之后,1939年西部片的缔造者约翰·福特通过经典影片《关山飞渡》形成了西部片较为固定的类型程式:通过固定的影像符号表现美国19世纪西部的风光,通过固定的人物形象来展现白人或牛仔与歹徒的斗争,通过声音符号把荒蛮的西部变成了音乐之乡,美国乡村音乐直到今天还广为传唱。民间的个人英雄牛仔,穿着牛仔裤和皮衣,戴着宽檐高顶毡帽,腰挎柯尔特左轮手枪,足蹬带有刺马钉的高筒皮靴,正是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得到认同和想象并由此传承,遂将西部片这一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的电影类型推到了世界观众的视野,以至于直接影响到世界其他类型电影的产生和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
以艺术性见长的欧洲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模式不同,它是电影的诞生地,在百余年的发展中也形成并保持了其自身的魅力。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文本大量使用影像、声音、话语、蒙太奇等符号,欧洲电影多从观众接受的角度大量以隐喻为主。麦茨结合雅格布森的论述,将符号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类型。隐喻是一种语言学的修辞手段,指的是用一个事物来暗指另外一个事物。换喻又名转喻,一种一个词或词组被另一个与之有紧密联系的词或词组替换的修辞方法。以隐喻和换喻为主的欧洲影片,大多以联想内容展开,因而必然淡化拍摄技巧与规定法则。例如就拿“蓝色”这一色彩符号来说,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经典的《红》《白》《蓝》三部曲之《蓝》,电影中有这样的一幕:主人公朱丽在遭受到车祸后,开始收拾物品,从蓝色光影的房间中扯下了一串蓝色的风铃,进而坐在楼梯上拿着这个蓝色的风铃在手中揣摩的时候,观众们可以看到折射在她脸上的蓝色光线。再比如在这部电影中,每当主人公朱丽陷入矛盾,从而痛苦地挣扎时,就会跳进蓝色的泳池,这是一个明显的隐喻片段,即便是只有蓝色,也能隐喻出朱丽悲伤至麻木无力的感受。再如德里克贾·曼于1993年拍摄的电影《蓝》,这是他生命中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记录了他患艾滋病之后的最后生命时光。这一阶段的他已经失明,所以整部影片除了嘈杂的环境音与背景音乐之外,只有一片蓝色,这里的蓝色,就是世界的隐喻。那又为什么欧洲电影偏爱选择蓝色的隐喻光线呢?笔者认为欧洲人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睛又是心灵的窗户,人们通过对方的眼睛会读懂触及灵魂的东西。另外,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与海结缘,海洋意味着生命的起源,蓝色符号可以让欧洲人经历灾祸之后,重新唤醒对生命的思考。
此外,欧洲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风车、雕塑、教堂、音乐、国王”等文化符号也构成了欧洲影片的独特共同想象。
三、电影符号之于亚洲电影
早在电影诞生之初,亚洲各国的电影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影像表达,不同于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放眼全球的定位,亚洲电影初期创作主要面向本国观众,这一做法奠定了电影早期在本国的迅速发展。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国彼此间不可避免的隔阂,早期的亚洲电影人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在大范围内共通共融的叙事方式,从而使影片在跨国传播过程中大打折扣,很少走出国门,遏制了本民族影片在亚洲直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到了当下,亚洲电影因为这种自身文化符号表达的缺失,为了迎合被好莱坞大片冲击下的本国观众,而普遍存在着娱乐过度与文化不足。中国电影从前些日子的《小时代》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到各种综艺节目的大电影;日本动画烂片《钢之炼金术师》《烟火》等;印度烂片《巴霍巴利王》等,尼尔波兹曼所担心的娱乐至死正在蔓延。亚洲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中所存在的急功近利式的过度娱乐,即便是能够为一些观众带来短暂的刺激和猎奇感受,但这些不具备民族共同感和情感共通性的影片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而那些能够为观众展示传统精神当中具有永恒根性的理性追求才是电影艺术所应提倡的。因此找到并养成一批建立在亚洲文化间共通的电影符号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尽管亚洲区域广大,民族文化多元,但“东方民族在艺术和美学思想方面的相似性、一致性、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和独特性。这是因为,东方各民族在生活生产的方式上,在历史发展的实践中,相同的因素远远比差异的因素多”。
(一)处变不惊的长镜头符号
受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影响,典型的亚洲电影擅长用质朴的画面构图来映衬生活中的细节,在平静悠远的镜头语言里带入作者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会借助于比较、隐喻、象征等手法,不直接性,永远是亚洲影片中自觉的一种东方文化。
以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为例,在他著名的往事三部曲(《悲情城市》《童年往事》与《好男好女》)中,都倾向于使用长镜头来营造出一种以第三者注目时光流逝的真实感受,并透过琐碎的生活细节,看似可有可无的动作、对话,朴素的场景空间来勾勒出传统的生活轨迹。这种对于“时间流”的强调,成为东方电影的一个审美特质。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侯孝贤一样,小津安二郎一样善于使用固定长镜头进行拍摄。不同的是,他对画面构图的要求极其严苛,例如为了不使人物走出画框,小津经常使用较大的景别拍摄,好让角色的活动不会超出画框。如《东京物语》中,富子和周吉两人在河边散步时,摄影机一直在较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们,这样做既保持了画面的完整性,也流露出世事变迁下对两位老人境遇的哀叹。这就是巴赞所主张的:“电影应该保持模糊性,长镜头以保持素材符号的完整性、多样性无限趋于生活的真实,给观众的感知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或许以小津安二郎、侯孝贤等亚洲导演的长镜头符号所在就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一种东方式的哲思,这种哲思不同于好莱坞的浮光掠影、影像奇观,也不同于达达主义等风格的形式为先,这是亚洲人所特有的“积累、冷静、反思、领悟”。
(二)自然原生态浑然天成的东方音乐(音响)符号
电影是一门视听艺术,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声音无疑也成了最重要的电影符号。相对于西方音乐的人工性、技术性、科学性等特征而言,亚洲东方音乐具有自然性、原生态性、实用性等特点。“东方民族制造乐器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大自然的各种物件,这既决定了乐器所具有的高亢、清脆、纯净而尖锐的声音特色,又形成了东方民族声乐演唱的特色。久而久之,也训练出了东方人音乐审美方面喜爱高亢、清脆、纯净之声的听觉习惯。”与此同时,擅长天地命理的东方人音乐中也无不体现出宇宙“宁静致远”的本体意义,在这一点上,日本电影就是很好的例子。动画片巨匠宫崎骏的御用配乐——合作三十年之久的久石让所配的电影音乐大多呈现出旋律质朴而优雅、和声和伴奏织体都非常简单,注重于刻写旋律,目的是“够用就行”,95%以上打动人的地方都集中于旋律,音色缥缈而带有朦胧感等特点。使得受众在观影时切实感受到那种缥缈浪漫又时而夹杂着些许忧伤(《天空之城》主题曲),抑或是经历重重磨难仍然相信希望(《起风了》主题曲)。值得一提的是《千与千寻》和它的主题曲《永远同在》,《千与千寻》讲述了千寻误打误撞进入了神界,为了救出因为贪婪而变成猪的父母,历经一系列磨难,最终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的故事。这首《永远同在》在创作中加入了三味线、笛子、鼓等日本民族乐器,再配合以日本民族的曲调,同时加入西方的钢琴,使得整个配乐既富有浓郁的东方民族风格又不失现代流行钢琴的浪漫色彩。除了久石让,在后来的2017年日本大卖的动画片《你的名字》中,“溪水潺潺、秋风萧瑟、鸟叫虫鸣、风吹雨打”等自然声音符号都被很好地融入画面,用本民族画面、音乐符号描绘本民族的风土人情,日本电影无疑走在了亚洲电影的前列。
无独有偶,在中国导演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由三宝创作的主题曲,同样透过那纯净、灵透、悠长的笛声,在那每一次使观众记忆深刻的宁静透明的田野、绚烂艳丽的秋色和大雪皑皑的冬日等小高潮里,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纯净如行云流水、如四时更替般的感受。乐器笛子等浓郁的“中国风情”符号配以西方调音箱,给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东方印象。音乐(音响)作为艺术符号,配合以银幕内容主题,便也扩充为民族符号、文化符号、亚洲符号。
(三)叹为观止的视觉景观符号
“麦茨套用语言学的思路,把影像视为电影的最小单元,这是对影像作为最基本电影符号地位的认可。影像符号,毫无疑问是电影符号学讨论的首要对象,所有这些符号大体上可以归入三大类别,即人物景象、实物景象和虚拟景象。”
茶文化、泰姬陵、富士山、瓷器等,为什么这些景物经常出现在电影中?笔者认为这些景物是特定时代、背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标识,因为对电影文本的意义生成有着重要的作用。2017年上映的国产巨制《长城》,导演张艺谋透过“长城”这一隐喻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的实物符号来表现影片主题,进而又选择了古代中国神话传说《山海经·北次二经》中的“饕餮”这一怪兽形象,虚构出饕餮攻城大军,成为守护长城的御林军乃至全人类的死对头。 长城在这里除了隐喻又是像似符号,因为电影的可视性,所以电影中的大部分符号都是像似符号,而这些符号通过像似的关系,也大大吸收了原始媒介所标识的地方色彩、时代色彩,它可以将观众一瞬间就带入特定的时间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欧洲电影做到了极致,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凯旋门等早已通过文艺、影像作品成了全世界人们心中的浪漫符号。
亚洲文化历史悠久,能够引起广泛认同的视觉景象符号众多,如何善于抓住并利用好这些符号而不仅仅是地点表示一般的昙花一现,是亚洲电影人需要思考的又一个命题。
(四)其他内在的心理、意识形态符号
亚洲民族除了外在的景物符号,还有广泛的、历史的存在有心理的潜意识认同,这些认同来自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近代所共同遭遇战争创伤,共通的宗教节日、神话传说等。正是这些潜意识下的认同在亚洲电影共同体的建构上,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传统农耕文化下的东方民族千百年来就形成自己的古代朴素唯心主义宗教观,佛教文化从印度发端,传之久远,世界上13个主要的佛教国家全部在亚洲,可以说佛教观念已经融入大部分亚洲人的生活中了。电影在这佛教宗教表达上,以印度和泰国较为常见。佛教文化渗透是泰国恐怖电影的独特个性,泰国恐怖电影《鬼5虐》《恶魔的艺术》《鬼鼓》等的鬼形象设定、内涵主题、拍摄场景、内容细节、声音元素和服化道具等方面无不渗透着佛教轮回观。与此同时,“宗教作为电影元素得以展现也是印度电影的传统,当代印度电影的特色在于:不单独展示宗教仪式而是将其作为人物生活的背景或是人物日常必然会经历的事件、节日等,人们在景观中生活,并依照景观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变化,与景观逐渐融为一体。”在影片Oh
My
God
中,导演为了突出表现民众对神灵的崇拜而着力表现各种印度教日常祭拜活动。开斋节、萨拉斯瓦蒂节、灯节等宗教节日,更是印度电影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符号。不止于此,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如《大闹天竺》《功夫瑜伽》《我不是药神》等从传统从教文化符号中寻求故事根源。
四、“泛亚洲电影”和“亚洲电影共同体”
(一)“泛亚洲电影”
有学者指出,“所谓泛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平凡化表达,换言之,即文化的亲民化表达。这种平凡化与亲民化是文化真正意义上蓬勃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从后现代影视艺术视角而言,泛文化要做到更有效地传播,还应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多元文化与多元表达的交融、调性年轻化与意涵时尚化的交融、人性光辉与人文思维的交融。这种智慧与人性的基于精神愉悦的交融输出,是泛文化交融传播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
在亚洲电影泛文化方面,2000年,香港导演陈可辛创建了名为Applause Pictures的电影公司,并很早就提出了“泛亚洲”的商业电影理念。可以肯定,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亚洲地区电影产业的加快发展。“泛亚洲电影的产业包含多种形式。其中包含了人才共享、跨境投资收益促增长、联合创作,透过发行和海外基建投资达成市场整合。最主要的还是要对亚洲导演进行投资,利用其在本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观众。在亚洲建立一个完整的电影发行体系,以此针对好莱坞,建立一套完善的应对策略,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
诚然,这种观点已经初具共同体的雏形,但仍旧难逃一个商业导演固有的思维定势,只关注到电影产业等资本运作,而没有去深入研究影响泛亚洲电影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由于亚洲各国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泛亚洲电影”这个大的目标很难在近期内实现。目前建立“泛亚洲电影”的条件还不成熟,能够建立整体的框架和构想,但很难涉及具体的拍片项目。因此,在市场没有办法进一步整合的情况下,可以先进行文化上的差异的弥补,首先形成一些基本共通的文化。
(二)“亚洲电影共同体”
根据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民族从来不是什么真正存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们一种群体性的主观想象,通过对一系列符号的认同,想象我们是一群人一类人。由此可以认为在地理上有一个亚洲,但不仅如此,几千年来还有一个很多人思维里的亚洲,这个亚洲就是观念性的存在,是古老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一旦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它就比现实中的亚洲更稳固更长久。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符号,是民族历史上长时间沉淀下来的代表性形象元素,具有高度凝练的文化内蕴”。然而在当下电影的亚洲符号表达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西方主流电影思维下浅显的亚洲元素,例如亚洲景观、亚洲演员等,这些举动并非是亚洲影像文化在世界电影文化话语权的提高。更多的,则是西方电影为赢取自身影片在亚洲院线的一席之地而进行的必然选择。例如,在好莱坞著名IP电影《雷神3》中,神域军队里竟然有一张亚洲面孔霍根来统领全军,导演让日本著名演员浅野忠信来饰霍根,显然是为了日本观众而考虑,并非叙事上的需求。如此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近年来亚洲电影人纷纷开始在好莱坞电影中抛头露面,但就目前来看,这些举动依然只是西方主流文化下披着东方文化的伪符号。因而在电影中,我们更应该抛开对亚洲传统文化符号的浅表理解,抛开一味地生拉硬套以文化噱头作为卖点,避免沦为美国全球化策略下的附庸品。
要知道,电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交流内部想法、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媒介,因此,只有亚洲电影内部通过相通的符号率先互相认同了,在审美和文化上达到一个平衡点,进而才能在产业化方面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从而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电影的广泛交流,扩大共同制作的规模,实现对好莱坞大片的有力制衡。在亚洲,可以制作高水平电影的印尼、马来西亚将来可以结合中国、印度、韩国等资本优势,尽早实现电影产业化。电影共同体的形成,还能有效地促进地区人才交流和资本流动,通过电影符号所建构的电影共同体可以极大地加强对地区影视的凝聚力。还应该指出,在这个电影共同体中,东方符号并不是一概而论,亦不是文化大国对于文化小国的一次“文化整合”,各种文化符号的选择应本着亚洲民族倡导的“伙伴关系”“平等原则”,注重“团体导向、关注家庭元素,以义取利、勤俭节约、敬业诚信等以柔克刚的文化倾向”,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可以预见,亚洲电影共同体的建构一定非一日之功,它应该是一个随着实践和探索而逐步深化的历史范畴。确切地说,需要一大批成功挖掘出亚洲电影符号的优秀影片综合体在大范围内引起关注和认可。它们共同体现亚洲历史、亚洲传统、亚洲精神,它们还需要拥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美学追求。希望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到亚洲电影共同体的建构,向世界展现亚洲最真实的一面,为亚洲电影发展做出贡献。
五、结 语
放眼世界,在习近平主席再度提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当下,电影这种“一切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艺术”(列宁语),一定会在世界加快发展融合中贡献不可估量的力量。终有一天,当亚洲电影形成了共同的认知,成为一个世界意义上的亚洲电影共同体,那么这个组织内部的效率就会极大地提高,借亚洲经济腾飞的步伐,电影产业也必将加速整合,绚烂多彩的亚洲文化一定能够在银色世界里演绎自己的影像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