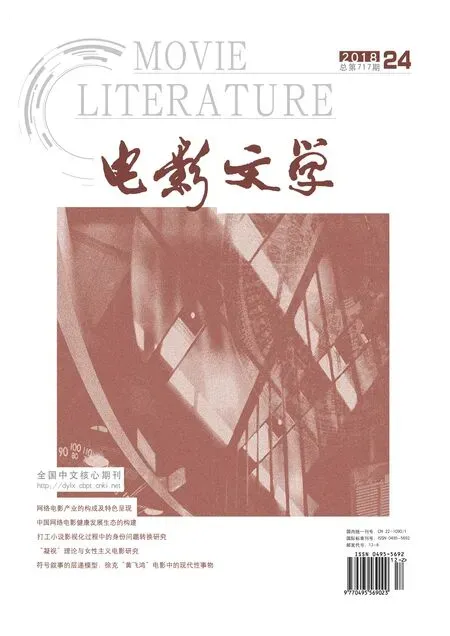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终结者》的暴力文化符号解读
魏 萍
(成都理工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7)
暴力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行为之一,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必然举动。在如绘画、舞蹈、文学等艺术中,暴力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而第七艺术电影也不例外,电影人不断在电影中对暴力进行表达,让其赏心悦目,有的也会在其中隐含道德批判。以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终结者》和《终结者2 :审判日》为例,电影中充斥着大量枪战、武打、爆炸、杀戮等暴力文化符号,既以一种合法化了的方式释放着观众的欲望,也引发着观众的思考。
一、《终结者》的暴力文化符号
(一)枪战
枪战场景给观众充分展示了枪械的威力,让观众得以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收获的刺激体验。例如在《终结者2》中,约翰在楼道中仓促地逃命。而T-800则从盒子中掏出一把枪,就在约翰误以为T-800要杀的是他时,对面却出现了同样持枪的T-1000,随即两人展开了对射,T-1000还打死了一个清洁工人,人中弹的血肉横飞和机器人中弹的毫发无损形成鲜明对比。
(二)斗殴和杀戮
拳拳到肉的斗殴与杀戮直接指向人肉体的受损,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极能满足观众的攻击欲望。例如在《终结者》中,T-800在经过油罐车的爆炸后,以机器人的形态追杀莎拉,两人在工厂里展开追逐,其冰冷的手伸向莎拉的场景令人极为揪心;又如在《终结者2》中,T-1000跳入莎拉母子所在的电梯厢顶,将手化为金属刃从厢顶捅下来,与莎拉母子仅有分毫之差等。
(三)爆炸与追车
爆炸与追车是商业电影中常见的大场面。如在《终结者2》中,少年约翰先是驾着摩托车逃命,不料T-1000驾驶着大卡车从天而降,眼看约翰马上就要被对方追上,T-800也驾驶着摩托车出现了,三人行进在狭窄的隧道中,险象环生。T-1000的卡车不断与隧道壁、障碍物等相撞,碰出火花,同时,T-800还一边单手开车,单手持枪射击。T-1000在卡车玻璃受损的情况下,索性用手拆掉玻璃。最终T-800单手抓住约翰,并打爆卡车油箱,在烈焰前扬长而去。然而不久,T-1000又以液态人的姿态从火中走出。整个过程极为紧张,足以令观众目不转睛。
这些都是商业电影中常有的暴力符号,它们具有消费时代观众需要的奇观性,并且体现了科幻片所应该具有的庞大、严谨的科幻体系,对传统暴力符号既有沿袭,也有拓展。如,在《终结者2》的结尾,T-800在杀死了T-1000之后,攀着吊钩将自己沉入滚烫的岩浆中以销毁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这个时间的地球上没有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机器人。随着身体的沉没,他最终向人类,也即约翰竖起了大拇指告别。这些都是属于科幻片的暴力,令观众耳目一新。
二、《终结者》的暴力正当化与暴力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终结者》系列中暴力美感虽然具有一定的暴力美学特征,即以暴力作为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并让暴力具有形式感,但是在本质上,它与暴力美学有着区别。在暴力美学中,暴力是一种美学选择,而几乎不涉及道德判断。但这显然有悖于卡梅隆的创作动机。只要对卡梅隆电影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他的作品在浪漫化的叙事以及诗意的暴力场面背后,通常都有着社会批判与道德劝诫意味,甚至为了达到说教的目的,卡梅隆不惜使用其他导演通常回避的字幕。这是卡梅隆与昆汀·塔伦蒂诺等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终结者》中,存在暴力的正当化与对暴力的批判。所谓暴力正当化,即赋予主人公的暴力行为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例如在《终结者》的开头,T-800赤身裸体地来到1984年,这时候,天台上有三个朋克打扮的小混混正在用望远镜看天空,这三个人在T-800到来之前就已经有过内部的暴力举动,其中一个人显然在争夺望远镜的过程中霸凌着另外两个。当T-800出现,并开口问他们要衣服以后,他们三个又误以为T-800是一个醉鬼,准备凭借人数的优势对T-800展开霸凌,其中一个甚至还掏出了小刀。可就在他们上去挑衅、殴打T-800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T-800在这部电影中是反派人物,但他的出手依旧被赋予了正当性,观众在看到小混混被打时,都会感到他们是罪有应得。
而暴力批判则在于,卡梅隆从来不回避暴力的错误性,暴力即使被与美感关联,它依然是残忍和痛苦的代名词。以《终结者2》为例,此时的T-800早已改邪归正,虽然他依然没法拥有人类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但是他的程序和意识中已经有了不能伤害人类的概念。于是在他冲进警察局的时候,尽管被警察打得面目全非,也枪口向下,不曾打死一个警察,在被楼外的警察围攻时,T-800也只是烧毁了一辆警车,其屏幕上会时刻提醒他:“人员伤亡: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更为冷酷无情的T-1000。这个冷血杀手机器人视人命为蝼蚁,尤其是当他要变身为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模仿的对象杀死,以免世界上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而使计划败露。这个机器人是不折不扣的反派,与T-800还能宣布“我会回来的”不同,他被消灭了。显然,卡梅隆对这个机器人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暴力的批判态度。在卡梅隆看来,暴力应该是有节制的,观众尽管从T-800和T-1000的对决中获得了娱乐,但是观众自始至终都应有着“邪不胜正”的信念。
可以说,卡梅隆尽管提供给了观众满足其趣味的、暴力的视觉盛宴,但是他无意让观众拥有一场暴力狂欢,一切暴力行为都是被高明地组织在叙事之中的,它们没有被“去污化”与“去痛化”,依然是应该被否定的对象,且服务于卡梅隆所想表达的主题。
大量科幻电影中都蕴含了暴力文化,尤其是在暴力美学大行其道的文化语境中,以科技的外衣来包装暴力更是一种常见的行为。而如果我们回溯卡梅隆拍摄于20世纪的两部《终结者》,或是将其与并非卡梅隆执导的《终结者》第三、四、五部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卡梅隆精心设置了电影中的暴力符号,并使其具有美感和十足张力,但是暴力从来就不是卡梅隆电影叙事的焦点,它不可能削弱叙事目的,也不可能弱化卡梅隆寄寓在电影中的道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