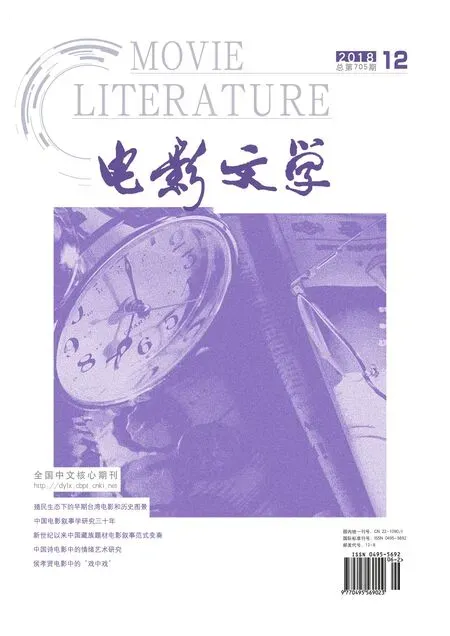政权更迭情势下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认同研究
周玉琳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孙慰川曾指出:“克拉考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比其他艺术手段能够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心理。”尤其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势下,民众心理会被移置于电影所要表达的纷繁之意中。在台湾电影发展进程中最常被大陆学者提及的词语即“国族”与“在地”。在新世纪后的台湾政治社会,国民党与民进党交替执政的情况空前出现,至此已完成了三次“政党轮替”(2000—2008;2008—2016;2016至今),反映在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观念也随着政治情形的变化呈现出具有差异的阶段性变化,台湾民众对待历史的态度通过电影媒介展现无遗。“对台湾历史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与台湾人的国族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政权更迭情势下的台湾电影中不难发现,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认同已有所改变。
一、重构主体,“在地”回归(2000—2008)
2000年台湾民进党代表陈水扁以微弱优势当选领导人,开启了长达8年的民进党主政时期。李扁二人对于大陆与日本的观念都在企图挣脱历史羁绊。在强调台湾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在政治层面影响了社会对于台湾、大陆、日本历史关系的重审。民进党对待历史记忆的不同态度改变着民众的思想风向,政治鼓吹的“台湾意识”与“全球本土化”进程让深陷身份认同危机的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趋于混乱,走上了消解历史的“寻根”之路。
“爱台湾”在电影界走出的第一步即在“在地”视野下对身份进行重建。2001年电影《10+10》中,由陈玉勋指导的《海马洗头》讲的是为了达到选择性的遗忘而洗刷记忆的故事,自欺欺人地否定甚至洗去真实过往,将自己设定的期望通过否定历史与构造想象以完成圆满,有意逃避历史的迹象已初见端倪。在对待大陆问题上,《五月之恋》(2004)将青春的忧伤议题置于迷茫的城市之中,用台湾乐队五月天的演唱会架起了哈尔滨少女瑄瑄与台湾少年阿磊沟通的桥梁,以此隐喻大陆与台湾的关联,也承认了两岸始终是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但更多的电影选择表达大陆的缺席与对中国情结的不明确性,例如《台北二一》(2004)中人们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蔓延在台湾都市之中,台湾青年男女在面对都市经济的不景气与面对大陆崛起时的没落形成强烈反差,来台寻根的日本人成为带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性人物,这反而拉远了台湾与大陆的牵连,表现了与日本的亲密关系,而大陆始终缺席;在电影《经过》(2005)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甲骨文、青铜器、二胡、太极拳被展现出独特的色彩,影片以中国传统字画——苏轼的《寒食帖》作为主要载体,却因其在历史流转中与日本的丝丝关联而着重表现了台湾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大陆人念念不忘的《寒食帖》在台湾当地老人耳中却闻所未闻,历史与文化的指向实属尴尬,割裂程度可见一斑;《练习曲》(2006)中的环岛脚踏车之旅“把台湾各群族的复数历史记忆和本土风俗传统巧妙镶嵌于沿途的风景中”,即使在影片中涉及了大陆元素,像是妈祖神像与“外省”老兵诉说历史,却不敢明确表示中国情结,只给出暗示性的隐喻指向与更多的空白。此时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对国族建构的兴趣,在试图摆脱权威的精神压迫后再无意提及“沉重”的历史,对大陆的构想从思乡变为他乡,反之用客观模糊的心理构想出了新的“母亲”——日本,企图在历史想象界缓解现代时空中的精神伤痛与身份危机。对“日本”情结与台湾自身主体性的强调,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台湾人民国族认同的信念。电影中对于日本的呈现是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母性依恋与暧昧的,对殖民历史的重构满足了当时台湾社会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及侵略暴行的刻意回避与淡忘。
“‘台湾意识’被逐步误读为‘台湾主体意识’,被异化为虚幻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爱台湾”口号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似乎是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暂行办法”,主体确定性的断层与政界影响,使台湾电影开始重构主体,急于寻找一个看似更加包容的日本“母亲”与美国“父亲”,作为具有“在地”性的“精神游子”,对“国族”态度的忽视使“认同”变得含糊不清,“地方认同”开始主宰电影媒介。
二、追寻民主,激发“在地”(2008—2016)
2008年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当选,陈水扁下台后民进党沦为“在野党”。台湾政坛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但政治斗争导致当时台湾政治、经济发展失调,族群矛盾升级。“政党轮替”不仅令民众与期盼中的安定与和解渐行渐远,而且也使台湾社会更加乱象丛生。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后与两岸来往更加密切,国民党亲近大陆的一系列举动对台湾社会民心冲击极其强烈,民进党则选择持续融入台湾社会,并与年轻世代结盟。此时的台湾年轻人基本是在1987年“解严”前后出生的,那时威权势力的施压已不复存在,在经历了民进党“去中国化”倾向的“洗涤”、全球化趋势对传统地理文化空间的消解,以及台湾社会后殖民思想的来袭后,其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愈发强烈,加之两岸频繁接触,大陆游客蜂拥而至,都使得不安感与危机感随之加深。
政治上的负面情绪激发了电影界“在地”趋向达到新高,电影开始侧重于重构台湾集体记忆,主张以自身特殊经验的挖掘来构成不同的国族想象。本土题材的影片更受青睐,甚至有电影工作者总结道:“如果想让电影获得票房收益,‘到现在为止成功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爱台湾’,‘要用台湾的演员、台湾人的个性和角度来看事情’,‘纯纯粹粹的台湾片’更容易引发共鸣;‘要欢喜爱台湾,不要悲情爱台湾’,这几年的票房数据显示,‘悲情爱台湾是一千万,欢喜爱台湾是一个亿’。”而且对于底层小人物与本地居民的讨论也成为确认本土认同的重要标志。
作为台湾电影的转折点,青年导演魏德圣的《海角七号》是2008年不得不提的台湾电影界大事件。这部影片扭转了往年台湾电影产业的低迷状态,创下了台湾华语电影历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被看作是台湾电影行业复兴的标志。《海角七号》将台湾本土青年与日本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分别放在当下时期与殖民时期呈现,对大陆的地位视而不见,但对于日本温情怀旧的暧昧态度显然割裂了真实历史,进一步说明了台湾社会中青年一代刻意回避日本种种恶行并乐于活在与现实相悖的想象空间之下。另一部“后电影时代”代表作《艋舺》(2010)在结尾处把对故乡的美好憧憬也归结到日本的形象上。“这些日本恋人或者日本故乡想象总是能够治愈爱慕他们的台湾男女的心灵创伤,对于急欲表明自身独特文化和族群身份的台湾来说,电影中日本他者形象的建构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化过程,也正是在国族认同上对中国进一步疏离的表现。”
“台湾本地居民题材电影的主题框架被设置于‘在地性’诉求之下,其中混杂了主流社会对异质文化的想象性期待。”《不一样的月光》(2011)从泰雅人落水女孩的故事引发人们对于家园的意义的思考;《赛德克·巴莱》(2011)将赛德克人的一段抗日历史真实地呈现。“必须肯定的是,台湾本地居民题材电影中所展现的本地居民的风俗习惯贴近实际,反映了当下本地居民族群面临的土地丢失、身份迷茫、文化重拾三大主要问题。也牵扯着台湾电影中一大重要文化母题——“原乡情结”。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关于两岸亲情的电影《面引子》(2009),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大陆青年被抓去台湾充兵,他们在台湾过完了后半生直到年老才有机会回到大陆寻根的故事。一改对于大陆历史避而不谈的态度,这部影片涉及了在台湾生活的“外省人”回大陆寻根,尽管有两岸话题但也仅是浅尝辄止,导演用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替换了深入探讨两岸和解复杂性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题材或者也可能关系到电影本身,影片在岛内上映后票房和口碑皆如石沉大海,对比《海角七号》的强大号召力与高票房,不可不说“国族认同”的趋势正在悄然让步。不论是《斗茶》(2008)中关于茶圣陆阳的传说与中国传统茶文化,还是《父后七日》(2010)中的丧葬文化,都是在强调台湾与大陆传统文化有差别,有异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台湾电影更倾向的是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2013年的纪录片《看见台湾》以直升机高空摄影方式,以鸟瞰的角度呈现了台湾各种景观,让观众能从全新视角了解台湾,对在地空间的关注使此片大获成功,更是把“在地精神”推向了高潮。至此,“在当下的台湾电影中已难以寻觅到关于民族国家的清晰表述或是认同指标,几近陷入国家认同失语的状态”。
三、理性转向,“认同”反溯(2016至今)
2016年民进党代表蔡英文当选,完成了台湾社会“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在此前多年的“公民运动”中,使民众似乎看到了前进的希望。蔡英文对“台湾价值”含糊其词、闪烁其意的解释,以及上台后频繁“空谈”,既不接受“九二共识”,也不尊重历史源头的行为,将与大陆的亲缘关系排斥在千里之外。根据台湾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任期两年民调仍然萎靡不振,在2018年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中,蔡英文的不满意度高达60.3%。台湾《天下》杂志表示,“蔡英文推行错误的政策导致两岸交流交往中断,已经让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发生变化,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历年最高。这充分说明,民意从来没有站在蔡英文及其所坚持的立场一边”。
政治引导思想,成长带出历史。青年人在经历了众多政治变化后有了更多理性思考,近两年在政治上出现的由青年人成立的新兴小党们都在自发为社会正义与反“独”发声。台湾电影以往的流行标志台湾青春片大量减少,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影片增多,电影人开始走上了反思与批判的道路。《日常对话》(2016)记录了导演对其个体生命的经验反思,与母亲共同面对过往伤痛,渴望通过追溯源头来给予彼此重新开始的勇气。用生活中琐碎化做解剖情感的利刃,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常对话,却时刻透露出对压抑人生的无奈。《只要我长大》(2016)以本地居民为主角,表现出几个本地男孩的真实生活状态,用清新自然的台湾风格引出家庭缺失带来的孤独。《白蚁:欲望谜网》(2016)在对台北绝望的都市想象下对边缘人物进行关注与心理探究。导演朱贤哲说道:“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长成一朵花的自由,要长成很奇怪、很丑的花也没关系,这是人的生存权利,只要不侵扰到别人,人们便无权干扰人家的成长与最后的状态。”《再见女儿》(2016)讲述了在北京生活已久的台商阿盛,在面对台湾的大女儿嘉欣涉嫌故意杀害大陆的二女儿刘恋的案件时的心路历程,一个牵扯命案一个发生不幸,影片在悬疑案情的框架下,用吸引人眼球的跨海峡家庭关系来隐喻大陆和台湾的紧张现状,表现了仇恨埋怨疏离终究无法解决问题,最好的结果还是爱与理解、宽容。《再见瓦城》(2016)用女孩莲青与少年阿国为了一纸身份想要在城市中得到“合法”认可而在城市的边缘徘徊,历经各自底层的体力劳动、吸毒、自残、卖身,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最终毁灭的故事,则再一次暗示了“身份”问题依然是萦绕在台湾民众心中挥之不散的终极母题。
台湾电影的尺度越来越大,对重口味惊悚片的探索开始成为主流,甚至出现了讽刺意味十足的电影。《健忘村》(2017)表现了裕旺村外来道士田贵通过“宝器”改写村民记忆与全村命运的故事,将记忆作为材料对人们进行思想实验,使用暗喻以喜剧的形式进行政治寓言可谓讽刺性十足。《血观音》(2017)中三位不同世代的女性在乌烟瘴气的社会中各怀心事,把人性的贪得无厌与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切人物都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人物的心理也是根植于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心中的,杨雅喆导演曾说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也正是如此,该片被评价为“太台湾”,太有当地特色。《大佛普拉斯》(2017)有着浓厚的讽刺意味,用一尊大佛展开剧情,片中底层人物、公路风景更接近台湾本土偏远地区所面对的情况,用荒谬的形式阐释了生命的无奈和悲凉,并以此进行社会批判。无论是《自画像》(2017)中压抑的政治环境与生活困境,还是《小猫巴克里》(2017)见证了“造神”到“神幻灭”的全过程,台湾年轻人热衷的自我成长断代史开始有了深度并加入了自身的思考,台湾不同群族对于“中国认同”与“台湾意识”的“国族想象”开始呈现分化形式。正如廖庆松所言:电影最后是人的问题。台湾电影的理性转向与对历史的辩证思考,使得国族认同的讨论已不再是简单的“是”与“不是”,虽然“在地”情节不可避免地在场,但电影界的主要关注点已不仅仅是整个大环境下的迷茫,更是有了对在社会中的人物个体更立体的诠释,接受立体人物的多面性历史开始成为探讨主题,对于以往“被蒙蔽的双眼”有了主动掀开遮蔽的趋向,国族认同的回升已是在所难免。
四、结 语
我们能从政权更迭情势下的台湾电影中窥探出的就是在新世纪初期台湾电影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后,已呈现出更加理性的趋势,电影人除了依旧会探讨身份母题,但更多的是开始关注自身、思考历史、批判政治社会。“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有着独立又开放的对仗,这是自我建构与多重交构的结果,更是传统和现代、历史与当下、东方和西方冲突交流的结晶。”
台湾的国族身份认同注定是流动的、混杂的,但能肯定的是,台湾电影“会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实利益的需要、未来愿景的变化,以及台海两岸统一进程的发展,不断发明其国族身份认同的新想象”。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实现历史和解与文化认同应当是台湾电影未来无法逃避的最终归宿。台湾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影作为“建构身份”的机器,隐含在台湾电影中的国族意识与国族认同观念也将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变得无法回避,良好的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社会同样也是重要的基石,我们期待着台湾电影在今后能更清晰地明确自身文化传承作用,确立自身毋庸置疑的国族身份。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