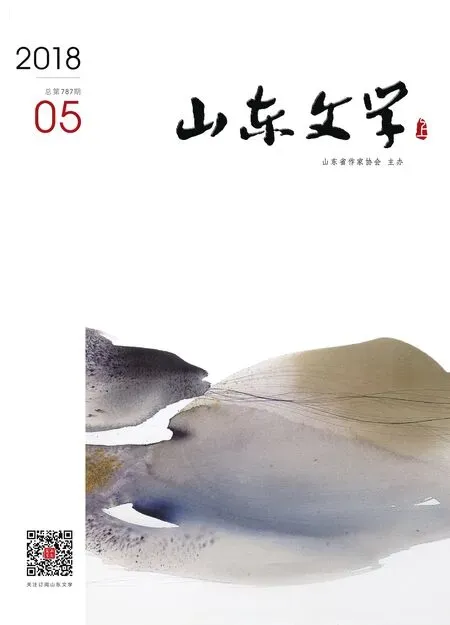永恒之前奏曲(组诗)
陈小素
在湖边
夏天的荡漾在此静止
几乎是一夜之间
西风就吹空了这里的蛙鸣、飞鸟
吹空了水草里的缠绵
冬日的寂寥里,只有捕鱼人
站在冰面上
手中的铁棍即将揳入水中
欲望真是个好东西,多么失措的年代
都有人耐下心来
在湖边,我看欲望在冰上开花
生命无处可藏
看湖边徘徊游荡的白鹭
失落的眼神里都是霾尘和荒草
它掠过湖面时,我看见它的翅膀
犹疑、盲目,在霾雾里
越来越远
小如针尖上的战栗
漫过风行荒草的凌乱
永恒之前奏曲
这些屋子密集而拥挤,像一个集中营
也像声音的排练场
液体的滴答声,咳嗽、呻吟、啜泣
避重就轻的劝慰,一颗灵魂飞升前
最后的呼嚎
他们有的已回到原初,正被上帝招回
有的在走廊上,狱囚一样走动
打探彼此的籍贯、家庭、年龄和儿女
让生活回到原貌,让幸福靠近本质
有的在向医生索要“安乐死”
就像一个孩童迷上一颗黑糖球
哦,上帝啊
他们的骨头,他们的心
他们由死向生伸出的手指头……
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中元节
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买路
带来冥钱、衣物、纸上的超市
人世间的奢华,他们都有
虚幻主义的好,就是可以相信
这些虚无的存在
让死者免于水火
让活着的人获得美誉与脸面
秋风起,荒草倾覆
越来越短的捷径
人生最大的通途
莫过于生与死对饮
虚无和虚无彼此安慰
在石膏山喝茶
悬于山腰的茶舍
垂立而下的崖
一只舍身的鸟
被放下的执念
那云雾笼罩下的人间真的是我的来路
那个上午,秋阳照着洞里的众生
也照着洞外的寺庙
一群逃亡一样的人,那些浸着汗水的脸
疲累而潦草
有那么一会,依着一面石墙
倦怠、迷离,仿佛就要睡着了
透过木质屏风的间隙
我看着他们在光影中慢饮
闲适的样子让时间倒退了几十年
他们轻如蝶翼,面如琥珀
清澈得像刚刚被泉水洗过
没有一个是来时的模样
在博物馆看一只锛
一只锛睡在博物馆的柜子里
泥石与瓦砾吻过的锋芒和倔强
如今都沉默不语
它垦出田地奉养五谷
它筑出石块砌成骨骼
我是它养育过的孩子
它凿出的渠道流淌成精血
它擦亮的时光填满了我的诗
如今,作为遗迹
一只锛沉睡在博物馆的柜子里
一束倾斜下来的光照着它的锈迹
也照着参差的缺口
英雄末路哦,隔着一块玻璃
我看见比死亡更沉的寂灭
比锈蚀更缓慢的毒
看见了被时间堵上的眼,和嘴巴
狐
我们谁是谁的化身
依着我的手,你一只脚踏着这人间
一只脚踩着身后的山林
活在传唱里的精灵
隐身在书里就是一截红袖
是挑灯伴卷的良人
落身于荒野就是一缕轻薄的魂魄
你雪色的皮毛, 那个染白我诗歌的夜
我们谁又是最悲伤的那朵
那些饥寒你替我受着
那些孤寂我替你忍着
当风吹起,更大的苍凉漫过
这个被叫做狐的女子
背负着往事,和你一样
咬紧着唇齿间的怨恨
在清霜里,越走越远
天涯山祷词
我看见鸟儿低飞,云朵低垂
石缝里落满草籽
滹沱河在阳光下缓缓流淌
我听见山下的人间日夜传唱着福音
石鼓日夜敲打大地的经卷
自此,天涯山风调雨顺、繁花葳蕤
心怀慈悲的人
将拥有比母语更可靠的祖国
来收留他的炊烟和羊群
眼里弥漫的忧伤将被乌云一起带走
男人喊他的乳名,女人亲吻他的额头
几十年光阴虚度
他还是那个未识忧愁的孩子
用他渐渐长成的喉结
和麋鹿一样的眼神
爱、做梦、缓慢地赞美
旧事是一粒寂灭的烟花
在涌动的人流中安下身来的女人
光影驱逐着身体里的黑、 骨头里的孤单
胸腔里横着一条逼仄的小巷
在涌动的人流中安下身来的女人
旧事只是一粒寂灭的烟花
有多少悲凉能被它照亮
眼前的阑珊正被风吹成虚空
在涌动的人流中安下身来的女人
像一个盲从
被那些幸福的面孔牵引着
仿佛每一道光环里都住着深爱的人
等我们老了
等我们老了,行囊只剩下皮肉
骨头弯曲,走路的样子像皮影戏
我们再也写不出诗,也不闻江湖纷争
我们只择水而居, 将房子筑在湖边
男人下棋垂钓,女人烧火烹煮
春天有开不完的花让我们糟蹋
夏天有采不完的野蕨供我们挥霍
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任乡野里的空气荡涤肺腑
也倾听那些失散的虫鸣,蛙声,掠过耳际的风
意兴阑珊时,就来一个月光诗会
一个人起头,一群人朗诵
意兴愈浓时,可歌,可舞,亦可饮
要允许口齿不清,允许忘词
允许将酒洒在身上,驱走我们年迈的气息
像一群贪玩的孩子,累了,眼睛睁不动了
就鸟一样散去
要允许老眼昏花,偶尔痴呆
或成心来一个恶作剧
允许扣错房门,也允许靠错灯下同样昏聩的人
谁和谁在一起都不要紧
反正我们都老了,那些哄人的话已不屑再说
再蚀骨的爱我们也做不动了
要允许其中的某一个犯懒,或耍赖
睡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
这没什么
就当埋掉一段过往,一片花瓣
山脚,水边,都是不错的地方
宁静得让人掉不出一滴眼泪
而剩下来的人一切如旧,看花,听雨
骨肉一样
每天晨起都玩一次报数的游戏
直到剩下最后的一个,无论是我,还是你
都要努力写下他们的名字
人世苍茫,他们怀揣着善,和美,匆匆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