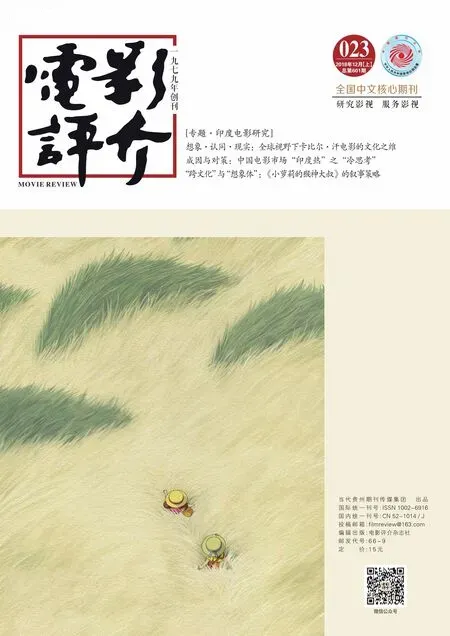历史剧《大秧歌》叙事图谱与文化透视
79集大型历史剧《大秧歌》,依托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激荡的历史背景为叙事起点,将电视剧的叙事视角落在一个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胶东小渔村虎头湾,铺开了吴、赵两大家族的族群争斗、爱情传奇、抗击日寇等复杂的历史故事。创造性地构建了由“点”布“线”构“面”成“体”的宏大叙事结构,从而形成了复叠而又清晰的历史脉络,造成奇峰迭出的艺术欣赏效果。把观众带进一个充满传奇性的艺术世界,显示了编导熟练、高超驾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合的艺术才能。
一、“点”的叙事设计
电视剧的叙事视点的主点是虎头湾,叙事散点是海阳县城、聚龙岛、蛇岛、寺庙等。虎头湾成为电视剧主要的发生场,吴、赵两家的世代恩怨情仇,主要人物海猫、吴若云、赵香月、吴乾坤、赵洪胜等生活在虎头湾。散点之一海阳县城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故事场所;聚龙岛是黑鲨与虎头湾恩怨的集结地;蛇岛成为海猫和岛主竹叶青发生联系的又一个散点。
这些主点和散点铺开了故事发生、情节展开的关键点,灵活地连接各个线索和故事的发生,既可以有效扩大故事展开的活动范围,增加传奇性的发生合理性,多点也就是产生出不一样的故事序列方向,根据方向的重点不同排列组合,使得故事富有传奇性和合理性的效果,造成观众视点的不断转换,从而调动观众的好奇心。“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达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这样,电视剧就有了情节繁富、传奇万般,吸引着观众的审美心理导向不断探究的引力,电视故事的传奇性就有了合理性的考量,不至于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感,每一集都设置了待揭开的谜团,也符合创作的魔幻和现实的融合要求,没有生硬、拖沓的感觉。
二、“线”的叙事运用
《大秧歌》故事叙事主线之一,是吴、赵两大家族的历史恩怨斗争。吴家和赵家本来是镇守海防抗击倭寇的军人,由于皇命留在了虎头湾繁衍生息成为两大家族,也因为历史恩怨两家规定互不通婚,老死不相往来,虽然同住一村,但两家分住不同的区域,造成了历史隔阂越陷越深,以至于两家族长带领族人相互争斗。为了挣脱出海权,每年要祭海斗秧歌,明争暗斗使得矛盾无法化解,正是海猫的出现给两大家族的纷争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就是第二条主线,海猫的曲折经历和复杂的爱情故事,把吴家赵家的命运又一次摆在了历史与现实境遇的面前,并且海猫的生命就是赵家和吴家私定终身的结果,将矛盾的两家联系在了一起,也就和另一主线吴家、赵家的矛盾连接起来,使得故事更加扑朔迷离,特别是海猫和吴家大小姐吴若云以及赵家侍女赵香月的爱情纠结贯通一起,成为叙述线的一翼。“经典好莱坞叙事的线性事理结构除单一时间向度的线性原则和因果逻辑之外,还包括叙事结构的完整性(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和时空统一连续性的幻觉。而戏剧性和巧合(叙事意义上的偶然性)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无巧不成书’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像《北非谍影》中亨弗莱·鲍嘉就抱怨前情人英格丽·褒曼说,‘世界一切城市的一切酒馆她都不去,偏偏要到我的店里来’。”海猫的出现就是解开吴赵两家恩怨的关键性钥匙,这个巧合安排的合理性在于海猫的特殊身份,是吴赵两家新血缘的纽带。
另外,《大秧歌》中的斗秧歌是另一条不可忽视的叙述线。编导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海阳大秧歌的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仪式,绾结一个或明或暗的线。大秧歌不仅仅是贯穿始终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五场极具文化审美特色的大秧歌表演,内容和形式的渐次演变,也显示了这种文化的仪式作用的演变。
在这些主线下面又衍生出小的辅线。吴家、赵家族长吴乾坤和赵洪胜命运的起起伏伏本身就是故事性非常强的辅线;品质低下最后成为汉奸的吴江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人物,本质的贪婪造就了这个变化多端、人性复杂的人物,他自身就可以联系一条故事线;林家耀独特的人生经历,或明或暗的线也把历史的视野波及到南洋闯荡中国人的命运以及林家与旧军阀的关系,虽没有展开,但可以看到有一条线在不断延伸,让观众去探寻未知;海猫的爱情人物吴若云、赵香月、苏菲娜、竹叶青又各自成立了一条条辅线,本身就是很好的故事链条;还有日本人三浦侵入虎头湾的传奇故事与吴天旺交织在一起等小故事链辐辏成更大的故事链。
三、“面”的叙事铺排
《大秧歌》的主要叙事面是由以上叙事点与叙事线结合的历史面与现实面的铺排。电视编导选择了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目的就是让观众既能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了解历史,又可以增强电视剧的艺术真实感。“真实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合理搬演的尺度在于是否是生活本身的常态。要尊重生活本身,削弱人为戏剧化、故事化的比例,不能影响再现事实。”因为历史剧审美艺术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不是随意的搬演和编造历史故事,要有真实的历史来支撑。编导就是把胶东半岛的抗倭历史、昆嵛山根据地、八路军胶东纵队、地下战地医院、日军进海阳、游击队用地雷炸日军、1942年冬天日军大扫荡这些最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写进了剧情,使得电视剧历史容量增加的同时,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夏仁胜说:“《大秧歌》来自生活、来自基层、来自胶东抗战历史,并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胶东红色文化,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经过艺术化的处理,把这些真实的事件通过特定的叙事点和叙事线穿插在一起,构筑了叙事面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历史剧的厚重和真实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既有历史长度、又有广度的覆盖面的艺术空间,增加了电视剧剧情的容量,并可以不断将戏剧冲突引向深入。
编导在利用这些真实历史故事作为构筑历史剧的各个叙事基本面,用虎头湾这个主点和吴家、赵家这个主线,在主要人物海猫这个行动元素参与下完成前后左右上下勾连,绾结整个叙事的点—线—面—体的整体构造。将主点、主线、主面建构成宏大故事的主体框架,整个历史剧在观众眼里就是一个活动的、可以移动的传奇旋转体,造就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审美效果。真实历史故事打造的叙事面共同组成了《大秧歌》的整体美感,避免了电视剧在不断行进中出现错乱、重叠、头绪混乱的现象。有助于观众在不断生发的故事点推动情节的转换,因而出奇、出新、出彩的电视叙事结构是电视剧必不可少的手段。电视编导可以根据这种结构安排故事的分段开端、高潮、结局,在更大的故事冲突、高潮、结局中自由移动。“影视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故事信息在剧中人与观众之间的选择与分配的艺术, 意味着编导必须掌握把不同信息选定何时( 在剧本开端、中部或结尾)、以何种方式( 对话、画外音、闪回或动作背景)传达给观众, 可以和盘托出, 也可以透露局部信息, 或者只是一些相关信息,扣发另一部分信息直到必要时候才宣布。”
同时,历史剧《大秧歌》这样庞大容量的故事网络,处理好主线与辅线、魔幻与现实、爱情与仇恨、抗倭与抗日、叛徒与忠诚、家仇与国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既要铺排具有一定历史厚度的时间、空间跨度,又要将观众带入到传奇的合理性世界,不完全靠创造传奇的情节和多样的故事链来完成,要革新一般叙事的结构特征,必须处理好点、线、面的关系。首先,是处理好叙事视点。正是布点的成功,使得故事戏剧性冲突造成悬念,吸引观众不断探究;其次,是编导革新叙事的以往结构方式。创造性使用这种点—线—面—体式组合体,观众可以在“奇”中求“正”,故事情节的“传奇”性统摄在立体叙事的“正”上,不至于感觉是编导故意创设的“传奇”,是合情合理的逻辑“传奇”。只有“传奇”依附于历史故事的“正”,才使得观众信服,感到审美“奇”感符合实际,符合艺术真实性。这也是《大秧歌》并无附会之嫌、了无痕迹、不着笔墨但笔墨自出的艺术之境。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准评价《大秧歌》所言:“百花齐放是繁荣文艺的必由之路。电视剧创作的更大繁荣也需要鼓励各种叙事方式的自由竞争。当然,每种叙事方式在文艺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分量,都是由相应的作品的水平来支撑的;任何一种叙事方式在新的时代能生长出多少新的生命力,则取决于相关艺术家在运用这种方法中有多少开拓和创造。”
四、魔幻现实的叙述手法追寻古老中国文化的“根”
(一)冷静展演古老中国的文化之“病根”
《大秧歌》编导用魔幻现实的艺术手法追寻古老中国的文化之“根”,这个“根”是其中的“病根”,是阻碍民族进步的国民“劣根”,愚昧无知、盲目信仰、缺乏科学的“根”,生长在这个古老中国的病“根”需要斩断和根治,赓续文明之“根”,来疗治中国的精神之“疾”。编导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所以,电视剧从懵懂无知乞儿海猫开始,揭开了魔化与现实交织的叙事。海神娘娘就是人们心中尊崇的充满魔幻的神,它主宰着虎头湾的命运,主宰着大海。“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寻根文学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土化的发展策略,致力于寻找传统文化资源,重构新时期文学的国家话语。”《大秧歌》主旨就是通过追寻中华文化之根来启蒙大众,认识文化之根里的弊端。
整个电视剧就是通过海猫寻根的视角来创设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海猫寻根恰好是祭神出海的日子,直指古老的祭海神娘娘仪式,并且开始打破这个古老仪式的合法性,引爆了向传统文化宣战的引信。事实上,每年这个时候争夺出海权是吴、赵两家不变的规矩,凭据就是大秧歌比赛的获胜方可以优先出海打鱼,不知就里的海猫也因为寻找生身父母而冒犯了这个祭神仪式。在虎头湾的全体成员看来,触犯了海神娘娘,破坏了几百年的老规矩,是一个该死的人,特别是赵家族长的亲妹妹赵玉梅认下了儿子海猫,这个特殊的场合无疑石破惊天,平静的虎头湾沸腾了,一系列悲剧就此开始,由此海猫的寻根认祖就和编导的文化寻根以此契合在一起,彼此交结发展,也恰恰揭开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是阻力重重、流血牺牲。内在的传统文化力量的魔幻合法性和新生文化力量的现实冲击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推进电视剧情节不断发展,成为电视故事情节的内在推动力。随着电视剧情的展开,海猫的生身父母双双寻死,海猫被沉海后死里逃生,被赋予魔幻的海神娘娘所救,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与新生文化的矛盾碰撞所致。
由此开始了虎头湾动荡的岁月,也恰恰是海猫的认亲,揭开了革命虎头湾宗法制度统治的序幕,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艺术缩影。“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则是“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依托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将现代主题的启蒙与革命引向深入,打开了电视剧阔大叙事的历史序幕。
(二)魔幻意味下的封建宗法制度
《大秧歌》编导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寻根,重拾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崇高或愚昧或血性的国民性,希冀达到深挖国民性在虎头湾这个中国封建浸染的小渔村的现实反映,也是瓦解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愚昧”“封闭”“阿Q”的国民劣根性,启蒙民智。
艺术创作的落脚点,恰恰是一个普通的渔村和一群普通的人,地域文化浓厚的胶东代表着古老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典型性的宗法社会在两大家族不断上演,而且也面临即将崩塌的命运。“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地域的独特性也是民族文化共性的外在显现,虎头湾是千千万万中国村落的代表,这里上演的宗法制度“病根”是整个民族的“病根”。藉此消灭这个“病根”来清理保守的宗法制度给人民精神带来的戕害,表明反对精神的奴性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吴、赵两大家族互不通婚的愚昧约定,不知扼杀了多少相爱的男女。海猫的父亲吴明义和母亲赵玉梅偷偷相爱、生子、被骗、认亲、双双殉情自杀,是封建宗法的强大力量的“胜利”,也是封建宗法泯灭人性的“胜利”,可见传统“恶”的可怖与残忍。面对突如其来的父母自杀殉情的巨大变故,让“启蒙者”海猫明白这个该死的宗法制度的可恶、可恨、残酷,决心寻求破坏这个制度的革命道路,这也是海猫走向革命的必然结果。海猫首先自身对抗着这个“愚昧”的约定,勇敢地和吴家族长的女儿吴若云相爱、相知,冲破了世俗封建的力量,用自己的生命践行革命。
将主人公海猫置放到魔幻的世界里,造成情节变幻莫测的效果,也使得故事的传奇性得到加强。可以看到,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海神娘娘是魔幻世界的精神符号,海神庙是魔幻世界的物质符号。精神符号海神娘娘不时在画面中出现,不是实体的海神娘娘,而是神奇的、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支配者这个宗法制度覆盖的渔村,没有人看见过海神娘娘,一些人说看过,但又没有说出海神娘娘具体的样子。海神庙里供奉的那个海神娘娘是一个想象的图画的现实雕塑、金身的塑像,也是人们想象的化身,几千年就这样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结语
《大秧歌》这部宏大的历史剧,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叙事头绪繁多,线索难以处理和把握,必须有一个高超的叙事设计能力才可以驾驭。这就要求编导善于使用合理的叙事方法、叙事技巧和创新叙事模式才能够完成。以往大型历史剧出现叙事繁琐、内容重复、叙事混乱的毛病,使得观众不得要领,引起审美疲劳,兴趣丧失。所以,要设计合理的叙事模式来支撑大型故事,实现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完美结合。
《大秧歌》放弃了单线发展的叙事模式,创造性地使用点、线、面的立体构造原理,设计整个故事情节的全面推进,点与点相连,线与线相交,面与面相合,完形了整个历史剧整体效果,使得点—线—面环环相扣、逐步深入。观众走进电视剧的视点,看到的是一个传奇连接的根根故事线和情节线,这些故事、情节线构成了整个大大小小的故事面,这些故事面又有机构成了整个历史剧的宏大历史体。巧妙的设计实现了审美的艺术需求,观众不断领略传奇性构思,并不感觉故事情节的突兀,因为这些点—线—面有机成体、互应互联、串联通达。多角度、多线头、多层面展开,使故事情节紊而不乱。造就了观众不断探究和领略传奇性的效果局面,适应电视剧吸引观众审美需要而不断创造吸引点,将观众的审美需求不断引向深入,这些巧思妙想是叙述创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