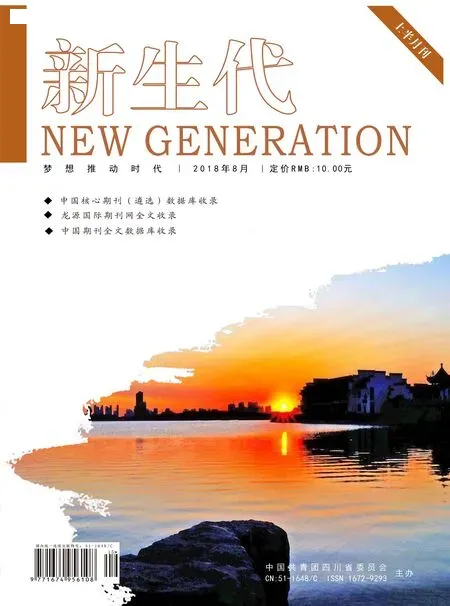中国明代文人画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色彩观对比研究
武洁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475000
一、中国明代文人画的发展
中国明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发展时期,在时间上是几乎同时存在的,但在这同一时间里,就艺术作品比较而言,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意大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绘画色彩观。艺术都是以有限表现无限、言说无限,或者说就是超越有限。中国的文人画,强调的是“无色”,所谓的无色其实是以画面的白和墨汁的黑来作画。画面中只有黑白两色,再没有其他别的颜色来表达主张抒写胸中之意的写意之路。
在明代的画坛,其实并不只是黑白两色。明成祖朱棣对美术十分重视,试图效仿宋代简历翰林书画院,推动宫廷绘画的发展。明代文人画色彩观为何多为黑白呢?这和当时的政治高度集权也有一定的关系,高度集权的政治需要在各个领域建立严密森严的等级制度。若说前面这点是客观因素略微有些牵强的话,其实文人画家从主观上也并不想在画面上使用更多的颜色。当时的颜色并不像现在的颜色一样获得的方式很多,人造的合成颜色价格低且与天然颜色差别不大,明代时的颜色多需要画家自己研制,这既需要熟悉颜料的特性又需要耗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而笔墨纸砚则是每个读书人都具备的文房四宝,随处可取,不需费心,如此中国文人画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色彩观,即仅存于黑白的色彩观,以墨色为主,彩色只为“补笔墨之不足。从视觉心理上讲,“任何视觉刺激图式,最终都倾向于被看成是在给定条件下最简单的图形。”人的眼睛相对于较复杂的形状和色彩更容易接受简单的,就这样文人们为了无色的山水画发展出了许许多多自圆其说的理论“墨分五色”“水墨最为上”等等。
二、文艺复兴时期色彩观发展
在中国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富商们需要显示自己的身份,争夺话语权。观念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中国人接受文人水墨画也是自魏晋以来慢慢养成的视觉习惯,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题材以及色彩观大部分还延续着中世纪的宗教色彩。
比如说文艺复兴三杰都创作了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画作,达芬奇创作了《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创作了圣经故事穹顶画《创世纪》,拉斐尔也创作了许多以圣母子为主题的画作。即使都是表示宗教题材的画作,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用色比较中世纪的更为大胆。如中世纪时,圣母子只能穿着红黄蓝三原色的服装来表示人物纯洁高贵的身份。而在拉斐尔的《坐在椅子上的圣母》中,圣母居然披上了绿色的披肩,这在中世纪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而出现这种现象,便是当时人们思想解放,开始关注身边的人的意识表达。画家画中的圣母子不再是冷冰冰的天神形象,而成为了出门就能见到的和谐美的农妇与婴儿。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画的背景不再是中世纪时的神明的金色,而变成了更有空间感的风景或者暗黑。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来自自然:“自然是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简化的背景,更顺畅的使观者把目光聚集在画面的主体人物身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画家虽然已经开始表现物体的转折、穿插的体积感。在肖像画的用色上也更贴近实际,宗教画的用色更接近于人的本身固有色。但当时的画家并没有深入描绘过环境色及反光,所画的画作中的颜色往往是一种固有色的身材变化,画出的画更像是一幅结实的素描的上色完成稿。
三、文人画与文艺复兴时期色彩观差异
反观中国明代文人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色彩观,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画比起真实地反映自然,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精神需求,他们在开始思考、理解世界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则开始注重科学性,绘画在各种科学理论的支持下,发展的更为璀璨。
不同的色彩观的产生都是由各种条件互相影响形成的,中国美学思想所讲的“意象”,都与“意境”以至“境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诗之至处”,它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万物一体”即显隐之综合为一。这种能引人进入此种境界的艺术,比起模仿性艺术和现实典型之艺术来,我以为应居艺术之最高峰。我们今天的美学应继承中国的这一思想传统,以提高境界为旨归,最高目标也应是使人高尚起来。因此画面中一切是要合乎自己心境便好,作为初期是文人墨客的信手随笔所以并不会很注重画中色彩的探究,追求自己最简单的颜色来完成整幅画面。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资本主义慢慢兴盛,画家多为职业画家,人们相信术业有专攻,画家们也会穷其一生研究探索绘画的更深含义,因此更容易产生更丰富的绘画色彩观。不管是庄子还是当代的的简化美,看似两种毫无交集的思想或者说审美方式,细细道来是有相通之处。
结语
万物一体的境界是超越有限的意识所无穷追求的目标,在文化全球化和全球地域化的背景下,对美学的研究就不能一味地限定在某种传统之下,要扩展美学研究范围,加深中西方不同的美学思想、甚至艺术文化交流,“因此,在当代美学研究过程中,开放的态度与多维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审美意识中“不在场者”在“在场者”中的显现实际上就是通过想象力把在场与不在场结合为一体,人能在审美意识中体悟到与万物一体,这就是一种崇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