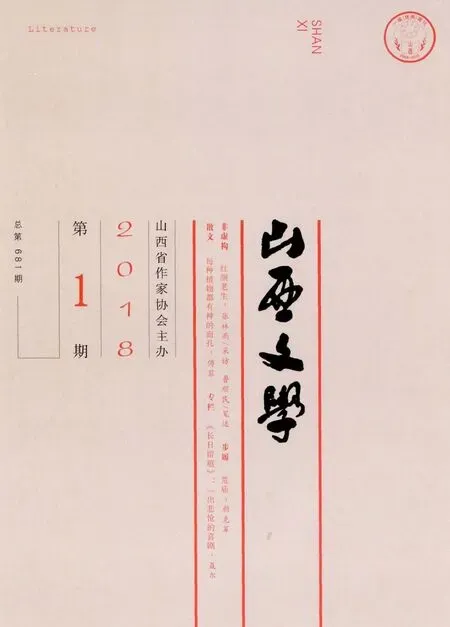每种植物都有神的面孔
傅 菲
葱花白薄荷花紫
葱切成圆末,撮一把,撒在汤面上,和煎黄了的鸡蛋,以及八九根红椒丝,像不像四季盛在一个青花碗里呢?杜甫写过组诗《绝句》,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语文老师打趣地给我们讲解,说,杜甫不是写雪景,而是写一道菜。我们多好奇,问,什么菜。老师说,葱末咸鸭蛋。
葱从来不是食物谱系中的主角。即使种植的地方,也是在旮旯地头地角。种白菜,种荠菜,种辣椒,地头空小块阴凉地,分株移栽几株葱,浇上水,撒一些草木灰,过个三五天,葱发出细叶。在菜蔬类,葱芽叶至美。一般的植物在发芽叶初始,青绿或黄绿或芽白。葱确是滚圆发绿,像条青菜虫蛹。细胖,中空,油绿,在早晨凝结着露珠,亮亮地闪着光。浇水三次,葱有了半截筷子长。做汤煮面烧鱼,葱是首选。葱有分葱 、楼葱、胡葱、黄葱 、地羊角葱、大葱、小葱、沟葱 、青葱、老葱、香葱,南方人通常吃香葱。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杜甫在《赠卫八处士》写韭菜。时代动荡,有一盘韭菜吃吃,够美好了。但我每次读这首诗,有一种错觉,似乎写的不是韭菜,而是小细葱。葱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鳞茎单生,圆叶筒状,随便找一个阴湿有泥的地方,葱也四季葱茏。有些人家,葱不种在地里,栽在阳台或窗台或矮墙上或矮屋顶的花钵里,花钵是个破脸盆或破土缸或破扁篓,装上肥泥,不用施肥不用浇水,满盆浮绿。临时割葱,下到汤碗里。葱割了,过不了几天,又发叶,生生不息。一钵葱,我们一辈子也割不完。
我是很喜欢吃葱的,看见细香葱,舌根生津。原先住白鸥园,八角塘菜场有一个老农,密密的白胡茬,围一条粗布围裙,挑一担竹萁,来卖葱。葱叶短短,滚圆,绿得发亮;葱蔸白白,饱满,沾满了黑色的草木灰。老农手上握一把割葱刀,坐在矮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是他熟客。他敲敲旱烟杆,捏着细葱说:“全草木灰种,香得凶,嫩得凶,找不到比我更好的葱了。”我信。有时我买一斤,分做汤两餐吃。汤上浮一层葱末,像荷叶田田,鱼戏蝶舞莺飞。我小孩看我吃白菜一样吃葱,摇头。没切的葱,扔在窗台一个空沙罐里,忘记了,过了两个月,清理沙罐,倒出来,葱叶枯萎了,葱蔸却发出了细叶。窗台上有一个茶叶筒,一直也没扔,我把葱塞在筒里,活了五个多月。
有一次,徐鋆说,他阳台也种了葱,可不是细香葱,大叶葱不如小叶葱香,武汉找不到小叶葱。第二次,他来上饶,我给了一个纸包他。他说,是什么。我说是小叶葱,你带回武汉种吧。神不神啊,几百公里,带细葱回去?他说。当然啊,细葱放在手提包里,又不碍事,带回去种吧。他把细葱塞进了手提包。我估计他半路把细葱扔了——除了我这样的人,谁还会带几百公里的细葱回去呢?我是一个多么吝啬的人啊,切下来的葱蔸,我也舍不得扔掉,放在早上泡起来喝,撒几粒盐花,明眼补气益精,驱寒,预防感冒。泡水喝还吃不完,便和鲜红椒一起,腌制,作下粥菜。
镇里有很多农人,去上海包地种小葱卖。我表哥水银有几年不务正业,生活很落魄。他叔叔种了二十多年的葱,对水银说,你要不来上海,一起种葱,一亩地一年可以赚八千来块,夫妻种十五亩地,除了吃喝,一年赚十几万还是可以的。表哥带上被褥衣物,去了上海。可过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我二姑发火,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人,一亩地赚八千,你也不去赚,你要去打抢,也没那个力气。水银说,赚不了三个月,人都要抬回家,种葱比打铁累,早上三点起床拔葱,洗好,扎起来,赶到菜场卖,晚上睡菜棚,蚊子多得可以吃人,铁打的人才可以赚这样的钱。
葱有辛辣味,少虫灾。葱价也高,过年的时候,镇里卖二十块钱一斤。种葱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比种白菜好。我母亲便怂恿我哥哥也种一亩葱。我哥哥怎么也不答应,说,葱又不是菜,只是佐料调味,哪有把一盘葱端上桌当菜吃的。我母亲说,养牛把人养傻了,像头牛,走路不知道转弯。
很多人以为香葱是不开花的,一年四季随时割随时长。其实香葱开的花,白如飞雪。冬至后,寒露成霜,早晨的大地一片银白而灰暗。稀朦朦的太阳像一块毛豆腐。霜越厚,葱花越白。花葶圆柱状,中空,中部以下膨大,伞形花序球状,多花,花丝锥形,花柱细长,伸出花被外。花伞撑在一茎上,像一个梦。冬日,原野肃瑟哀黄,溪流枯瘦,阡陌如死去的藤蔓。一片深绿的地头,一层白花被风吹得轻轻招摇。哦,那是葱花。到了春分,花结成了颗粒般的青籽,山雀开始孵雏鸟,叼食花籽,呆头呆脑地吃,吃得肚子发胀,雏鸟长出了麻黄色羽毛。
在矮屋顶破土缸,和葱一起栽种的,还有薄荷。薄荷在入冬之前已落尽了叶子,暗紫色的杆茎已经变得麻白。薄荷七月开花十月结籽,霜后凋谢。花为淡紫色。薄荷如清雅故人,给人凉爽。确切地说,和邻家女孩差不多:挺拔,婀娜,温雅,娴静,穿青蓝色的布衫,带球形帽。在南方植物里,还有一种植物给人清凉之感,但大多数人不识,叫腐婢。腐婢的叶子采下来,用纱布包起来,手搓揉压榨,汁液入碱水,凝结,便是柴豆腐,拌白糖或砂糖,入口即化清凉无比,醒酒解毒佳品。薄荷也叫仁丹草,解毒解暑,是一味常用中药。
事实上,薄荷是无人栽种的。屋角墙角,薄荷和杂草、洋姜长在一起,三月之后,一支独杆拔节一样上长,半米高分丫,叶子婆娑。雨落下来,叶子抖一下,水珠滑落。无论雨有多大,激烈狂暴,薄荷不会被摧残。和箬竹差不多。我家楼下,有三株薄荷,长在一棵枣树边。有一次,暴雨下了半天,雨声如鼓,路面被水淹没,哗哗哗,盖过了台阶。家中停电,我站在窗下看雨打薄荷。雨水一遍遍地滚过它的身子,它摇一下,又直条起来,叶子像鳞片。
鱼,我常买。买了鱼回家,在楼下,顺手摘几片薄荷,洗净晾在砧板上。中午烧菜了,薄荷叶卷曲萎缩。这是我见过的,最易干枯的叶子,两个小时,毫无水色。薄荷去腥,芳香,是烧鱼必备的调味料。也可去冰冻味。去年,我去浙江温州,买了二十条黄鱼二十条鱿鱼回来,备给我女儿吃。女儿说,鱼冷藏了,有冰箱味,怎么烧都会变味,不好吃。怎么保存呢?饭吃完了,我想出来了。我把鱼抹上细盐,鱼肚里塞几片薄荷。过了一个星期,我烧黄鱼,问女儿:“冰冻味,有吗?”我女儿惊奇地看着我,说,和鲜鱼是一样的,没杂味啊。
薄荷叶烧鱼,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薄荷叶炒黄瓜、炒豆芽、炒丝瓜,都是十分适合的。水煮豆腐,是家常菜,放几片薄荷叶别有风味。薄荷还可以煮粥。粥煮好了,打两个鸭蛋下去,调稀,薄荷叶切丝,撮下去。这是很多人没吃过的。
有很多动物,要么很腥,要么很膻,生姜是无法解决的。薄荷可以。薄荷叶、山胡椒叶、酸橙、姜,和动物肉一起焖,腥膻全无。
小时候,我吃了太多的薄荷,当药吃。我的小腿,只要被露水打湿了,会发痒,直至溃疡。天溽热,我也是穿长裤。可长裤无法遮挡露水。上山砍柴,下田割稻子,露水深重,打湿长裤,便裹在小腿上。到了中午,小腿发痒,红斑一块块瘆得我发慌。看过很多医生,都说是湿疹,涂红汞或药膏便好了。我的小腿,整个夏天都是红的,像条赤链蛇。有一次,来了一个凤阳婆,来村里行医。凤阳婆背一个白布的米袋子,说我们听不懂的话。她看病不收钱,收米。看一个病人,她收一升米,倒进米袋子里。她在我家里,借住了十几天,见我坐在门槛上,给小腿抓痒,皮肤被抓出血丝。她给我开了一个偏方,说,用薄荷包紫苏籽,碾碎,中晚各吃两勺,吃三个月断病根。我祖父收了一畚斗的紫苏籽,晒干,用布袋存放在谷仓里。我祖父每天中午也不睡,坐在青石板上,碾紫苏籽。我整整吃了半年多,病根也断了。
上元节之后,薄荷开花。花从叶子间的节上,云霞一样浮现。
轮伞花序腋生,轮廓球形,花冠淡紫色。秋阳一日比一日羸弱,如慢慢浅下去的水。而薄荷花日日繁盛,像一群火烈鸟飞舞。这个时候,薄荷叶多了纤维,也无人采摘了。暮秋,薄荷光秃,寒风又一年来临。秋风真是个好东西。是时间最锋利的刀。
而葱继续油绿。它躲过刀锋。
葱和薄荷,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命运就是担当盘里的配角。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忽视它们,甚至彻底遗忘它们。它们是滑稽演员。有很多东西,是恒定的,难以更改的,如世俗的口味。口味就是味觉的价值观取向。
即使是配角,也是深受人喜爱的。
溪野枇杷
第一次知道枇杷,是在八岁。端午,我走亲戚。亲戚在高山上。我母亲说,你去一次山里吧,你敢不敢去呢?我说,我敢,给我一根棍子,我什么也不会怕。我母亲笑了,露出一口石榴牙。她把扫把棍脱下来,给我,说,棍子可以挑两挂粽子去。一挂,十个,一头挂一挂,我上山去了。那时短粮,山里人更缺吃食,给两挂粽子算是很重的情了。临出门,我母亲交代我:“五月黄枇杷,六月红麦李。回家的时候,记得摘一袋枇杷来吃。”
山上人家,我并没去过。沿途都没人家,爬一座山,深入一个山垄,翻一座岭,下坡,到一个深山坳,便到了。山垄以前去过好几次,随大人去砍柴。山垄经常有豺出没,伸出长长的舌苔,尾巴垂到地上,眼睛放淡绿色的精光。到了亲戚家,正午了。矮小的土屋窝在几棵树下。屋前有一口水井。水井旁有一棵树,挂满了黄黄的果子。亲戚随手摘了一碗果子,说:“枇杷正黄了,你吃吃,鲜甜鲜甜。”剥开软皮,浆水流了出来,吮在嘴巴里,口腔凉阴阴。还没开饭,我便把一碗枇杷吃完了。枇杷是小枇杷,蒂上有灰色的绒毛,皮色如咸蛋黄,肉质如金瓜囊。吃一个塞一个,吐出深褐色的硬核,如茅栗。
拎了一布袋回来。我问母亲:“核可以种出枇杷树吗。”母亲说,那当然,哪有核不出芽的。我把枇杷核收集起来,埋在屋后一块菜地里。过了两天,一个老中医给我祖母看病。老中医是祖母的堂弟,戴一副老花眼镜,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懂的。他常来我家吃饭,说话轻言细语,温文尔雅。我说,我种了枇杷籽,会发芽吗?老中医说,舌头舔过的果核,都不发芽。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世上最毒的东西,是什么吗?是舌头。舌头比蛇毒还毒,没有比舌头更毒的东西了。舌头舔过,毒液进了果核,果核便成了死核。死核是不会发芽的。”我很是伤心。我不该把枇杷全吃了,至少得留十几个,连果肉一起埋在泥土里。
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问了很多人:“舔过的果核会发芽吗?”被问的人,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怎么问这个问题?炒熟了种子,不会发芽,可舔过的果核会不会发芽,谁知道啊。”
当然,我是相信老中医的话。第二年,果核也真没发芽。山上的亲戚来我家,我说,种了那么多枇杷籽,一颗芽也不发。亲戚到菜地,看了看,说,不发芽,不是因为果核从嘴巴里吐出来,而是这儿积水,果核全烂了,怎么发芽呢,下次来,带几棵苗给你种。可能亲戚忘记了,始终也没带苗下山。
在孩童和少年时期,我对植物发芽,抱有浓厚的兴趣。豆子发芽,红薯发芽,马铃薯发芽,洋芋发芽,荸荠发芽,藕发芽,谷子发芽,麦子发芽,白菜发芽,樟树籽发芽,我都十分细致地观察过。发芽,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物了。我还采集过很多花籽,放在破脸盆或破瓦罐瓦钵里,摆在院子的矮墙上,看它们发芽。如野菊、指甲花、酢酱草、三白草、紫地丁、野葱。瓦罐里,装满了湿泥,把花籽撒上去,盖一层泥,浇水两次。花籽每年都发芽。我还玩恶作剧,把扁豆放在火柴盒里,埋在瓦罐,也发芽。可枇杷籽发芽,怎么那样难呢?
村里很少有人种枇杷,不知道为什么。
我外出读书第三年,二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表弟种的时候,兴兴地说:“这是余姚的枇杷,个大,味甜,村里没人吃过这样的枇杷。”我说,一棵枇杷,哪有那么神秘,个再大,也不会比梨大,再甜也不会比红柚甜。表弟说,没有梨大也比棉枣大,肯定比红柚甜,吃起来和蜂蜜差不多。我说,比蜜甜,那不好吃,比蜜甜的东西,就是苦了,甜的极限就是苦,或者酸,而不是甜。过了三年,枇杷生了满枝,果真个大蜜甜。二姑是个细心的人,枇杷吃完了,还把枇杷摘一些,洗净,晒干。她说,老中医的堂舅嘱咐几次了,枇杷叶煎水喝,治咳嗽,是上好的咳嗽药。可收进了阁楼的枇杷叶,一次也没煎过水当药喝。有人咳嗽了,还是去鼻涕糊诊所打一针,开几粒药丸吃。二姑却乐此不彼,年年摘年年晒。
二姑的枇杷树下,每年都会发枇杷苗。我大哥觉得枇杷细皮嫩肉,好吃,挖了一棵栽在自己院子里。院子不大,却种了好几种果树,有枣树,有柚子树,有橘子树,有梨树。还种了两棵葡萄。葡萄藤抽疯一样,爬满了屋顶,也爬满了树梢。大嫂拿一把剪刀,把葡萄藤剪了,说,两株葡萄害死人,葡萄喂了鸟,其他果树也不结果子。枇杷树在橘子树下,长得慢,长得艰难,一年也发不了几支新枝,更别说结果了。我说,大嫂,你爱吃橘子,还是枇杷呀。大嫂说,枇杷当然好吃呀,汁多无渣。我拿起柴刀,把两棵橘子树砍了。大哥看见晒干了的橘子树,说,橘子也甜,砍了多可惜,年年结果呢。我说,哪有那样的好事,巴掌大的地方,想吃枇杷又想吃橘子,橘子十块钱五斤,枇杷十块钱一斤,你说怎么选啊。
过了三年,枇杷树高过了瓦屋。
枇杷叶肥,密集。阳光难以到达地上,树下阴湿,长蠕虫,蚯蚓也会爬出地面。树下成了鸡的粮仓。鸡,咯咯咯咯,出了鸡舍直奔树下,觅食,趴窝,还生下鸡蛋。烧饭,打一个番茄蛋汤,大嫂开菜柜,摸摸,鸡蛋没了,她转到枇杷树下,捡一个上来,打进锅里。大嫂咯咯咯笑了,说,还是枇杷树好。也有烦的时候,夏天阴湿处,多虫蚊。虫蚊多,蜘蛛也多,满树都是蜘蛛网。大嫂用一个稻草扫把,戴一顶斗笠,撩蛛网。
每年初春,我会把院子里二十几棵果树修枝。我穿一件十几年前的劳动布衣服,戴一顶斗笠,戴一双黑皮质大手套,一棵一棵修剪。枇杷树最难修剪,枝桠多,又粗,有不直条,爬上树,蛛网也会蒙上脸。但我还是乐意修剪,修剪过的果树,树冠如盖,果实压枝。四月末,站在楼上,看枇杷树,杏黄绿叶,甚美。
枇杷、樱桃、梅子,并称“果中三友”,都是我们十分喜爱的水果。梅子树,我没见过。樱桃好吃难栽,是俚语。我栽过四十几株樱桃,却没一株活下来。从樱桃基地拉了一板车秧苗,种了七亩多地。头三个月,樱桃树都活了,三五天,毛绒绒的绿叶,从枝节发出来。我便估算着,三两年,樱桃可自己采摘了。可入夏,叶子软塌塌,半个月,全死了,枝杆和麻杆一样,脆断,折一下,啪啪啪,水气干了。枇杷树是蔷薇科植物,也是易于栽种的植物。秋末初冬,枇杷树开花了,一束一束,花瓣如盛雪。花开了,雪也从山尖盖了下来。枇杷开花迎雪,梅花则斗雪。唐代诗人羊士谔(约762年—819年)写过《题枇杷树》:“珍树寒始花,氛氲九秋月。佳期若有待,芳意常无绝。袅袅碧海风,濛濛绿枝雪。急景有余妍,春禽幸流悦。”
有一次,我在横峰还是在井冈山,记得不确切了,听一个人无意间说起,枇杷树是做琵琶最好的材质。我听得心怦怦直跳。琵琶为什么叫琵琶,是因为枇杷树做材质而来的。说的人,让我佩服五体投地。我回到上饶,自扑琴行,问修琴师傅:“琵琶是用枇杷树做的吗?”修琴师傅愣愣地看着我,说,硬木音箱发出的声音,更悠扬,可细腻可宽阔,音质好,易共鸣,枇杷树不是硬木,不适合做音箱。他一棍子把我佩服的人打死。修琴师傅说,通常是由鸡翅木,铁梨木,花梨木,白酸枝, 红酸枝,黑酸枝,紫檀等硬木制作琵琶音箱。
我有些灰心丧气。我又查资料,为什么叫琵琶,为什么叫枇杷?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批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推手为批,引手为把,遂名批把。“王玉” 作上偏旁,为弦琴类 ,遂名琵琶。有一种树的叶子为琵琶形,即梨形,世人取象形之意,把这种树叫枇杷。
让我心怦怦直跳的,不仅仅是琵琶,还有白居易。我简单的大脑里,还没产生《十面埋伏》,或《塞上曲》,或《醉归曲》,或《大浪淘沙》,或《琵琶语》的旋律,白居易的《琵琶行》便喷射出来。还好,白居易写过一首《山枇杷》:
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
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
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
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
深山老去,许是一种最好的命运。枇杷树本是寻常之树,进不了华贵的庭院,进不了高雅的园林,溪野便是去处。去处即归处。人都是实用主义者,眼皮翻开,势利如狼。枇杷因了味美,止咳养五脏,也多栽种枇杷树。若枇杷不可食,有几人会知道它呢?
笨拙的木耳
有几个朋友,问我,你的微信名字,为什么叫木耳。我说我喜欢木耳。又问:“为什么喜欢木耳?”我说木耳看起来笨拙朴素,色泽也不鲜艳,但营养价值高,炖鸡汤、炒蛋、炒白菜丝,木耳是不二选配食材。
乡间野生木耳,非常少,很难采摘得到。野菇在春天的松林或山溪边的灌木林里,每年还可以采几次。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采到木耳,但我从来不对别人说。河滩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杈常被人砍了做豆芊,有些杨树便被砍死了,留一个大木桩,长指甲大片的木耳,灰白色。八月,空气如炽。杨树皮腐烂,落下来的木屑如米糠,木耳从树皮缝里,不谙世事地长出来。像戴着灰皮帽的童话里的小矮人。采木耳,也不要篮子,也不要剪刀,摘一片荷叶托在手上,把采下来的木耳,放在荷叶里,包起来,游了泳带回家。
一年之中,吃上木耳的次数,极其有限。小孩贪吃,我也有吵母亲争吃的时候,缠着母亲买木耳吃。家贫。母亲拿几个鸡蛋去杂货店卖,买一些木耳回来。买来的木耳,是白木耳次品,只有木耳蒂,上部的木耳花被剪了。木耳蒂泡水半天,发胀,成了一个小碗的形状,像一朵割了花瓣的白芙蓉。只有一个好日子,木耳管吃够,还不挨骂。家里做喜酒,如家兄结婚、姐姐出嫁,请来几十桌客人,烧流水席,每桌上二十四个菜,第一道菜便是酸辣白木耳。我端一个大碗,站在灶台边,厨师用一个铁勺,从大铁锅里,舀上来,倒进我大碗里。碗面上,扑腾腾地冒着热气,几根肉丝漂在碗面上,辣椒粉刺鼻呛人,忍不住喷嚏连连。我用洗脸巾盖在手掌上托碗,蹲在院子的台阶上,嘴巴对着碗面吹,热气莹白地一圈圈散去。边吹,边啜汤,热气散尽,汤也啜完了,再吃木耳。木耳软脆,溜滑。
我三姑来看我祖母,有时候会买两斤肉,有时候也会买一包木耳。我祖母不爱吃,说,木耳不好吃,像嚼树叶。母亲舍不得木耳炒起来吃,把白菜帮切丝,和木耳一起炒,放上两片咸肉。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村里人能常吃木耳的,没几家。我有一个邻居,我叫他五爷。比我祖父小好几岁。但死得早,六十来岁便病故了。他的眉毛是白白的一撮毛。他喜欢吃死猪仔。猪仔易夭折,弄堂里养母猪的东家,把死猪仔给五爷吃。五爷把猪仔架在火上煻熟,猪皮焦黄了,切丝炒。他还喜欢喜蛋,煮熟,毛茸茸地塞进嘴巴,口角两边淌涎水。他得慢性病,在床上挣扎了几个月,腌黄瓜一样。临死前,对他老婆说,木耳好吃,我们家从来都没买过木耳,你去买一些,炒一碗木耳吃吃。他老婆炒好木耳,他已经无法吞咽了,托着碗,看着木耳,泪水一直流到碗里。
村里有一个瓦匠,泥胚摔打得有力结实,做出来的瓦好。他喜欢吃木耳。他常去杂货店赊账,赊了两年也还不清,年年有余账结不了。他赊木耳,一袋一袋赊。一袋半斤,要不了几天吃完。店老板便说,你一个苦力的命,天天木耳上桌,不是穿着绸缎挑担吗?店老板不想赊账,取笑他。瓦匠说,账你记着,利润也记着,有一天你盖房子了,到我这里搬瓦去。店老板说,白米可以换米糖,豆可以换豆腐,鸡蛋可以换洋碱(肥皂),妹妹给哥哥换亲的,冇听说瓦可以换木耳的。边上喝闲茶的人,脱下解放鞋,给瓦师,说:“木耳这么好吃?你用鞋子掌掌嘴巴,就不想吃了。”
顾城是我十分敬重的诗人,1993年10月,他离世时,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中文名叫桑木耳。顾城为木耳写过一首诗《回家》:我看见你的手/在阳光下遮住眼睛/我看见你头发/被小帽遮住/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在笑……我很喜欢这首诗,木耳是顾城可爱的上帝吧。
木耳有白木耳,黑木耳。这是色泽上的分别。树木耳,石木耳,这是腐生原料的区别。还有一种不是木耳也称木耳的木耳,叫水木耳。水木耳是一种念珠藻,也叫葛仙米。东晋道教名士、医学家葛洪,把水木耳献给皇帝,作长生之食材,皇帝便赐葛仙米之名。在干净无污染的稻田、水里,水木耳常见。水木耳在水里,像鲤鱼孵的卵,一串串,单个滚圆,黑色,或绿色,或暗黄色。水木耳用清水清洗几次,即可做菜。孩童时,在夏秋的雨后,我随我老二常去田里捡拾水木耳,用一个鱼篓,捡半蒌回家,养在大缸里,想吃的时候,捞上来。
树木耳,就是我们通常吃的。石木耳可不常见。石木耳也叫石耳,长在高山滴水的岩石壁,或高山溪涧的崖石上,伴生青苔。石耳只有小指甲那般大,半透明。我买过两次石耳。一次在婺源的江湾镇。那是十多年前,江湾还是个破落的小镇,一个妇人用包袱包了半包的石耳,她说是在溪涧边捡的,捡了三天,才捡了这么半包。我全买了。我骢骢那时还是三岁。她十分爱吃,低着头,拿起筷子,不说话,把石耳扫光。在庐山买过一次,在一个农家杂货店。老板娘说,这个石耳多好,你摸摸,你摸了就知道是庐山正宗石耳,你看看,石耳还有一层霜白。我拎拎,起码有五斤。我买了两斤,背了几百里路到家。我泡了小半碗,泡半天,烧起来吃,咸死人。原来石耳用盐水浸泡了再晒的,咸味很难去除。再也没吃。
还有一种叫地耳的植物,被人熟知。地耳,土话叫地皮菇。和泡水后的石耳很相似。草地上,芦苇地,田埂上,河边的洋槐树地下,在初夏的雨季,满地都是。地皮菇柔滑,鲜嫩,香润,低脂低糖,可炒食可做汤,是南方地上“美味八珍”之一。酸辣地皮菇也是上饶地地道道的本土名菜。我有一种做法,吃过的人,无不称赞。把油炸豆腐剁碎,和地皮菇一起做酸辣汤,最后放香葱。地皮菇好捡,半天可捡一篮子,却难洗。地皮菇会卷起来,里面包着泥沙,要一片片洗,耗费工夫。春季,菜场路口,每天早上有人拎一个竹篮卖地皮菇。现在我很少吃地皮菇了,原因是土地污染太严重,地表重金属过高。
在央视记录频道,看《舌尖上的中国》,有一个篇章讲皖南美食,描述了皖南牯牛降采石耳。一个绳子从山顶悬挂下来,绳子绑一个人,慢慢垂降到山崖中间,荡秋千一样,采石耳。像走达瓦孜,真是惊险万分。一天也只能采二三两,有的人甚至落下悬崖,粉身碎骨。
自小生长在山区,其实我并没有看过木耳是怎样人工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地域的人,培育木耳是主要谋生方式。浙江的龙泉,福建的武夷山,安徽的祁门,这几个地方的人培育木耳,相当于我家种白菜。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龙泉人来上饶一带,培育木耳的人很多,在山坞里,搭一个棚,住上好几年。有的人也落户在上饶山区。我第一次见木耳培育,是在1996年,我去婺源,在梅林入口的一个小山村里,见田里有一排排规整安插在地里的圆木桩,包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用黑色的遮阳纱布蒙着。我很是好奇。当地的一人,对我说,那是培育木耳。
我在闽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镇,来我学校读书的孩子有好几百人。我问同事,这个镇的人,为什么来这么多孩子。同事说,镇里的人大多以培育香菇木耳为业,没时间照看孩子。那年冬天,我去镇家访,见了很多菇民。暖冬,阳光黄黄的,从山垄斜照在小镇的街道上。溪流的两边,是稻田。稻田全是香菇木耳大棚。镇街两边的小店,大多经营香菇木耳。菇民在算,一年打多少桩,一桩赚多少钱,夫妻一年可以培育8000个桩,还不会很劳累,培育1万个桩,那烧饭都没时间了。我买了一包香菇一包木耳回来,放在办公室,以此警醒自己,把事做好,不然真对不起辛劳的菇民。
有一段时间,我对木耳真是迷得入骨。随时随刻翻开我的储藏柜,肯定有黑木耳白木耳。白木耳,也叫银耳,泡在水里半个时辰便完全发胀,如燕窝,如雪浮在水里。我把白木耳、豇豆、红枣、葡萄干、红豆、黑豆、花生,一起煮,当饭吃。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舌苔难以产生味觉了,我才没吃。骢骢看着我端起碗吃,鸡皮疙瘩冒出来,说,世界上傻的人很多,比你更傻的人可不多。我哈哈大笑。我母亲喜欢吃白木耳,可她不吃。她吃了银耳,会发胃酸,想呕吐。
木耳,木头上的耳朵。李时珍在本草中说:“木耳生于朽木之上,无枝叶,乃湿热余气所生。曰耳曰蛾,象形也。”地生为菌,木生为蛾。桑、槐、楮、榆、柳,这五种朽木,易生木耳。培育木耳,也多以这五种树为腐生木。
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印象:笨拙的、木讷的、有童话色彩的木耳,单纯的、野气的、有山民肤色的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