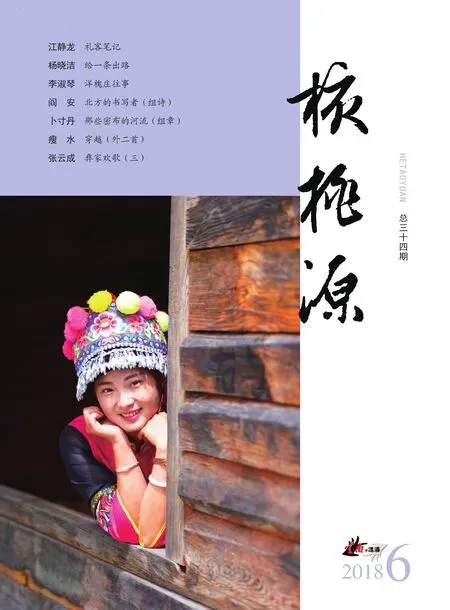春 草
方世开
一
咯咯咯咯,吴妈在屋檐下端着筲箕,一边唤鸡,一边撒玉米。十几只鸡呼啦啦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推推搡搡地争抢着啄食。
吴妈抬起脚,狠狠地踢了那只花羽毛的大母鸡,咬牙切齿地骂道,就知道吃,吃,吃!连一个蛋都不会下!
春草正坐在屋里吃午饭,听见婆婆的骂声,愣了一下,重重地将碗撂在桌子上,扛上锄头,撅着嘴摔门而出。
吴妈看了一眼春草的背影,又踢了花母鸡一脚,大声骂道,脾气还不好呢!你这只中看不中用的死母鸡,白养你了!
春草来到山坡上的玉米地里,放下锄头,坐在草地上,默默地流起泪来。
六月午后的太阳真毒,似乎要将地上的一切都烤焦。巨大的热浪一阵阵袭来,将春草流泪的心思都烤没了。
春草站起身,握了锄头,开始锄草。今年的玉米长势真好,都快有自己高了,绿油油地惹人怜爱。
可是,自己那块责任地却始终是荒芜的,长不出庄稼来。想到婆婆怨恨的眼神和恶毒的咒骂,春草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也怨不得婆婆,都五十多岁了,还抱不上孙儿,心里急着呢。山里人结婚早,像她那样的年纪,孙儿都该上学了。这样一想,春草心里平静了下来,反倒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婆婆了。
屈指一算,自己嫁过来已有四、五个年头了,可是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丈夫体壮如牛,能吃能喝,一次次拍着胸脯说自己绝无问题。
婆婆只有将一腔的不满发泄到她这个身体有些单薄的媳妇身上。
二
这是一个峰峦如聚的偏僻山区,造物主似乎刻意将千山万壑集中驱赶到了这里。人们因地制宜,通常把房屋建在山顶或半山腰。山与山之间,两边的人甚至可以大声对话,但要走到对面去,非得费上半天功夫不可。吴妈的背篓曾经在一个清晨从院坝滚下山去,待她从谷底捡拾回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
这些年,政府实行退耕还林,将一些人家迁移到山外,本就稀少的人烟更显稀疏了。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十户人家散落在方圆二、三十里的大山深处外,就是几处政府为护林员搭建的简易小木屋。
天刚蒙蒙亮,春草早早就起了床,梳洗完毕,用开水泡了一碗剩饭,就着昨夜的剩菜草草吃了,背上背夹,出门朝山外走去。
今天是赶集,她得去镇上给丈夫搭把手,回来时顺带捎些盐巴和日用品。
到镇上有三十多里路,步行需要三四个小时。春草的丈夫来福在镇上开了间榨油作坊,靠着一身力气和诚实,生意做得还算不错,尤其是赶集的日子,买油的人更多。
到了镇上,场已经齐了,人潮熙熙攘攘。油坊里,聚集了不少买油的人。春草将背夹放下,捋了捋额际汗湿的头发,接过顾客递过来的塑料壶,麻利地装起油来。
满身油污的来福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又是从库房里搬油桶,又是收进油菜籽。两百斤重的油桶,他双手抓住桶耳,轻松地就提溜起来,脸不红,气不喘。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集市散场了,来福的油坊也清净下来。春草出了一身汗,湿透的衣服黏在身上,更显得前凸后翘。来福盯着春草,两眼泛光,傻呵呵地笑着。春草佯怒地瞥了来福一眼,拿起扫帚扫起地来。
吃完夜饭,二人洗了个凉水澡,来福迫不及待地抱起春草光溜溜的身子,扔到床上,像一匹狼一样扑了上去。
你说,咱们又不是没尽力,咋就生不出个娃呢?春草伏在来福的胸脯,幽幽地问。
这要问你啊,该做的我都做了。来福喘着粗气,点燃一支烟。
要不,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春草说。
要去你自己去。咱上床能做,下床能吃,反正我没问题。来福猛吸一口烟,吐出浓浓的烟雾,呛得春草咳嗽起来。
抽,抽,抽,就知道抽!抽死你个烟鬼!春草坐起身,拳头在来福的胸上打了几下。
来福嘿嘿直笑,他就喜欢春草嗔怒的样子。他知道,春草不仅人漂亮,对自己也很好。夫妻之间表达爱意,很多时候却是以相反的方式。
来福转过身来,再次把春草压在身下。
春草将身子蜷缩成一团,说,你不听话,不给!
来福笑着说,听,听,我听老婆的话还不行吗?
那咱们去医院检查。春草松开手,同时展开了柔软的身子。
三
吴妈哭得死去活来,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来福被查出精子活力弱,生育的几率很低。
我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没做过一件缺德事!老天爷,你咋就忍心让我家断子绝孙呀!吴妈的头不停地撞着木板墙,声泪俱下。
来福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着烟,脸色极是难看。
春草双手蒙着脸悄悄地流泪,她想,不管是自己不孕也好,还是来福不育也罢,结果都一样,就是自己做不了母亲。
看着婆婆哭得伤心,春草有些不忍,之前的恩恩怨怨,此刻已经没有了意义。她觉得,这个年近花甲,操劳了一生的婆婆,也真是不易。
春草走过去,用衣袖给婆婆擦着眼泪,轻声说,妈,别哭。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日子还是要过的。
吴妈听了,哭得愈发厉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草儿啊,妈错怪了你,对不住你了!
春草长期以来郁积在心底的委屈涌了上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两个女人抱着哭成一团。
四
黄牯,我家电线短路了,来帮我看看!临近晌午时,吴妈站在院坝边沿,朝着对面山上的小屋大声呼喊。
小屋里出来一个身影,朝吴妈挥了几下手。
那个挥手的人就是黄牯。因为长得体格健壮,像条黄牯牛,所以人们就这么叫他。
黄牯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发了几天高烧,后来病虽然好了,却成了哑巴,发不出一点声音。幸而他耳聪目明,倒也没有太影响生活。他没有兄弟姐妹,父母也在前几年相继离世。因为不能说话,没人愿意嫁给他,所以三十多岁了还是孤身一人。村里考虑到他的状况,推荐他做了护林员,每月的补贴加上自己种地的收入,日子倒也过得去。
吴妈挥着长长的竹扫桠,扫着院子。她似乎有什么心事,扫几下,心神不宁地停一会儿,不时抬头看一眼对山。
太阳下山的时候,春草回来了,背着满满一背篓洋芋,汗水湿透了衣服。
吴妈在堂屋里帮春草卸下背篓,怔怔地看着她,眼神有些怪异。
今年的洋芋好着呢,个儿又大。春草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轻声地说。
那是因为地肥,天气又适宜。吴妈将背篓里的洋芋倒在地上,答道。
春草洗完脸,吴妈从锅里端出温在热水里的饭菜,婆媳二人吃了起来。
吃罢饭,天有些暗了。吴妈洗了碗,指着盖了盖子的塑料桶,说,出了恁多汗,去洗个澡吧。吴妈说完,走出门去。
黄牯走进院子,四处打量,没见吴妈的身影。他径直朝屋里走去,偏房的门缝,漏出微弱的光。
他从门缝看进去,惊得张大了嘴巴。烛光下,春草坐在大木盆里,正用毛巾擦着丰满的身子。
黄牯看得心惊肉跳,大口喘起粗气来。这个春草,穿着衣服好看,脱了衣服更好看!
黄牯猛地推开虚掩的们,像一头发情的牯牛,扑了进去。
春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双手下意识地抱在胸前。
黄牯从盆里将春草抱起来,扔到旁边的床上。
妈,妈呀!救我!春草大声呼喊,抓住黄牯的头发拼死抵抗。
吴妈失踪了一般,没有任何声息。
在强壮的黄牯面前,春草的抵抗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黄牯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她身上,令她窒息,竟发不出一丝声音了……
黄牯刚穿上裤子,吴妈就进来了。
你这砍脑壳的!喊你来看线路,你倒好,祸害起良家妇女来了!吴妈拾起墙角的晾衣杆,朝黄牯劈头打去。
黄牯挨了几棍,抱着头慌不择路地逃走了。
吴妈看着坐在床上嘤嘤哭泣的春草,大声骂道,千刀万剐的!不得好死!
春草抽泣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去报警,把这畜生抓起来枪毙了!
吴妈急忙说,这一来,人们不就都知道了这桩事?我们家的脸往哪里搁呀?你也没法再做人呢!
春草听了,大哭起来,捶打着枕头,喊道,那怎么办?总不至于便宜了那个畜生!
吴妈抚摸着春草的头,安慰道,善恶有报,他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会惩罚他的!
妈,我回来了!屋外传来来福的声音。
草儿,冷静些,这事千万不能让来福知道。听话,妈是为你好。吴妈压低声音说。
来福进得屋来,打着手电检查线路。不一会儿,灯亮了。
环顾一圈屋子,来福问道,春草呢?
吴妈并不抬头看来福,说,她累了,已经睡了。
来福听了,转身就要往偏房去。吴妈叫住他,说,我托人给你弄了副草药,来,趁热喝了。
吴妈从灶上的陶罐里,倒了一碗药,催来福喝下去。
来福闻了闻冒着热气的药,自言自语道,有用吗?
吴妈说,用过的人都说特效呢!张村的张麻子吃了这药,前些天生了个大胖小子。
张村离这有二十多里,来福没去过,更不认识张麻子。但他对自己的妈说的话还是深信不疑的。
五
玉米已经挂包,红红的缨子煞是爱人。再过一个来月,就该收获了。这个时候,野猪开始频繁出没,它们成群结队蹿进玉米地,拱倒玉米杆,吃起玉米棒子来。
春草戴着草帽,握着镰刀,在山下的河滩上巡视自家的玉米地。
野猪敢来偷吃,我就跟它拼了!春草挥挥磨得发亮的镰刀,心里说道。
突然,她感到有些恶心,干呕起来。她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暗想,这么热的天,该不是中暑了吧?
春草走到小溪边,摘下草帽,捧起溪水洗了洗脸。清凉的水浇在脸上,让她舒服了许多。
背后响起了脚步声。春草回头一看,顿时怒上心来,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来人是黄牯,盯着春草傻傻地笑。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春草挥着镰刀喊叫着扑了过去。
黄牯拔腿朝山坡上跑,在高处站定。春草本想追上去,但肚子里翻江倒海,让她没了追赶的力气,蹲在地上大声干呕。
黄牯呲牙咧嘴地笑了,双手不停地比划着。
春草明白黄牯手语的意思,恨恨地说,老娘怀没怀孕关你杂种屁事!
黄牯沉默了片刻,又比划着什么,而且脸色有些凝重。
野猪来了咋的?野猪也不比你缺德!你这个连野猪都不如的畜生!春草并不领情,咬牙切齿地骂道。
春草又干呕了一阵,脸色变得苍白。
黄牯走下来,急急地比划着,要背春草回家。
春草站起来,挥刀扑向黄牯,声嘶力竭地吼道,老娘今天骟了你!不得好死的畜生!
黄牯落荒而逃,消失在树林里。
六
吴妈坐在一座荒草萋萋的土坟前,泪眼婆娑。
死鬼,我也是被逼无奈!谁叫咱们的儿子得了那样的病呢?咱们家不能断了香火呀!吴妈一边流泪,一边拍打着坟头。
月近中天,像一把镰刀悬在头顶,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吴妈心惊肉跳,颤颤巍巍地站起身。一阵风吹来,吴妈打了一个寒颤。山里的夜晚真凉。
吴家已经好几年没有置办过酒席了,今天孩子的满月酒,热闹而喜庆,院子里十几张桌子坐满了客人。大家兴高采烈,划拳行令的声音此起彼伏。
吴妈和来福屋里屋外来回穿梭忙碌,不停地与客人打招呼。
屋里,春草妈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赞,哟哟哟,我外孙子多漂亮,你看这小嘴,你看这眉眼,将来一定有福气呢!亲家母,咱春草可是给你家立了大功呢!
吴妈讪讪地笑着,应道,是咯,是咯!托你的福!
春草木然地看着人们逗孩子,脸上没有表情。
送走了客人,收拾完屋子,已是午夜时分。吴妈长吁一口气,洗罢脸上床睡觉了。
来福陪客人喝了很多酒,倒在床上鼾声如雷,孩子响亮的哭声也没能惊醒他。
孩子吃完奶,安静地睡着了。春草看了看熟睡的孩子和来福,轻声地叹了一口气。
后窗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有什么响动。春草推开窗,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
春草拿出手电一照,只见窗台上放着一篮子鸡蛋。
春草朝窗外吐了一口唾沫,忿忿地关了窗户。
七
转眼又到了夏天,孩子已经半岁了。春草在红薯地里拔草,孩子坐在树荫下的小毛毯上,独自玩着玩具。
春草一边薅着草,一边大声地逗孩子,可儿乖,等收了庄稼,咱们买新衣服和好吃的。孩子咯咯咯地笑着,声音是那样甜。
有一会儿,春草见孩子没有声音,抬头一看,只见黄牯蹲在孩子旁边,手里拿着什么。
春草站起身,疯也似地扑了过去,骂道,畜生,你想干啥?
黄牯抬起头,冲着春草笑,扬起手里的一串用红线穿起来的野猪獠牙。
春草感到恶心,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厉声呵斥道,滚!有多远滚多远!
黄牯点头哈腰,转身离去,频频回头看孩子。
春草郁闷了一会儿,便回到地里继续拔草。
突然,孩子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春草扔下手里的草,飞奔过去,只见一条长蛇甩着尾巴溜进了草丛。
孩子的脚踝红肿起来。
春草大惊失色,抱着哭泣不已的孩子不知所措。
黄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二话不说就俯下身子,在孩子的伤口上吮吸起来,吐出几口黑血。末了,撕下一块衣服,紧紧地缠在孩子脚踝上。
做完这一切,黄牯打着哑语,说孩子没事了。
刚比划完,黄牯就倒了下去,不断地抽搐着。不大一会儿功夫,黄牯便断了气。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春草没了主意。这个让自己忍辱含垢的男人,现在却不知该如何评价了。
八
看着一天天成长的孩子,春草欣喜之余,心里却是极不踏实,仿佛做过贼一般,此生的污点难以洗去。尤其是在来福抱着孩子逗乐的时候,春草的这种负罪感更加强烈。
婆婆脸上的笑容,像极了花瓶里的假花,虽然鲜艳,但明眼人一看就不是出于自然。
夜阑人静的时候,春草常常咬着被子默默流泪。这种非人的折磨,让春草痛不欲生。
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分别?!
春草拿定主意,趁深夜来福熟睡,剪下一撮他的头发,用布包好揣进怀里。
我娘病了,我得陪她去县医院检查,可能要两、三天才回来。春草一边奶孩子,一边对吃早饭的婆婆和来福说。
好哩!你娘身体不好,好好照顾她。婆婆从里屋拿出一些钱,递给春草。
来福在镇上的汽车站送春草和丈母娘上了车,叮嘱春草小心孩子着凉。
给母亲检查完身体,将她安排到旅馆住下,春草抱着孩子又折回医院。
拿到结果出了医院,春草蹲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
来福啊,可儿是你的种哩!老天长眼哩!春草的哭诉里,有欢喜,更有委屈。
九
春草背着孩子,搀着婆婆,跟在挑着家什的来福身后。他们家从今天起,作为第二批异地安置户搬到镇上去居住了,将永远告别这云山雾罩的世居之地。
走到山垭口,春草回过头,看着浓雾紧锁的大山,心里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