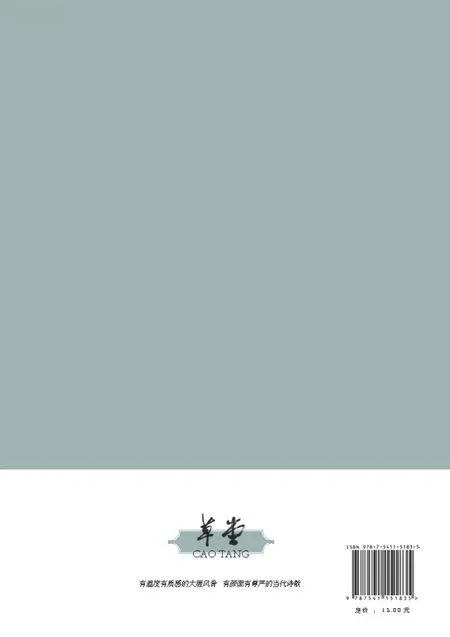压伤的芦苇(组诗)
沈 方
拾旧魂
秋花开时踯躅于江山万里,
却没人吹笛到天明,
而一些旧魂的归来毫无预兆。
管他是花魂、鸟魂,
还是无主的孤魂、游魂,
既不知来路,谈什么出处。
唯悔恨脱胎换骨太早,
以至看山不是山,看水反见火,
看星星想起缝隙里的芝麻。
没有比梦中做梦更深刻的思想了,
没有比井底看天更完美的残局,
没有比一千年更近的距离。
来的时候空无一物,
就不要妄想去时琳琅满目,
平生所学皆不足于令哑巴开口 ,
但罕见的沉默吓倒了聋子。
来了就好,请报上各自的名字,
将打水的竹篮里装满。
只有石头压住,才能下沉。
只有底部才有重见天日的运气。
只有扛起来向前狂奔,
才能忘记目的地。
只有停止才能避免摇摆。
唯遗憾丢失了点铁成金的机会,
口中念念有词毕竟是徒劳。
生死两忘
耗尽浑身记忆力我尝试,
牢记此生的全部,
从早晨至黄昏。不曾想到,
过去的全部加上全部过去,
难以填补夜晚的缺口。
可是我不得不经历一切,
荒废掉树林中的空地,
尚未走完的路。
沿着河堤绕过一望无际的圩田,
已没有根深蒂固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及那天很晚时,
我找到一幅古地图,
找一座桥,一座城门,
一座不存在的房子,
而一阵凉风吹拂我的额头。
吹醒我掌心的纹路,
吹醒了预言中沉睡的混乱。
我一脚踏上我的前途,
风吹得我出乎意料,
吹得我生死两忘。
对 饮
在长兴人开的小酒店,
我们点了四样菜,
咸菜烧鲫鱼,炒肚片,千张包,
还有一个蔬菜。
他拿着二斤装茅台酒瓶问我,
能喝多少?
这是几天前朋友聚会喝剩的。
他端起酒杯与我碰杯,
今天兄弟你陪陪我。
我向来不善饮酒,一生中,
错过了诸多酒桌上交友的良机,
我们因诗结缘,虽然,
曾有过几个品酒论诗的夜晚,
可是我们从来不曾,点几样菜,
坐在小桌前对饮。
等到多年朋友见面不为别的,
只为喝酒的时候,
彼此还有什么不能明白,
无论什么事都无须多言了。
后来他又叫了半斤泸州老窖,
要我再陪陪他。
说到去年我父亲过世,
他陪我一起守灵那个夜晚,
我看见他眼眶涌动泪水。
记得他坐在灵堂门口长凳上抽烟,
那一夜似乎过得很快,
而我不会忘记,
那一夜比一生更长,
那一夜是我的最后一个开始。
河 湾
夜深时对岸的市民广场,
只剩两盏路灯,
左边一盏,右边一盏,
中间是明亮的部分。
平台上一尊雕像站在灯光外面,
看不清他的面孔,
这青史留名的人物来自何方?
今夜的颜色深不可测。
圆弧形台阶一步步向河岸推进,
比白天更有力度,
沉入河湾的最后一步,直截了当,
干脆利落,并未溅起水花。
河湾中的小洲我看见它,
轮廓线隐隐约约,
夜夜栖居于树丛的众多白鹭,
为什么异乎寻常地安静?
答谢宴
总有一天,天下会有不散的宴席,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座取之不尽的空山。
总有一天,你说先结果后开花,
你就会得到一篮子禁果。
而今胡椒、芥末摆上了桌面,
何必还要捧出冰雪?
既然上天赐予我们稻草、木柴,
我的掌心就会聚集星星之火,
和火焰的哲学面孔。
酒杯早已不是昨天那一只,
而杯中之酒满而不溢,
像一个不肯多言的老僧。
儿时的伙伴围着我坐在灯下,
今夜不捉迷藏不斗嘴,
且袖手行过旧年阡陌看东风摇百草,
篷窗睡起,不睬那不成啼的虫鸟。
谁来谈谈叩门之喜、倒裳之欢?
居家的嗜好不足道,
即便从前行善将来作恶也俱为笑谈,
唯窗外流水和水边凉亭不多不少。
喜鹊成双、松鼠落单,
而猛虎独行,
古人的寂寞不过是莫可奈何。
在人间长对秦时明月,推杯换盏,
一来一往,已过汉时关。
压伤的芦苇
走下堤岸,在水面告别,
压伤的芦苇倒在水中,
与佯装成朵朵浪花的鱼握手,
清澈的诉求已经喑哑。
绿色的衣袖划破了,还是新的,
被湖水的眼睛收留,
来年再沿着堤岸生长。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忍受着时间的枯黄。
多年以后重逢那一天,
一支短笛盘旋着。
记得从剖开的芦苇中,
取出他的伤,取出空无的内涵,
贴在记忆的笛孔。
在水面告别,没有人走得更远,
没有人追赶高飞的鸟语。
风雨茅庐
整理他赠我的书,
总共六七本,
有的曾通读,有的,
不记得读过几篇。
朋友三十余年,
彼此宽容,理解,
无所求,偶尔争论,
一笑了之,
而不争论岂非互相敷衍,
未必真朋友。
多少年来相见时,
各自说过的话,
倘变成文字,
比眼前的书的字数,
要多得多,浩如烟海,
也算一件奇事。
一个人长年累月,
埋头读书,独自著述,
多少会有倾诉欲,
而读者和听众,
有时有,有时无。
我们说买两只小板凳,
到时候作为专用座位,
终究只是玩笑。
那天你坐的椅子,
是唯一的客座,
我就只能坐在床沿。
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
谈郁达夫,
窗外,雨越下越大,
仿佛郁氏风雨茅庐。
床单旧了,
床的一角叠起的,
毯子不像毯子,
被子又不像被子,
已陈旧不堪,
不知你有无注意。
·创作谈·
诗孰好孰坏,要放在生命中检验,可以是一段光阴,也可以是整个人生,这样终于能够在脱身后逐一确认,而除此之外,无论好坏皆可有可无。诗需要平衡,写一首诗应该产生盈余,换言之,写一首诗得到的收入应该大于支出,否则必然造成亏空,甚至成为空壳,所以诗不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成全,写得越多越充实,写得越好越富有。如果找到了这样的感觉,那就谢天谢地吧。
古之中国,有文章而无今之“文学”观,有教化论而无文的自觉,后来自觉了,仍旧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今,朽不朽不为人的意志而转,即使求不朽者也只是心里想想,言之无益,至于经国及教化,早就不吃香。文学除了以今之“文学”观独步于世,大抵不便有所作为。讳言经国甚至无意于教化,唯自家好自为之,近观似乎摆脱了束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而从长远看,恐怕祸福难料,因为好自为之的各得其所,好在跌宕自喜,坏在自得其乐,文学毕竟不是可以孤立的。
好在文学并无可能抛弃必要的载体,取消固有的功能,古人的教化论和经国说岂是没落的陈腐之见?文学不必反映时代,而风气必然体现于文学,文学家拿文学当什么,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