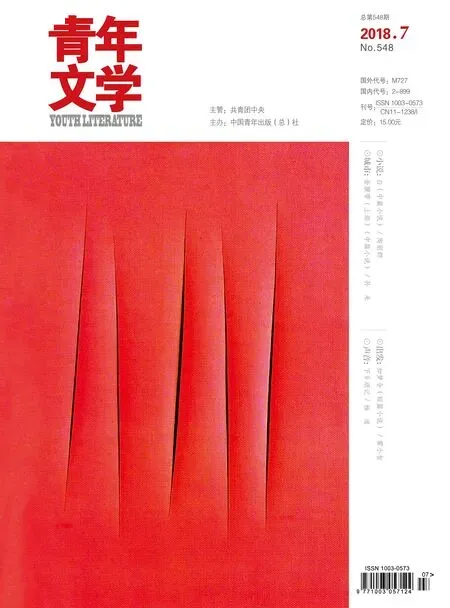张远伦的诗
⊙ 文/张远伦
河心洲之光
我不知道缓缓的流水,与我的语速有什么关系
我说话减慢,渐渐近乎口吃
甚至,一个黄昏,没有一句话
我看见有一些阳光的反光,从河面上起来
幻化成几个十字,而后消散
我突然想说话,张大嘴巴
竟然没有声音
诘问的能力,没有了
一个黄昏,我都没有找到,能将几个词语连缀起来的
那一条射线。我闭嘴
世界不需要我的命名,独卧河心洲
把最后几点弹跳的光的碎片,收进眼皮内
河心洲之石
石头用流水洗脸,还是长满了青苔
我怀疑那不是青苔,更像是黑泥
嵌满小水生动物的残骸
我甚至看到了小贝壳,被挽留在石头上
我像这些来历不明的幽微之物
慢慢喜欢上一块狭路相逢的石头
搬到河心洲上,用细沙慢慢拭擦
直到露出它脸上深深的罅隙来
这是一块有肺部的石头
我喜欢它被镂空的部分
那些无缘无故的消失和放弃
让一块石头活在我的怀里,轻轻喘息
与卑微的我,在封闭的村庄
相互换气,相互透过对方的胸廓
找平
清晨的阳光均匀地铺展在人民广场
蘸水写字的老人,一边写一边后退
金色绸面上,字迹渐渐萎缩
继而一个一个消失
他有足够的耐心,看着宽阔的大理石页面
变成他的一张废纸
他每天都制造这样的废纸。把骈文、歌赋
和散句,一一显现出来
而后亲眼看着它们变成幻象
驻足,停留,冥想,转身离开
他穿过牌坊,脚后跟像在带起纸屑
每天,我与他反向而行
把他身后卷起的广场,又熨了一遍
方块石头,一片一片柔软下去
我紧身疾行,他慢条斯理
我中年的一个平面,和他老年的一个平面
重叠了。同是在这世界上找平的人
怎么看,我都是他的路人
平,在他的笔锋下;不平,在我的步履间
那些长满眼睛的树
我在黑龙江的白桦林,看到无数只眼睛
淡白色的树皮上,那些黑色的节疤
总有着优美的眼眉线
瞳孔逼真,甚至见不到杂质
中国北极的大雪飘来,一定会落在
这些忧伤的眼眸里
我在武陵山的生漆树上,看到无数只眼睛
漆匠短促的利刃,一刀一刀
在树皮上割出泪眼来
像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假想的哀恸
漆匠把接泪的贝壳取走
一棵树就会停止抽泣
我在那么多的树上,看到了眼睛
众多的眼睛,也看到了我
从中国东北,到中国西南
那么多的树长出眼睛,探视我
逼视我,歧视我,藐视我
无所不在地,监视我这具,戴罪之身
拜台
新泥松软,有一个深深的凹痕
有人长跪不起
换成石头,变成拜台
石头,也需要一个凹痕
一个人的膝盖,无法完成
许多人的膝盖,也未必完成
一个村庄所有悲伤的力量
都在那个凹痕里
这个痕迹,一旦出现,就是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