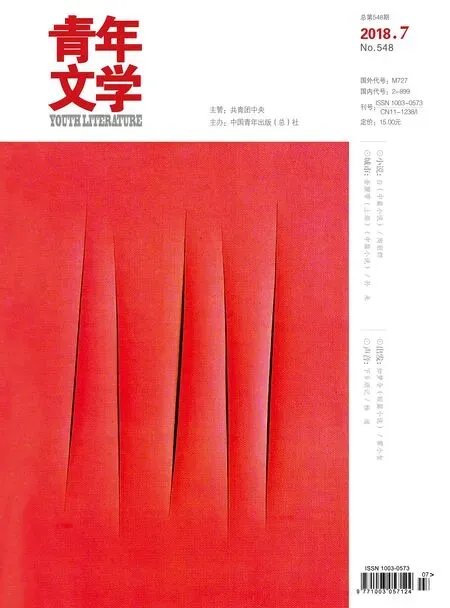谁在城市
⊙ 文/朝 潮
一
四月行迹诡异,忽暖忽冷,在别人的城市里游荡很容易感冒。昨日在烈日下大汗淋漓,今天在阴雨绵绵中打寒战。谁没有打伞。谁像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没有目的地在街道边奔跑,跑鞋已湿透,一个落魄身影融入街道人车汹涌的万顷波浪中。街面的水光,倒映出另一个城市。像童话世界。
谁很难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走路时总想着别的事,甚至想着一只猫的冷酷眼神。谁不喜欢猫。
在一个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谁在想某种交通规则的障碍。如果真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一定会以为城市人中蛊了,集体被羁轭和操控着。城市人借了钱买车,然后跟所有上班族天天拥堵在街道上,担心停车、碰撞、违章、扣分,下班回到家,再出去走路或跑步几公里来消耗体能。城市里住着的是一群欲望缠身的人,必须要用各种各样的规则来限制他们。限制通行,限制买房买车,限制跟别人同床……在人的世界里,大概只有想象还没有被限制,否则会乱成巨大的灾难。一只猫是没有限制的,唯一能限制它的也是人类。
谁在十字路口走神时,一群人已从他身边穿过,走到了对面路口。他想通行时,红灯又亮了。谁就开始集中注意力,读着红灯上的秒数;当人集中注意力于某事某物时,实际上是失散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至今没有哲学家能破译。失神和凝神通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人读秒时,时间的意义反而失散了;当十字路口的一条路线通行时,另一条路线是被封锁的。
每个十字路口停泊着一片云,车辆汇聚成的云。当某朵云违反规则时,就会与另一朵云发生碰撞。两朵云的电流发生对撞,就产生了雷。城市的天空中响起了春雷,像两辆车的猛烈撞击,零件散落一地。
春雷唤醒万物。
谁蛰伏了一个冬天,在春雷轰轰的日子,游走在别人的城市里。雨还在下。这是谁在冬天就立下的心愿,春天要在城市里独自游走几天,做一朵闲云,飘来飘去,不与别的云发生碰撞。谁已经几个月没出远门了。谁中了一种叫作自闭的蛊,一半是享受,一半是孤独——好比想象的每次飞舞都随绑着一百多斤的地球引力;飞得越高远,回到地面的冲击力越大。谁乐此不疲。某天,谁看到窗下的两只猫在谈情说爱,就知道春天已情不自禁,该出门了。
谁奔跑在城市里,不断舍弃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下着雨,春雷响了几次,像科林斯国王的巨石,一次次滚落下来。
在谁的眼里,城市只有一条路,一种摆设,一张面孔,一种思想。在谁的眼里,乡下也在学习城市的各种规则:笔直的水泥路,直挺的高楼,规划过的绿化。“朋克之母”维维安的叛逆人类设计,现在成了城市街头的主流。趋众是人类最明显的愚蠢之处。
在谁的眼里,前沿就是所有人的风向,也不存在所谓的先锋。
在谁的眼里,猫最不会迎合主人,最自我和孤傲。
谁不喜欢猫。
二
别人的城市里开着最美的花,发着最嫩的绿,下着最湿润的雨。住进城市客栈那天,天气晴朗,很热,谁只穿着一件短袖衫。客栈的一只猫目不转睛盯着他。谁进了房间,猫也跟进来。猫通身黑色,幽灵一样占据了窗口有利地位,蹲守着谁。黑猫用爪不断地挠着耳朵,挠几下,停下来定睛看着谁。老人们说,猫挠耳,是要下雨了。谁想走近它,黑猫马上伏低身子,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嘴里发出低沉的警告声音。黑猫的眼神是敌对的。谁有点不敢对视它的目光。
谁想起了传说中的九命猫妖,还有《圣经》中伪装成大黑猫的吸血鬼女巫莉莉丝。
谁佯装出门,待黑猫跟出来后,又迅速回房并锁上了房门。黑猫被关在了门外。谁大大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仰躺在床上。几分钟后,窗口传来一声悠长的“喵”。谁惊起身,发现黑猫已蹲在窗台上了,隔着玻璃盯着他。它到底要干什么?没有人能瞄准一只猫的动机。它是随心所欲的一种动物。
这只妖猫!谁在心里说。
晚上起风了。风没有规则,风声也妖,像一只怪兽间歇地发出低吼。窗玻璃随着它的频率在震动。冬天里幸存下来的树叶在经受考验,在风中凌乱,一部分已经失散在夜色的街道上。风声之外,整个客栈很安静。所有人低落着心情,躲在自己的小房子里。临近子时,不远处传来车祸的消息,客栈的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纷纷出去看热闹。没多久,谁在窗口看到了警灯闪烁的光。后来听到走廊里有人在说,一位出租车司机为了避让一只黑猫,车冲上了人行道,撞在一棵树上。车毁了,司机被送进了医院。
谁身上起了一层疙瘩。这只妖猫!
后半夜,谁在朦胧中听到附近猫的叫声。那叫声凄凉、骇人,刻骨铭心;它是在叫春呢,还是在叫魂,那种狐绝的声音深深安插在黑夜里,像一个幽深的黑洞。
三
第二天,谁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穿行;雨下大了,他就奔跑到能避雨的地方。谁在奔跑时,幻觉自己像二十年前那样意气风发。他爱慕街头不同与众的事物,新鲜的,或者突兀的,悲观主义者大多偏爱奇异。谁的心里清楚,他的价值美学只能通过其对立面才得以实现。很多人想要自由,又离不开规则;离开了人群的规则、汽车和房子的规则、钱和爱情的规则,他们就活不成了。占有就是被占有——这句话是一位叫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家说的。谁什么都没有,还是觉得不自由。
狗和猫们,可以自由奔跑在乡间山野,可它们宁愿被人类套着绳索,抱在怀里,享受物质主义的贵族生活。要什么自由和精神,那是用来嘲讽和批评的对象。当一大帮人在评说自由、精神和规则时,他们脖子上正套着汽车和房子、财富和名利的绳索。这个寓言千年传承。
幸好猫和狗只享受,不谈论。
第二天,谁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或奔跑时,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第二天下雨了,黑猫是个预言巫师。
气温降得厉害,谁加了一件衣服还是觉得冷。昨夜被车撞过的那棵树,裸露着一大块伤疤,旁边还残留着车子的一些碎片。谁去客栈对面的饭馆吃饭时,大家正在谈论那棵树和一辆出租车的故事。有的人吃完了,还特意到对面那棵树边参观一下,甚至拍个照发个微博什么的。
当天,谁拿到了一张地铁票,在地下飞速穿行了几十公里——这事要是放在一千年前的话,是个彻头彻尾的童话。童话的物质性很脆弱;精神性的不可动摇或不可颠覆的原因是,它原本就是根据人的意志、人的属性创造的。无论美丑、善恶,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偏见是余孽,个性反而是被各种规则打压的著名对象。
城市童话里,最难得的安慰是教养和仁慈,相对于白雪公主和卖火柴的小女孩。
下午,谁去了城市的不少地方。没有目的,谁只是在参观和体会城市的游客。傍晚前,雨已停歇。吃过晚饭,谁走进附近的一个公园。公园入口附近的椅子还是潮湿的,大多空着,只有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少年,整个椅子上垫着一块塑料布。少年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一本书。谁在公园里走了一大圈,用手机拍了一些花木,回到入口附近时,发现那少年还坐在那里。谁打算在他旁边坐下来,因为只有这张椅子垫着塑料布。谁说,我可以坐这里吗?少年从书本上抬起目光,绽放出笑容说,可以。少年热情,友善,长相俊朗。谁就在少年旁边坐下来。并排坐一起,谁与少年的鞋有了鲜明的对照:谁的跑鞋被雨水和尘土弄得狼狈不堪;少年的运动鞋像新的一样,款式时尚,红白相间。谁有点自卑。谁羡慕这样的年龄和长相,羡慕这样一双漂亮的运动鞋。谁的注意力又不集中了,在想自己的少年时代。后来两人开始聊天,聊这本书,聊天气。少年问谁是做什么的。谁说,他兼职在家做些文字工作,有钱了就出去到处乱跑。少年以真诚的眼光看着谁,说,大哥,我真的很羡慕你。少年那种清澈的眼神让谁无地自容。这时,一位女士推着一辆轮椅来到少年面前,说,儿子,该回家了。然后吃力地把少年抱到轮椅上。女士微笑着跟谁点了一下头,少年也跟谁道了一声再见。谁错愕地凝视着一点点离去的轮椅,注意力再一次涣散。
四
十点起床。谁只配拥有一个粗糙的上午,和一个乏善可陈的中午。幸好后来看到了窗外的一株含笑。含笑的香味类似浓郁的香蕉味。一枝含笑,挽袖静听;阳光啃啮着它的花枝,显得更加悠扬。
气温又开始回升了,城市人已在规划着下一个风流假日。房间里圈养几棵小草木、几尾小鱼,只是田园和文艺生活的自诩,他们更向往大片土地上花木的恣意生长;到了节假日,城市人会一窝蜂挤上车,一路挤到有山有水的风景区,挤到乡村去看油菜花、桃花,去农家乐摘桑葚、采茶……这跟生活、消费方式关系不大,主要是本性上的从众心理和集体世俗主义。人口密集处,病菌扩散很快,这也是城市的蛊毒之一。
抢购潮、旅游潮、广场舞潮、电视选秀潮……一个个浪潮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在扼杀人类个体意识里最富贵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平衡。每个人都害怕落伍,在追赶的路上把自己的一生搞丢了。他们的一生,过的是别人的一生,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生。
清明前,谁去老家扫墓。谁的母亲指着山脚下的一户人家说,这里住着一位一百多岁的老人(跟谁早年去世的奶奶同岁),从来没去过医院,每天还在院前院后的菜地里干活。谁不认识这位老人,只猜想生活在山脚边的人没有什么规则需要去遵守,不用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和证件。她守着自在的生活,和尘世喧嚣中圣洁的清静。
谁打赌,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少年时最鄙视的那部分。越成年,越庸俗,这是每个人从童话世界走进现实世界的必经之路。少年纯真是用来祭奠和赞美的。每个人在认识自己的路线上,总在不断美化自己,掩盖自己的恶俗和无知。
认识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否定自己。
在城市里住到第四天,谁准备回家了。谁看望一株含笑后,去对面饭馆吃饭。饭馆里没人再谈起那棵受伤的树,有人在谈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战,谈论股票、物价和叙利亚战火。
谁午后收拾了一下背包,去客栈前台结账。谁问老板,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家的那只黑猫。老板说,那猫不是他们家的,是野猫,只是经常过来。猫很有个性,老板说没人能靠近它。
一只生活在城市里的野猫,没有身份。它在有规则的城市里不会有好结果。
五
从前,有位少年热爱城市,长年仗剑行走于很多城市。
后来,少年中了城市的蛊,变成了沉默寡言的资深中年,选择在乡间生活。他就像寓言里那个刻舟求剑的楚人,一次次去寻找失落在城市江水中的那把少年时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