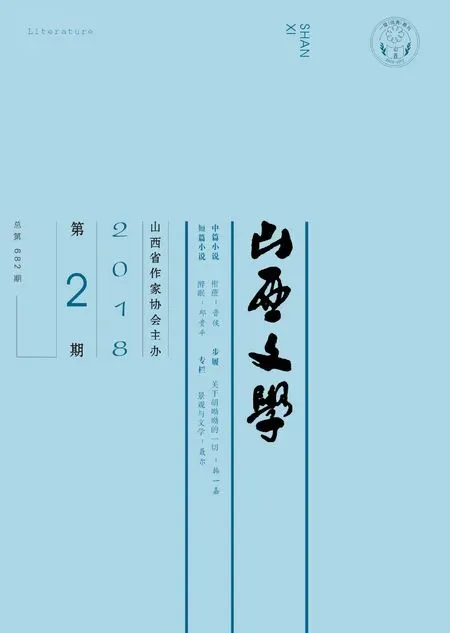古典心性与浪漫情怀
——弱水散文集《黑白盛开》中的女性意识
刘 剑
最早认识弱水,差不多是在十年前她的天涯博客,“弱水”这个笔名让人觉得文雅而又充满诗意。老子《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就像那水一样,是所向披靡,同时又是随物赋形的;它既有滔滔汩汩的气势又有细密温润的情怀,就像弱水的文字带给人的感觉。老子喜欢水,是因为水的品质“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厚德载物且沉默谦逊,善处下,善容人,就像弱水平时为人处世的样子,善于倾听、处变不惊、灵活通融、秀外慧中。古人认为是由于水羸弱而不能载舟,因此把这样梦想的河流称之为“弱水”。生活中的作家弱水是一位端庄秀丽的才女,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弱水也正是这样的智者。她总能以月光一样的温柔和流水一样变通的智慧悦纳周围万物,和所有的关系和睦相处;同时也能在文字中坚持理想,思索人生,批判社会,体验爱的绝望与孤独,有着山一样笃定的态度和火一样炽烈的感情。古典的心性和诗意的情怀就这样无缝对接于一身,成就了这样一位既有人文知性又有生命感性的才女作家和浪漫诗人。
古典的美:用知性化解生命的疼痛
弱水作品“文如其人”,有一种古典的美。古希腊作品常被看作古典美的范本,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赞美古希腊精神有一种 “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古典的美要求内容与形式、感情与理智的和谐,要求艺术的自由与自然规律之间的调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 -1832)在1802年写的《自然与艺术》的一首小诗中,曾经这样加以描绘:
自然与艺术好像分开,
但我们一想,就会发现它们的共同点。
代替斗争,和谐的歌声高唱
二者一起,走近在我的新房。
……
要做出大事,须得节制力量;
在自我的限制中方才显出手段,
在规律的下面方才有自由无疆。
按照蒋孔阳先生的理解,“所谓古典风格,”就是有点像“暴风雨后的晴空万里和惊涛骇浪后的清明澄澈”,这正是弱水散文带给人的第一印象,自然、素朴,就像一滴水一样单纯,像雨后的晴空一样明净,却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她的文字清新洗练,蕴含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奏感,宁静、理性、节制,在该静默的时候静默,该透明的时候透明。有别于诗歌中的弱水用语言的技巧将“自我”包裹起来,在散文中,她把自己打开,那样赤诚坦白地面对我们,从容地叙述过往,剖白心迹。散文集的开篇《与我们的性别和谐相处》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之作,却不像一般的女性写作那样剑拔弩张。而是经由自己痛苦的经历,达到了对两性关系认识的升华。这饱含着对“自我”与“他者”的重新认识。成长是痛苦的,但是这种认识的飞跃却是理智和清明的。在这个过程中,她克服了那些我们大家都会经历的生活矛盾,用知性和爱心化解生命的疼痛,达到了一个自然而又自由的心性境界。
“我”按照母亲的传统教育长成一个成绩优秀而又听话的好女孩,因为父亲的重男轻女,“我”从小抱定要自强,好让自己不逊于男孩。然而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忧惧、疼痛、危险却如影随形。当青春期来临的时候,我刻意隐藏自己内心的波涛,淡化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把身为女性,看作一种不幸,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疏远一切可以贴上女性标签的东西,不事化妆、厌恶琐碎生活,致力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人。“我”拒绝了青春期那些饱含明确欲望指向的异性追求,在冥冥中等待一份超越身体欲望的纯粹爱情。终于有一天,在寒冷的华山山顶上,一位和我一起看日出的青年,以他的赤诚感动了我,他用长臂撑起温暖的空间,为女友遮蔽寒冷,“在毛巾被狭仄的空间里,我们小心翼翼,保持着不被相碰的距离。我们听着彼此的呼吸,一动不动,象固化在琥珀里的两只昆虫,一起看着一颗金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山峰间慢慢升起,喷薄而出。自始至终,他撑着毛巾被的胳臂没有落到我的身上。我把这份爱看作是经过了肉体考验的纯粹的爱,是我信奉的形而上的爱。一生的选择有时只依赖于一念。”(《与我们的性别和谐相处》)然而,当作者终于与自己女性的身体和解走进婚姻的时候,却在婚姻中发现另一种不幸。多年的爱与痛、怨与念,也许都是性别带给我们的与生俱来的宿命。那个我们从小不愿面对的麻烦的、疼痛的、内忧外患的女性自我,将一直与我们同在;那个弱者的形象即便在外在功利中克服了,比如女性通过努力达到了男性达不到的生命高度,但是人们会一直认为你是有缺憾的。曾经那个你认为经得住人性考验、道德纯洁、值得托付终身的忠诚恋人,有朝一日也会成为一个深陷在沙发里的“沙发土豆(Couch potato)”,成为一个漠视妻子的才华和付出、不肯分担一点家务、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者。
尽管生活中到处充满了这样吊诡的逻辑,不时要与千疮百孔的感情和无法尽如人意的生活周旋,弱水却从不大声呼叫,怨天尤人;她是节制的,隐忍的,从不将伤痛示人,而是能够理智、平静地面对这些生活难题,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让这些心灵上经历的暴风骤雨渐渐变为云淡风轻。这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靠流行的心灵鸡汤自我治愈,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这里面有辩证看待事物的理性和通达,也有儒家古典人文主义的生命涵养和生活智慧。比如,作者可能一直对父亲的“重男轻女”耿耿于怀,但当自己婚后发现每到过年过节,丈夫总要承担比自己更沉重的家庭责任时,她渐渐明白了为何一个中国家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穷还是富有,都希望下一代中有一个儿子。“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认识到,作为儿子是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去履行责任的。而作为女儿,父母对我从未有过责任的要求,更不会将困难交给我,相反他们对我是一味的付出,呵护,担忧。” (《与我们的性别和谐相处》)儿子意味着生活压力可以有人接续承担,无论我们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子女,我们都能感觉做男孩的“累”和做女孩的“娇”,这和男孩在人们心中的“重”和女孩在人们心中的“轻”正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样的换位思考,让作者体会到了那些根深蒂固偏见陋俗背后的人性内涵。于是,对生活里常见的或显或隐的性别歧视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达到这样的理解并不来自于作者的软弱和妥协,而是通过内心的道德反观,实现了推己及人式的内心平和。按照孔门仁学,内心有大爱的仁者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在弱水宽容的面对人际关系的背后,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传统的家教和读书的积累给她带来的儒家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这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教养,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真水无香,润物无声。
在知性上理解了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弱水在自身意识里完全向传统意识妥协,止步于认同现实社会对女性“第二性”的文化建构。在这里,强者的宽容和弱者的妥协区别只在于,“自我”是否能达到俯视继而审视这一切的人生高度。弱水毕竟是一位现代女性,实际上,按照她的成长经历,她一直走在女性自立自强的路上,没有被任何偏见束缚住个人飞翔的翅膀。当这些生活的“烦”和“闷” (海德格尔语)无处排解的时候,她发现了写作的奥秘。写作始而作为一种生活的陪伴抒发感情、缓解孤独,继而作为实现自我、反思人生的一种方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用写作照亮了自己的存在之门,并通过写作进一步确证自己。在那里,她遇到阿赫玛托娃,遇到汉娜·阿伦特、苏姗·桑塔格,遇到西蒙娜·薇依和弗里达等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女人们,她们是女诗人、女艺术家、女思想者,她们每一个都才华横溢却命运坎坷,然而她们每一个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荡气回肠的人生。弱水曾经模仿阿赫玛托娃的口吻给博客签名写道 “我已学会一种简单而明智的生活,瞭望天空并祈祷上帝”。她可以宁静地满足于自己构筑的精神空间,体验其内在的丰饶和充实,从而不去计较现实的荒凉和贫瘠。
然而即便在这种对生活的低限度要求中,写作与职业、家庭仍然常常出现矛盾,弱水写道,“不止是我的他,包括我的父母,他们认为一个女人除了工作之外,就应该以履行家庭职责为主,其实工作也是为了家庭给养。而与家庭无关的阅读和写作,则是有违家庭道德的。”(《与我们的性别和谐相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对于家务和写作之间的冲突,世人对待男人和女人是持守双重标准的。一个男性作家“会因为写作得到家人更多的尊敬和包容”。人们对男作家(如钱钟书)不懂日常杂务、生活能力略逊于常人,就可以宽容理解且还传为美谈,妻子杨绛在背后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而对一个女作家来说,她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多面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否则就难以在世人眼中自全。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弱水是一个“不仅书卷气浓而且烟火气重”的诗人,这半是因为她热爱诗歌也热爱生活的天性,也半是因为她要和自己扮演的多重社会角色相调和。如果她在追寻理想的路上稍微忽略了“烟火气”的日常杂务,那么来自周围亲人、熟人异样的目光和无言的指责,肯定是许多男性写作者无法想象的。对她而言,“无论在文字中如何获得突破的自由,生活依然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我当然不敢抱有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 -1941)那样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也不愿向传统男权思想做彻底的妥协,而是努力在妥协与坚持中创造一种平衡,在履行好传统女性家庭职能的缝隙中,坚持以读书、思考、写作,争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由,实现对自我存在的确认。”(《与我们的性别和谐相处》)她在这个妥协与坚持的过程中找到一种难得的动态平衡。
正如史铁生所言,“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既然不可能放弃事业也无法完全舍弃家庭,她所要做的就是在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个称职的白领,一位合格的母亲和一个孝顺的女儿等多种社会角色之间来回穿行。她麻利地应付完所有的日常工作和家庭杂务之后再拿起笔,独自面对属于自己的写作之夜。不是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身处这样一种忙碌而多维的生活状态中,仍能做到游刃有余,心无旁骛,仍能写出美丽睿智的诗歌和散文。这让我们在钦佩弱水有着堪与写作能力相媲美的生活能力的同时,也不禁感叹,她要付出多少常人无法想到的辛苦和努力,才能达到现在这样一种从容、丰实而又和谐的人生状态。
同时,弱水有别于大多数女性写作者,并非只将自己像琥珀一样包裹起来,而是能够随时将她的人文理性投射到周围世界,她能感知自身的生命疼痛,也能感受这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无人代言也无力发声的“病”与“痛”,这使得她的散文克服了大多数小女人散文的“自恋”和“自怨自艾”,从而通向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较之大多数女性写作多了一层公共关怀。她是一位有着自主的价值立场和自觉的写作意识的作家,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她不是只像一个“乖孩子”一样“悦纳”生活抛给她的一切,而是会像一个哲人一样,跳出世外,站到一定的高度去反思那些在我们也许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从那里看出“症候”和“问题”。这种“在世”写作是如此的自然平易而又深接地气。
当她走在太原的街头,走在西单路口,常常会面对着芸芸众生纷繁人事展开无限遐思。通过《府东府西》《小D回家》《公交车上的女人》等文,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人间世的关心和对“小人物”的体察。她不仅面对自我生命中那些难题运用理性去化解,而且也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世变迁和两难困境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她看来,“文明的生长有它自身的逻辑,一个个原子般的个人,唯有在外部世界的冲突中保有内心的和谐,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一场浩大忧伤的雪——读奥尔罕·帕慕克〈雪〉》)。她对世事的关照里既有深切的希冀,也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当她看到府东府西街道两旁的沧桑变化时,她写道,“我多么希望拆建工程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拥堵的车流畅通道路,而同时可以拆除强与弱的距离,掠夺与被掠夺的对抗,建立一条通往令人向往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秩序的道路,那才是对这个生死相逐、新旧交替的大时代的真正呼应。”(《府东府西》)在她笔下,有穷人与富人,强者与弱者,喧嚣的少数人与沉默的大多数;经济的热闹与萧条、权力的边界和限度,人生的荒诞悲凉,命运的反复无常。一个个人物和场景向我们走来,那样活灵活现,带着他们独有的个性。弱水的散文虽不刻意,却随处可见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她的写作不仅是我们了解“自我”的一扇窗口,也是我们重新发现世界的一扇窗口。
人文理性:在反思中探讨爱的真谛
弱水对爱情并非只有一厢情愿的相信,也有深刻的怀疑和反思。有时她也会无意中吐露对爱情本身的幻灭。在《爱在午夜飞行中》(《Midnight Fly》)中,一个面临丈夫出轨的香港妻子和一个爱上已婚男人的日本女孩在异国的旅行中偶然相遇,且成为知己。当女孩最后得知他们爱的是同一个男人的时候,一时经不住内心冲击而出走,遭遇不测生死未卜。而那个匆匆赶来的香港男人,不过陪妻子在摩洛哥努力找寻了几天无果后,就准备接受现实和妻子重新开始生活。妻子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男人之爱的平庸和现实,弱水淡淡地写道:“爱一个人,不过如此。”简短八个字,却有天风海啸般的力量,让人骨折心惊。如果走失的不是那个女孩,而是这位妻子自己,丈夫的表现估计也不过如此。“男人的爱大抵如此吧,李敖的‘只爱一点点’,胡兰成的现世的爱,都是现实主义的。只有女人,才怀抱着爱的理想,为了爱,生死都是不重要的。” (《爱在午夜飞行中》)影片结尾这位妻子没有随丈夫回香港,而是最终找到了那个女孩,她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女孩的新生。这个作品中男性偶像的坍塌以及对异性之爱的幻灭属于典型的女性主义话题,它隐含肯定了一种超越现实利害的女性之间的情谊,只有同样爱得深、爱得痛的女人们之间才真正惺惺相惜。女性虽然天性柔弱,但是她们更加感性,情感品质更加专注,关键时刻道德责任感更强,有一种为了真情不计得失九死不悔的执著。也许这个故事中夫妻两人不仅性别不同,也恰好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一个比较浪漫,一个比较现实。恋爱双方要想共同追寻理想的爱情,需要对等品质的忠诚、执著、浪漫和深情,就像茫茫人海蝼蚁众生中两个一看就能辨认出对方的精神贵族。而这样高标的要求一遇到现实生活,或是具体到某个恋爱对象的时候,马上就会变得捉襟见肘。就像张爱玲所说:爱情的尽头,是一眼眺望得到的虚无。
如果爱情的尽头是虚无,如果爱情一遇上具体的对象就马上会露出颓败、荒凉的底色,如果爱情让人渐渐地失望乃至彻底绝望只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爱情,去追寻爱的幸福呢?经历爱情的痛苦和幻灭,对于这个问题,弱水的回答依然是含蓄而且意味深长的。“到底爱情可以持续多久?有永恒的爱吗?我还是要说我不能回答,而不说我不知道。就像我们看不见太阳以外的其他恒星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存在着。我们不能说不知道,只是看不清,所以不能回答。”(《身体之痛》)虽然永恒的真爱在生活里并不常见,但是她还是愿意相信它在某个地方切实存在着,就像有基督教信仰的人相信上帝存在一样。伏尔泰说,假如上帝确实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创造一个出来。因为相信爱情的存在和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可以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寻找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正视自我、矫正自我的过程。在爱人的眼光里,每个女性试图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或者试图成为那个理想的自己。很多认真思考过爱情的女人一般都认同张爱玲冷峭的爱情观,认识到异性之爱是不完美的;但同样的理性也会告诉我们,女性自身也并不完美;并且,也许人生本身就是不完美的。
怎样在爱中超越自我,获得内心的成长,克服完美的诱惑,弱水对《黑天鹅》的解读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黑天鹅》是对传统《天鹅湖》故事的反写,她对人性的设定和理解类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性本是善恶二元并存的,随着具体情境而改变。“人文主义者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与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人身上的这个美德的真正标记,正如帕斯卡尔所言,是人协调他自身相反美德的能力,以及占有这些美德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toutl’entredeux)”。每一个人都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既是白天鹅,也是黑天鹅。身上时刻经历着善与恶、白与黑、理性与感性的天人之斗。“白天鹅的身上,活跃着黑天鹅的野心和力量;黑天鹅的心中,隐藏着白天鹅的柔软和脆弱。黑与白的纠结,善与恶的胶着,既是自然的,又是矛盾的,交织成演员所要突破的困境。”(《黑白盛开——电影〈黑天鹅〉观感》)而演员最后经历灵与肉的分裂与重生,以一己之身分饰了两个角色,完美地演绎了人性内在善恶冲突的本质。女主人公妮娜终于在最后追求到了梦想中的艺术完美,体验到了成功、爱与自由的欢乐,但也在抵抗压力浴火重生的同时,因精神分裂而自残走向了毁灭。弱水在结尾写道,“没有比死亡更极致的美,没有比毁灭更完美的艺术。”艺术是向死而生的,追求完美本身就包含了自残的倾向;幸福都是平庸的,要极端的美就要体味深处孤独。艺术与道德、天性与人力、黑暗与光明,幻想和现实,影片用充满张力的镜头语言让我们看到了“盛开在每个人体内的那朵黑白妖娆的恶之花”。
我想弱水的写作也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也许是这本散文集以《黑白盛开》命名的原因。在生活中她是白天鹅,善良纯洁,温柔端庄,宁静坚忍,善解人意;在艺术中她是黑天鹅,浪漫激情、才华出众,追求完美,渴望爱与自由。就像歌德和席勒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样,她从小深受古典的教养,经历过爱的苦痛与幻灭,最后用理性化解生命的冲突,和自身的处境和睦相处,重回古典的静穆平和。在追寻爱情理想、实现完美自我的路上,有通途,也有险径。与其铤而走险,顺从欲望和激情,燃烧自己走向毁灭,不如退守高贵的孤独,在痛苦中淬炼生命的智慧,从而超越自我,走向澄明。也许,并非所有女人对爱情都有洁癖,只是有些女人,宁愿承受清醒的孤独不愿享受稀里糊涂的幸福。这样的爱看似犬儒,却依然充满了希望。“我更相信爱是一条道路。由两个人建造的一条道路。它没有目的,也不被拥有。在未抵达之前,我们并不知它将通往何方。它永远处于‘在创造’的状态,以幻梦般的‘不可知’在时间中延伸。” (《爱是一种抽象的期待》)这样的爱因为从未开始,永远没有结束;它永远在探索,永远在进行,它就像我们伸向远方的希望。能承担这样一份“抽象的爱”源自女性精神深处的自足与丰盈,它是一个敞开的姿态,在向世界发出吁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