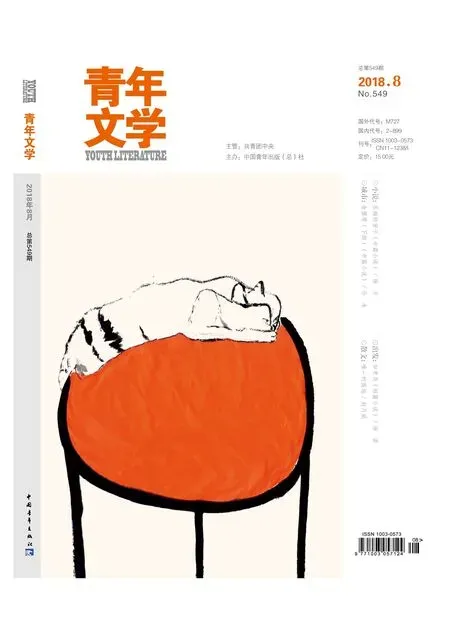没有雪的冬天
⊙文/徐 诺
我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书中度过的。那时候,南方还没有下雪。至少从我出生到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它之前,我对冬天和雪都毫无特别印象可言,即使在某个阶段亲身经历过了,也像是个局外人。依稀记得是一个暑假,我还在上小学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莫名地想起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名为《雪国》的书。我见过这本书很多次,但一直没有拿起来翻阅过。跟它挨在一起的是一本《千只鹤》和一本《古都》,作者的大名赫然写在书名的下方——川端康成。
这是个古怪的名字,却让我的人生另起一行。第一次阅读川端康成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对他所描绘的那些节日和场景都感到新奇。至今我还记得《雪国》的开篇,这对于看什么都健忘的我来说,实在难得。川端康成对雪的描写,直到现在都还能让我产生清奇和悲哀的感觉,也正是他赋予了小说不一样的基调,才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雪,喜欢上了悲剧,但并不是那种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的悲剧——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般让人肝肠寸断,了无生趣,而是让人看了心有悸动,若有所思,从中可以看到悲伤,看到惋惜,甚至看到自己。后来,我读了岩井俊二的小说,才更加确信了一句话,“冬天往往发生在悲剧里,悲剧往往被埋藏在雪中”。
二〇一二年年末,我去了英国。这里没有川端康成,没有岩井俊二,但我写完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虽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几篇小说,它们姑且可以被称为“轻悲剧”,但始终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我觉得我还不能在它们当中看见自己。“也许是因为它们没有冬天,没有雪吧!”我这样告诉自己。很多人说,写小说要贴近生活、观察生活,然后高于生活。这句话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错,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种对小说的修饰,都让人无法反驳,但这也正是它的危险之处。许许多多小说,急于呈现一个故事,急于把现实改编成文字让人们阅读,却背离了小说该有的样子。在我的过去的几篇小说里,我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小说不是单纯的故事,而是载体;它承载的不该是故事本身,而是审美情绪。脱离了这一点,小说就像一个人,活着的只是心跳,而非自身,最终成了活死人。也正如此,我在英国完成的那几篇小说,其实只是故事罢了,它们看上去完整,无奈没有承载起我的审美情绪,徒有躯壳。
我尝试着去完成一篇充满审美情绪的小说,可它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因此我总是想回到“原点”,回到阅读川端康成和岩井俊二的日子,回到那个有雪的冬天。也许,当我们看惯了冬天的萧瑟与荒芜,就会去怀恋它下雪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