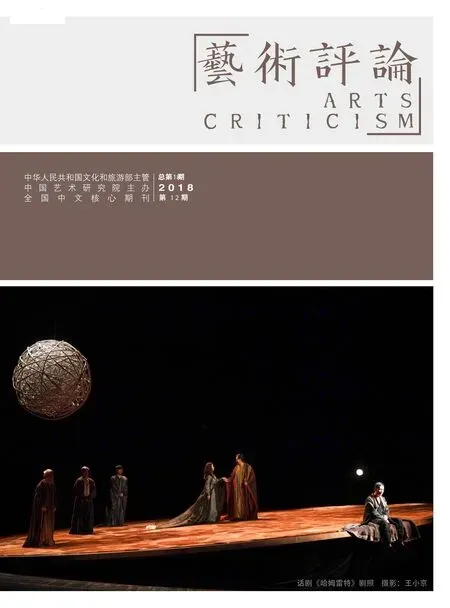这是一种博大的情怀
——大型民族舞剧《乳娘》观后
于 平
舞剧《乳娘》说的是“乳娘”的故事,说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抚育革命后代的胶东“乳娘”——胶东“乳娘”是一个令人景仰的群体,经她们抚育的革命后代就达千余人之众。这使我想起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段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的,如果不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她们怎会心甘情愿去做抚育革命后代的“乳娘”!
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许多被抚育的革命后代,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爹娘。但他们肯定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一个崇高的信仰;他们也切身地感受到,在那种“义无反顾”之后是因为“情有所寄”——他们献身于崇高信仰的父母,为自己爱情的结晶、也为自己未竞事业的继承者,找到了寄放自己的骨肉、同时也安顿自己心灵的“乳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乳娘”岂止是养育了“革命后代”,她们也实实在在地养育了“革命”,养育了我们的“新中国”,养育了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这就是说,我们的志士仁人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一个崇高的信仰,支撑着他们昂起的头颅的,还有这样一种博大的情怀——它或许不像“狸猫换太子”的“程婴救孤”那样惊心动魄,但同样是值得我们罄竹以书、永垂青史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的师生们,认为把“乳娘”精神载入史册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是为先烈们的“义无反顾”做一个深刻的注释,是把这个深切感动了自己的“博大精神”化作强劲的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征途中书写新的青春篇章!于是,他们创编了大型民族舞剧《乳娘》,总导演为该院舞蹈学院院长傅小青。
舞剧的序幕题为《生》。先是在台沿的纱幕外,由上场门向下场门走着一位待产的孕妇;那着意强化的“胶州秧歌”的拧碾步态,似乎在强调人物的地域属性(因为这种“拧碾步态”与孕妇的行走无关)。当这位农妇装扮的孕妇从下场门远去后,迅速拉起的纱幕让我们看到的是战场的一角:浴血奋战的军人似乎不用贴上“地域”的标签,他们的匍匐动态是作战行为的提炼与编排。你正在疑问这两个舞剧时空有何内在关联?在那排浴血奋战的军人身后,奋不顾身地奋战着另一位女军人——这居然也是一位待产的孕妇。无疑,“待产孕妇”就是这两个不同时空的内在关联,这个内在关联让你联想到一个成语“生生不息”,而这个内在关联也让你明白舞剧故事将要在这两位母亲和她们将生的婴儿中展开。
舞剧的第一幕叫《离》。《生》之后就《离》?对!不是说婴儿与母体的脱离,而是说其中一位母亲要与她才出生的婴儿分离。部队要转移,那位作为军人的母亲把孩子托付给了也才生育了的农妇母亲。在剧中,军人母亲叫原芳,农妇母亲叫秀珍;原芳生的是男孩叫利民,秀珍生的女孩取名杏花。在原芳向秀珍的托付中,观众都明白了“乳娘”就是秀珍,秀珍是舞剧《乳娘》的女首席。舞剧结构的重要特征是结构“人物关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围绕女首席来结构。因此,舞剧《乳娘》在人物关系上结构了秀珍的丈夫春旺,他在这一幕作为“支前”(支援前方的军人)队员也要出发;“乳娘”秀珍在接受托付之时,也将与自己的丈夫别离。在这种不得不“叙”的叙事中,舞剧叙事如何避免陷入“哑剧”的泥淖呢?如同现在许多舞剧所追求的,那就是用群舞来营造叙事的情境,舞剧《乳娘》在这一幕设计的是“农妇”的群舞——它既可以视为“乳娘”秀珍所置身的群体,也可以视为一个扩放了的“乳娘”,一个扩放了的人民对子弟兵的挚爱,一个扩放了的“革命战争伟力最深刻的根源”!
舞剧在《离》这一幕安排了双重的“离”,即原芳托孤的骨肉之“离”与秀珍别夫的亲情之“离”。相比较而言,原芳之“离”更为悲切;但秀珍的“离”意味着她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在隐忍中更升华出一种悲壮!虽然强调的是“离”,但这一幕是结束在秀珍对两个孩子的抚养中,孩子的成长及其未来的命运,显而易见的是“乳娘”秀珍性格刻画的重要依托!第二幕《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编创理念。第二幕当然也需要“情境”的营造。与序幕男群舞的“军人浴血奋战”和第一幕女群舞的“农妇深情育孤”有别,这一幕开场便迎来了“男耕女播的大群舞。这是人民群众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但场刊上却要写做“乡亲们在为支前耕耘和播种”。虽然“耕耘和播种”也用于“支前”,但强调“日常性”会显得更平实。这个大群舞从“耕耘和播种”的动态中提取“动机”,与序幕“浴血奋战”的“动机”提取方式具有一致性;相形之下,一幕的“农妇群舞”似乎没有找到准确的日常生活动态作为“动机”的提取,只能将秀珍作为孕妇时的“胶州秧歌”的拧碾动态作为“动机”,创编者更将其定位为“乳娘群舞”。在我看来,这个“农妇群舞”如果从“绱鞋”动态中提取,整体的叙事风格会更加统一——一者胶东妇女绱鞋“支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者在“缟鞋”的情境中会通过“慈母手中线”的隐喻来喻示“乳娘”养育的艰辛。
作为舞剧叙事,第二幕《死》想要陈说的是秀珍丈夫春旺和女儿杏花双双遭遇的不幸。先是丈夫春旺在“支前”中不幸牺牲,他的遗物——也就是秀珍替他绑在身上的蓝印花布包袱被人带回;接着是日寇“扫荡”,女儿杏花被乱枪击中……在日寇对华入侵实施的“三光”政策,秀珍遭遇的“祸不单行”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在舞剧叙事中,由于这个“祸不单行”是在两条线上进行,对于二者间的纠葛似乎还缺乏有机关联;这使得丈夫的牺牲与女儿的惨死显得有些刻意而为,舞剧叙事的节奏显得有些过于急迫……我曾想,这一幕戏剧行动不妨安排丈夫春旺“支前”归来,在与家人团聚时遭遇日寇“扫荡”;此时夫妻两人各带一个孩子躲避,而带着女儿杏花的春旺双双遭遇不幸——这时还可以有一段父女的双人舞,使得舞剧叙事在叙中有情并以情带叙。这一幕中有一段以竖立的“土炕”为“舞台”的舞蹈——舞者借助“土炕”的支架摆弄各种造型,显得在刻意使舞蹈编创“出新”……这种游离总体风格的“出新”,我以为有“蛇足”之嫌,大可不必。
编创者把第三幕称为《别》。与此前的序幕及一、二幕相联系,你发现是对成语“生离死别”的拆分。我总觉得,这种构思看似显得精巧,但其实也给舞剧叙事的铺陈和递进带上了“镣铐”;这种幕次命名形成的“镣铐”,让人觉得舞剧叙事在不假思索、毫无悬念地奔向结局……所谓《别》,是“乳儿”利民与“乳娘”秀珍之“别”;“别”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利民的生母原芳回来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利民与乳娘秀珍之“别”其实也意味着与亲娘原芳之“聚”。这一幕照例也要设置情境舞蹈,以“鼓子秧歌”中“伞头”为主的动态再着以红火的服饰,体现出“解放”的欣喜和欢畅。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乳儿”利民与“乳娘”秀珍却处于欲舍难分的悲情之中……我忽然觉得,该剧每一幕(包括序幕)的“情境舞蹈”与人物的“叙事舞蹈”之间,都呈现出一种“差异性”的反衬:比如序幕中在“浴血奋战”的激烈中反衬出原芳和秀珍将要分娩的宁静;比如一幕中在“乳娘”群体的慈爱中反衬出原芳“托子与人”的决绝;比如二幕中在“耕耘播种”的平和中反衬出春旺与杏花惨死的悲恸;还比如三幕在“红火秧歌”的欣喜中反衬出利民与秀珍别离之感伤……全剧的尾声叫《望》,当然是乳娘对乳儿的不舍之情,也是乳儿对乳娘的感恩之心——这个“感恩之心”就是我们应该永远持守的“不忘初心”!
对于舞剧《乳娘》的编创而言,首先,应当高度肯定创编者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的融入生活、讴歌人民;“乳娘”的故事,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且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在情境舞蹈中除“实指性”舞蹈外,还可以考虑“象征性”舞蹈的设计。这可以改变舞剧叙事因直奔结局而仓促浅显的状况。第二,应当充分肯定创编者对于舞剧构思的精心设计。但我以为,此剧不必设“序幕”,“生、离、死、别”直接构成一、二、三、四幕即可。在《别》这一幕似应有生母原芳意欲将利民留在乳母秀珍身边的细节,这样会使原芳这一人物更血肉丰满些。第三,还应当充分肯定创编者初步建构的舞剧“形式感”——这便是“情境舞蹈”与“人物叙事舞蹈”的场景设置与情感关联,这增强了舞剧叙事的清晰性和感染力。第四,创编者舞剧的语汇设计上体现的某种自觉也值得肯定——这便是日常生活动态的选择提炼及其“舞蹈化”编织;但与之相关,山东民间舞、特别是“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的舞蹈素材如何成为人物恰到好处的“性格语言”,似还有再琢磨、提高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