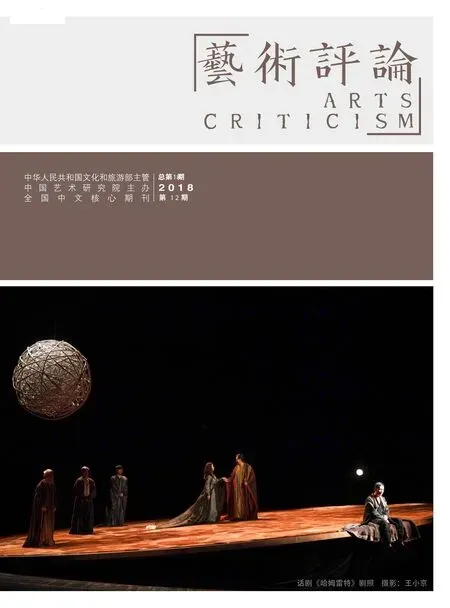漫谈歌剧的冷和热
王洪波 徐文正 韦 锦
王洪波:歌剧热的出现已有好几年,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评头品足,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对此进行梳理不无必要。
韦 锦:歌剧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产原创歌剧的制作热,一是外国经典歌剧的复排热。今天的漫谈是不是先着重前者?
王洪波:好的。我们的国家院团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中央歌剧院,一个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前者标榜西洋歌剧,后者以发展民族歌剧为指归。但多年来,歌剧走向大众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甚至连一般知识分子也都没有走近。也就是说歌剧还没有真正火、真正热。不知近年来,是由于某方面的倡导,还是文化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歌剧的制作,突然成了比较热的话题。
除去以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歌剧院为代表的专业歌剧院之外,一些大型演出场所,如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等,也开始制作歌剧,而且上规模、成系列,与原有的院团体系相激荡,激发了歌剧创作与演出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自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民族歌剧怎么做,西洋式歌剧之路怎么走;如何处理原创与经典移植的关系;如何看待歌剧繁荣表面下的良莠不齐与资源浪费等问题;如何预判歌剧在未来的发展,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话题。
徐文正:近年来歌剧的繁荣确实值得注意,每年有大量新作品上演,有人称为“井喷”现象。而且现在参与制作的单位中,高校也是值得注意的群体,像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一些综合性大学。如北大专门有歌剧研究院,每年也上演许多作品。
韦 锦:今天为什么出现歌剧热?许多朋友在问。歌剧是综合性强的艺术形式,是文学、音乐、表演、舞蹈、美术、服装设计等众多艺术手段的整体呈现。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艺术的要求、对综合艺术的要求更迫切了。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对综合艺术有所期待了,才会有那么多人致力于歌剧制作。由此可以初做判断,歌剧热的出现是人们的审美需求从单一化、平面化向综合化、立体化发展的必然。据此看来,歌剧热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可能适应需求不断持续、不断升温。但愿它不是呼啦圈和广场舞,不是发泄式的无序喷发。而这就要把歌剧热出质量、热出水平,让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焕发光彩。在我看来,“歌剧”一词的结构,既是偏正,也是并列。歌剧是用音乐表现的戏剧(亚历山德罗·斯卡拉第语),也是音乐性和戏剧性有机融合的独特种属。从音乐性的角度说,一部歌剧应该是具有整体结构的交响乐,而不是歌曲集锦(或唱段堆积)。而从戏剧性的角度说,它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设置情节冲突,而是着力于呈现情态,即呈现环境、背景、事件、氛围、人物心理的即时情状和形态。构建音乐张力是繁简取舍的重要尺度。缘此,它的语言要首先是诗,而不是板腔体的填词,否则就很难和曲艺进行区隔。它不能把其它品类的特色当成自己的固化模式。而且,歌剧语言应该是新诗、自由体诗,讲究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而不只注重句式和韵脚。应该更适合音乐体现的多层次、多维度。
徐文正:歌剧到底是“歌”还是“剧”,在歌剧史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莫扎特曾经说过,“戏剧应是音乐顺从的女儿”,瓦格纳认为“歌剧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我国著名作曲家金湘也提出“歌剧思维”的理念,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音乐的戏剧,戏剧的音乐”。但无论哪个观点,其中都包含着音乐与戏剧两个不可分割的元素。我的观点是:歌剧就是歌剧,既是音乐又是戏剧,同时既不是纯戏剧也不是纯音乐,而是两者杂交的一个混合体,音乐和戏剧在其中是高度融合、不可分割的。您刚才说歌剧音乐就是交响曲,但是如果真的把戏剧抽走只留下音乐的话,那会显得不完整,和纯音乐相比,离开戏剧还是不能活的。同样,如果把音乐抽走只留下戏剧,其剧本也显得不完整(和纯戏剧相比)。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音乐和戏剧的关系就好像是灵魂和躯体,音乐是灵魂,戏剧是躯体,戏剧离开音乐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音乐离开戏剧也就成了没有躯体的孤魂。
韦 锦:说到这儿又想起今年5月,洪波和我去广州看演出,他说没有任何一部歌剧音乐不好还能不朽。我觉得有道理,剧本写得再好,音乐不好,那也不会作为歌剧流传。这说出了作曲的重要。但这样强调,并不构成对剧本创作重要性的否定。如果一部歌剧,音乐又好,文学性又强,它被观众接受并得以流传的可能性就更大。
徐文正:但这好与不好的界定还有个艺术观的问题,一些经典名作也有人认为不好。尤其是随着时代发展,一些艺术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传统的歌剧观念比较看重“剧场效果”,强调戏剧冲突激烈集中,甚至提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性”的观点。然而从上世纪开始,一种新的思潮开始出现,即淡化情节、淡化外部冲突。
韦 锦:这和文学上的现代、后现代很相似。意识流啊,魔幻啊,反抒情、冷抒情啊,流派及相关的说法很多。其实,若想扎实点儿,能既古典又现代,能不玩花样又写得像样并不容易。
徐文正:我曾同某位编剧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人指出他的剧中没有对立面,没有冲突,作为歌剧剧本是失败的。他说他强调的是内心情感而非外部冲突,是用情绪作为戏剧发展的推动力,也就是“情绪布局,音乐填充”。
韦 锦:几乎所有成功的歌剧,它本身的文学性都非常高。在结构上富有张力的文学框架能使音乐获得必要的纵深、侧面和立面、维度和层次,会强烈、持久地打动人。不是用了一些新的手法就一定先进或先锋。刀锋的锐利离不开刀身的厚和韧。那种对人性的关注和不断贴近、对心灵空间诸多可能性的持续挖掘,才是艺术品在变动不居的人世间寻求永恒的途径。
徐文正:有时我思考歌剧到底要不要剧场效果的问题。就是观众在看戏,在剧场就应该得到让我感动的东西,让我哭让我笑,让我随着音乐和剧中人物的情绪而起伏。而我刚才说的那位编剧朋友就是另外一种追求,他不喜欢那种大的、强烈的、明显的对比,而是要观众慢慢地品味、感觉其中细微的精致的变化。但这就势必削弱剧场效果,跟观众离得远了。然而这是他的歌剧观,而且付诸实践了。但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有多少人能理解和接受,这就有点像“高山流水求知音”的感觉了。
王洪波:作品必须有思想性,但是必须把思想转化为艺术形态。现在有很多歌剧思想性很好,但艺术性很差,人们照样不喜欢。当然,既无思想性、又无艺术性的歌剧也不少。真正的好作品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
韦 锦:我和洪波经常谈到一个人,一个很值得敬重的、当代最具思想力的史学家刘泽华先生。刘先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有思想,有感情。他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是充满了感情的思想。他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充满了思想的感情。我在悼念他的诗中称他具备的是“有感情的思想,有思想的感情”。
王洪波:歌剧也需要这样有思想的感情和有感情的思想。那样的歌剧才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立起来,有血有肉,有温度,有亮度。
徐文正:对,这也是我的观点,歌剧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同时,歌剧的综合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歌剧之所以成为歌剧,它一定有单纯的文学、单纯的音乐所不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否则它就不会成为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的艺术形式。它是戏剧与音乐化合出来的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舞台艺术形式。
韦 锦:前些日子好好品味了国家大剧院出品、郭文景先生作曲、徐瑛先生编剧的《骆驼祥子》。像这种有思想、有感情、对底层小人物的疾苦不冷漠也不滥情,对处于什么境地、什么阶层的人都怀有悲悯的作品,实属少见。
王洪波:如果一部作品不能拓展人们的心灵空间,拓展人们的审美空间,只是就一些陈腐苍白的话题,没有任何新意地反复说,就会滞塞歌剧的发展。
韦 锦:最近看歌剧《西蒙·波卡涅拉》,被震撼了。威尔第作曲,皮亚韦编剧,主角是13世纪热那亚总督,西蒙·波卡涅拉。这个人是海盗。一个海盗做了总督,而且是非常伟大的总督,有意思吧?里面有爱情、亲情,也有阴谋、叛变、误解、猜疑、仇恨等,所有的情感要素都具备,包括总督和群众、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除了故事性,就是它的思想性、艺术性,那种深度契合人类文明走向的“先进性”,那种至今仍不失先锋性的特异和卓然,令人佩服。海盗的岳父要杀死海盗,岳父是贵族,在他看来,海盗不仅和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阶层作对,并且拐骗了自己的女儿,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女儿一生的厄运、自己统治地位的丧失,都是这家伙造成的。而这个海盗处处表现出宽容和大度,又和贵族阶层的偏狭形成了对峙,因此他的岳父多次想杀死他。生死攸关之际,岳父抽出剑,而波卡涅拉却亮出自己的胸膛,“杀死我吧,把你的仇恨和我一起埋葬吧”,太棒了。
如果这个情节出现在电影里,说“你杀了我吧”就完了,但在歌剧里面却是“把你的仇恨和我一起埋葬吧”及接下来的一大段咏叹。它不是简单地把感情拉长,也不是一般的渲染,它把它放大,让它继续“生成”,生成一种新的东西。情节在运行的中途定格。但这个定格又不是静止的定格,是流动的定格。定格在此处的故事不再发展,让人驻足、静息、仔细打量、凝视。
王洪波:在这儿它给延长了,是一种特殊的定格的方式。
徐文正:这也就是歌剧里面的好多场面如果用常情、常识来看是不合理的,但却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比如说,在好多歌剧作品中,主人公临死之前还要唱个大咏叹。
韦 锦:看上去的反常在这儿非常正常。类似的还有《艺术家的生涯》里咪咪临终的咏叹调,《托斯卡》里主人公临刑前的咏叹调等。
王洪波:这里存在一个对歌剧创作一般规律的把握问题。对于歌剧,它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需要有个共识。需要创作方、观众方都能有共识。这里面有大的规律,也有小的规律。由于舞台艺术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所以不能因为是小的规律就不重视。韦锦刚才说的流动性定格,就体现了戏剧呈现过程中的一个规律。该停下来,没有停下,然后转了,而故事推展不到位,这时观众就会觉得不过瘾。比如,听郭德纲的相声,他不时会有一个“咦——”,这时大家特激动,这激动的前提是他此前一定讲了特别打动人的段子。这个“咦——”等于让人回味沉淀一下,同时自己也有些自嘲。戏剧也是这样,有时候跳出来自嘲一下,抒发一番,戏里戏外就会呈现一种特别的趣味。如果戏剧不停地奔跑,自己很累,观众也很累,没有达到正常的互动。歌剧的节奏感不仅仅是音乐本身的节奏感,还有戏剧推演和观众心理的节奏感。只有同时把握这两种节奏感,并使之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才会形成创作者和观众都很过瘾、都很嗨的局面。怕就怕自己过瘾了,观众觉得不到位。或者自己觉得冲得很好,而观众觉得太猛了。在某些地方你该停下来,该让大家赏一赏风景,甚至静下来流连一番。
徐文正:这才是歌剧的魅力所在,这点要是抓不住的话就是失败的。这涉及刚才说的节奏问题,咏叹调的出现必须是经过一定积累才会感人,如果一直是抒情唱段的连续,那就会成为“歌儿剧”。
韦 锦:针对目前的歌剧热,我以为,不仅要创作者热、制作者热,还要让观众热。不能只顾自己一头热。除了宣传推广培训普及,主要还是要在戏剧性与音乐性的结合方面多下功夫,要把钱更多地用在编剧、作曲、表演、演奏上,即用在主创、主演上。要让人切实感受到艺术质量,而不是包装质量。契诃夫(或是托尔斯泰)曾说过一个故事,有人看一部戏,回来说太好了,问他怎么好,“服装太漂亮了”。契诃夫说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不是一般的本末倒置,这样夸人的话会惹事的。
王洪波:这就涉及要做一部好的歌剧,有哪些是充分条件,哪些是必要条件。有的根本不是必要条件,我们把它当成了必要条件,有的该是充分条件,我们却做得很不够。在这个过程中,在技术层面,我们首先不能忽略技术,首先得把歌剧的技术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然后再上升到哲学和灵性层面,这自然是在基础层面之上的。这时候,天才的因素就特别重要了。因为你把技术技巧都学会了,不难。但是,是不是具备这种天分,这是很重要的。就像烧开水一样,总是在九十几度,就是达不到100度。
徐文正:对。当音乐与戏剧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观众特别渴望听到高潮性唱段以满足对抒情性的需求。这就涉及对歌剧整体结构的布局问题。
韦 锦:速度、节奏、呼应和对峙,从编剧和作曲阶段就需要进行设计。歌剧既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它应该是跳高和跳远。前面的助跑是为了最后那一跳,而且最后那一跳也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或者要足够远。而且一部歌剧不能只跳一次,要不断刷新纪录,这才引人入胜。反过来说,舞台设计、灯光服装等重要不?重要,一开场就要让人震撼。但是戏剧不像电影,不能经常换景。这个震撼能持续多长时间?所以要吸引观众,还是必须从戏剧本身,从音乐本身下功夫。
王洪波:这个过程是需要的。世界歌剧艺术是个巨大宝库。这个殿堂里面有丰富的东西,琳琅满目,有各种不同样式、不同美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领略它,只是凭偶尔看到一点东西就认定一个模式,这是不可取的。第一步,是对歌剧的历史应该有个整体的把握,这个把握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敬畏感。我们对为歌剧艺术这个宝库、这个领域作出许多贡献的伟大艺术家们要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尊重。你要知道哪里是高峰,哪里是珠穆朗玛,哪里是乞力马扎罗,如果一辈子都不知道哪里是歌剧的奇峰峻岭,却要做自己最棒的歌剧,这是很可笑的。第二步才是融入自己的东西,再丰富发展它。第三步,是自己的创造。当然这个过程中,有的东西不是截然分开的,是可以同步的。但是你必须有这个视野,打开这个视野。今天各地建立起许多大剧院,有许多合乎标准的演出场所,对引进西方歌剧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的观众才有机会在现场看到这么多优秀的歌剧作品。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观众眼界很开阔了,是看过十几部甚至几十部以上歌剧的观众,对于专业工作者就是一个新的挑战。而只有在挑战面前,才有可能出现真正好的歌剧。
徐文正:这个“敬畏感”我觉得太重要了,搞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敬畏感,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歌剧是什么就来写歌剧,那能写出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引进这么多外国歌剧,包括外国导演、外国演员跟中国结合,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观赏高水平歌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创作歌剧、发展歌剧事业提供可借鉴、可学习的东西,不仅是一些具体的制作过程,更重要的是新的、多元的歌剧观念。
王洪波: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打开了你的审美视野,扩展了你的审美经验。我们经常说宇宙人生,有些东西就是从人生到宇宙,从宇宙到人生,这种富有张力的东西会让你很过瘾。就像杜甫的诗《赠卫八处士》,开始就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他把会面之难描写成西南方的参星和东北方的商星碰到一起,这就像电影中的大镜头。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音乐的节奏、色彩、画面感全出来了。春天韭菜是绿的,和黄粱的颜色交相映衬;而一冷一热,冷的夜雨,热腾腾的新炊,这种色彩冷暖的对比如果呈现在舞台上是多么漂亮。这种审美经验会让人觉得特别过瘾、特别美。这种诗句穿越千年,至今让人感动。好的歌剧也是,给你带来的震撼人心的审美经验,会让你觉得特别过瘾。
韦 锦:而接下来的“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其实就相当于歌剧里的咏叹调,叙述、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使整首诗的景深得到极大延展。
徐文正:对,中国艺术家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中国歌剧之路怎么走,应努力学习经典歌剧和各种艺术门类的知识、经验,多方面汲取营养。有人说没必要想那么多,只要写就行了,我觉得不妥。
韦 锦:这就涉及主动写作和被动写作的问题。好多人讲到被动写作就好像天生被拣选,是按照冥冥中的东西而非自觉写作。其实要达到这个状态,此前应该有个主动写作的阶段,就是不断寻求和选择可以走得通的路,找到这条路以后再说被动写作亦不迟。
王洪波:最后我建议聊一下歌剧批评。因为中国歌剧发展到今天,是需要批评的。但是今天歌剧的批评或评论还远没有形成气候。歌剧发展到今天需要有批评在其中起到去粗取精、标示引导的作用,如果缺少这个过程就会走很多弯路。什么是好的歌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歌剧?歌剧批评既是面向歌剧界的,也是面向公众的,要引导业界和公众对什么是好的歌剧形成基本的标准和共识。这方面的综合建构还很缺乏。歌剧一定要打动人心,要有它的质感、个性和风格,它的音乐性、戏剧性、文学性、舞台感,都要有恰当的表现,或细腻丰富,或简洁明快。另外,还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所谓的思想性。好的形式感加上好的思想性,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歌剧还要有其作为歌剧这个艺术品种不可替代的形式特点和艺术魅力。但是,现在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让人很尴尬的情况,就是一部歌剧也花了很多的钱,在形式上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看作品的时候,不能感动你,甚至在价值观上,你觉得它非常的落后,按照现在的小朋友们说,很low。当然歌剧并不长于表现思想,但蕴含于形式之中的价值与思想,不能够引起别人尊重,反而让人很不屑,就会很糟糕。
韦 锦:“批”和“评”必须就作品本身切入,要从剧本到作曲到乐队到演唱,分门别类解剖分析,指出它的优长和不足。而参与歌剧制作的人应该有好的心态,不要总渴望听表扬。表扬的话要听,它会让人知道自己有哪些长处,知道哪些长处已被认可。另外的意思也要听得起,听得懂。表扬你不具备的优点时,你不要只顾着高兴。人家可能不好意思直接指出你的缺点,于是提出一个期望,竖起个标高。你不要盲目得意。
徐文正:我感觉歌剧批评非常需要,但目前好的氛围尚未形成。制作歌剧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作为制作方来说就是希望得到认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要想走得更远就要听取批评,因为许多东西不可能一出来就完美无瑕。
王洪波:这有两个方面,首先被批评者,作为艺术创作者,心态要平和,要宽,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另一个方面,作为批评者也要有个基本的认识,要做善意的批评,要有批评的善意;还有一个就是“比例”原则,这个比例原则很重要。
韦 锦:不仅是歌剧制作,好多方面,人们为何怕批评,实际是担不起随便上纲上线和任意放大的责任。如果说批评者是法官的话,量刑要有尺度,要尽可能客观,是多大的问题就界定多大的责任。这样人们才敢接受批评。现在,一听批评就好像被宣判了,而量刑要么是从严,要么是从宽。尺度伸缩性太大。
徐文正: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性,要精准到位。
韦 锦:就像刚才说的法官问题。法官必须懂法,必须熟悉法律。不能谁都可以是法官。
徐文正:对,评判一部歌剧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歌剧思维”。这是金湘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无论对批评者还是创作者都很适用。另外,批评一部歌剧必须拿它和相应种类的作品去比较评论,而不能拿一个种类的标准来评论另一个种类的歌剧,这是“精准”的问题。
韦 锦:“歌剧思维”,这说法好,它强调的是思维,不仅仅是思维成果。思维工具、思维过程的重要性由此得到突出。歌剧思维的工具是什么,思维过程是什么,这又是一个话题,回头我们找机会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