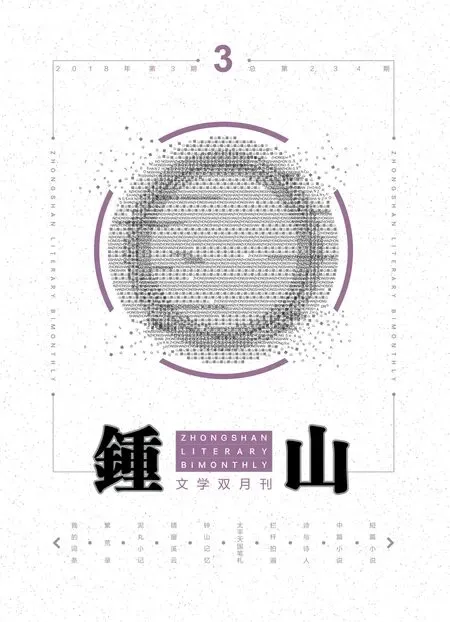虎吼
雷平阳
入冬后,大雪就没有停过,感觉天空里的奶粉厂、盐矿厂和面粉厂,全都打开了仓库的大门,愤怒地向人间倾倒着经济危机时代的积压产品。天空之上的过剩物资,对素来饥寒得高耸着巨石般灰色骨头的乌蒙山来说,足以满足另一种幻象的奶粉、盐和面粉,完全可以在萧瑟的梦境中变成求之不得的实物。人们从用来逃避饥饿的睡眠中翻身爬起,赤着脚,兴冲冲地就跑到了一座座千仞绝壁之上,打开久握的拳头,双掌从空中抓来一把把白雪,狠狠地往自己嘴巴里塞。边塞,边叫,脸上热泪滚滚。
松树镇后山最高的那座山峰,名叫打虎峰。自从这个山中小镇建立以来,每逢世上发生大事,乌蒙山里所有的老虎都会嘴巴上叼着一只羊羔赶到这座山峰上来,聚在一起,吃完鲜嫩的羊羔肉,然后就对着小镇发现轰天炸地的雷霆之吼。吼声经久不息,让小镇上的人如临末日审判,以一家人为单位,彼此攥着对方的头发,死死地抱在一块儿。那些鳏夫和未亡人,无人可抱,就每人抱着石水缸,剧烈地发抖,让水缸里的水泛起阵阵波纹。听见虎吼声,也有人撇下家人,拉开门,箭一样射向距小镇两公里的墓地,跪在某块墓碑下,磕头,哀求,希望在天之灵能伸出一双救人的巨掌,或从天上伸来一把把闪光的金楼梯。由于小镇建在了群山的腹心,四周就有很多溪流顺山而下,在小镇的一个个角落汇聚成池塘。平时,这些池塘明亮如镜,周边长满了青草和人们种植的果树,男人在里面养鱼,女人在里面洗菜或者洗衣服,夏天,孩子们则在里面嬉水。遇上干旱,人们就取池塘的水去救急,甚至可以将池塘的水灌满一个个巨大的塑料桶,用牛车拉了,去无水的山中出售,换一点买盐的钱。总之,它们带给小镇的全是好处,没有坏处。小镇上的人,翻山越岭到世界上去闯荡,变成了显贵或乞丐,谈起故里,鲜有人赞美高山,赞美打虎峰,但言及这一汪汪池塘,人人心里均会顿时涌出无尽的眷恋。然而,这些池塘,在那些经历过虎吼的人心里,一旦想起它们,眼底立马就会浮起一具具浮尸,它们的积水从山上流下来,仿佛承担了另外的使命。据说,当虎吼声传来,小镇上的一些外来人耳朵里就会接收到一道命令:“请你跳进池塘去藏身,快,快点!”虎吼声消失后,这些跳进池塘的人,当他们从池塘下面漂起来,他们已经把自己彻底交付给了池塘,没有一个湿漉漉地爬回到岸上。
下雪的时候,杀人凶手刘庄文就站在打虎峰上。他表情古怪地望着其它山峦上往空中抓雪狂嚼的人,嘴巴上叼着一支香烟,双手上的鲜血还没洗。把烟抽完,吐尽一团团白雾,照理说,刘庆文应该抬起血淋淋的右手,从嘴巴上摘下烟头,用食指将烟头弹向雪花飞舞的空中,接下来再用脚边上的积雪擦洗手上的鲜血。可刘庆文没有这么做,他懒得抬起右手,而是舌头一顶,一口粗气就把烟头吐向了松树镇方向的空中。随后,他蹲了下来,刻意让目光变得柔和一些,带着讥讽的微笑,用右手轻轻地扫着已经僵硬了的张佑太身上的积雪。积雪与鲜血凝结在了一起,他从旁边的雪堆里找出了匕首,用匕首尖将一块块红雪挑起来,再一块一块地赶开。匕首尖挑到张佑太衬衣上的金属纽扣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他干脆手臂微微上抬,手中的匕首垂直向上,轻轻一拉,张佑太的衫衣就被划开了,再用匕首尖左右一挑,衬衣和衬衣上的积雪倒向了身体的两边,淡粉色的胸脯就露了出来,血液还没有彻底凝结的创口也露了出来,奶粉、盐巴、面粉纷纷落在了上面。此刻,刘庆文也才收回脸上的表情,双手和双腿张开,茫然地向后倒向雪地,身体即将触地的一瞬,右手向内一收,把匕首深深插入自己的心脏,然后又迅速拔出,扔在了雪地上。他的身体与张佑太组成了一个天字形。
这一场大雪下到了腊月初才停住。天空也空了,再没有多余的素材可供乌蒙山里的人们培育想象力。人们肚腹里装满积雪,似乎也不想继续跑到绝壁上去手舞足蹈,特别是当这些积雪让他们领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冰冷的时候,他们反而开始向往头顶上那高悬着艳阳的天空,希望这梦境里的食物尽快排出体外,代之某种能够满足新一轮幻觉的崭新填充物。新一轮的幻觉大抵也是古老的幻觉,不会有什么新花样,无非仍然是布匹、火焰、食品和麻药等等俗常之物的影子,可那“崭新的填充物”属于未知,人们真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好吧,既然不知道,并且不知道什么稀罕物才能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那就不用挖空心思去乱想象了。人们因此进入了新一轮的梦境中,用新生的没有杂质的逃避之法,应对着时光的流逝和意念的反复涅 。能活命于意念中的人真是有福了,一个崇拜老虎的人,某天中午进入了松树镇,当他看到镇上关门闭户,人人都绻缩在被窝里等待内心的冰雪融化,忍不住大加赞叹,把松树镇的寂静归类为墓地的寂静。他说的墓地,是新修的无边无际的却又没有死者入主的墓地:“世界如此喧闹,只有松树镇是寂静的,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拜虎人其实没有夸夸其谈,也没有故意煽情,松树镇确实非常的反常,小街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更不可能有人交头接耳,谈论着打虎峰上的凶杀案。整个冬月,人们都足不出户,谁也不可能去攀登打虎峰,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知道打虎峰上的积雪下面卧着两具尸体。所以,当这个以老虎为图腾的人,跌跌撞撞,下了打虎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边跑边喊“杀人喽,杀人喽”的时候,小镇上的人们才知道老虎怒吼的山顶上,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杀了,杀人的人又把自己杀了。第二天,有关机构的人在出过现场后,组织群众把两具尸体抬下山来,分别交还给他们的亲属,人们才纷纷移动自己冷飕飕的身体,走到街头,或摇摇头叹一口气,或外表麻木不仁五内则生出些奇思乱想,或从衣袋里掏出手机,把刘庆文和张佑太的手机号码删除了。“我以为打虎峰上,肯定有老虎的魂魄在游荡,难说还会有老虎血染红的石壁,没想到气喘吁吁地爬上去,上面竟然……”崇拜老虎的人,逢人就高声喧哗,一副非将小镇从寂静中拖出来的架势。人们普遍都不迎合他,相反把他当成一个报送死讯的人,觉得他的身上夹杂着地狱的湿气。刘奇文的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松树镇上出了名的猎人,虎豹出没的那些年,出任过“乌蒙山猎虎总队”下属的一个分队长,伏虎、猎豹、杀狼,风头无二,家里的虎骨酒摆满了宽大的供桌,听说现在的床底下都还存放着一罐子。这个人在耳朵边上大声嚷嚷的次数多了,终于在葬礼上猛然绷直驼背了的腰身,用混浊又不失凌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你有着一副老虎一样的嗓门,上了打虎峰,为什么在上面时不对着松树镇大吼几声?”只字不提带来死讯的事儿,无意撂下眉毛底下一个凶手父亲所承担着的精神压力,但又巧妙地以挖苦人的方式把人们关注的话题分了个岔儿出来,同时,也是最有意味的,这个猎虎队的分队长,表面上虚晃一枪,实际上十分隐蔽地就把那个大声嚷嚷的人引上了一条重登打虎峰的小路。穿插着参加完两个同时举行的葬礼,回到只有他一个人住宿的春山旅社,崇拜老虎的人回想起猎虎队分队长的话,总觉得这话里分明在暗黑的夜幕中给自己递过来了一道闪电,闪电的光瞬息即逝,但又是真实存在的,闪现在某条登山之路的尽头。是啊,那天去登打虎峰,如果上面不是一个凶杀案现场,自己会不会像老虎那样吼上一嗓子呢?一旦吼了,又会怎样呢?他越想越是觉得这个气氛诡异的松树镇,它不但有意抽走了某些惊心动魄的客观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黑夜,而且它还将幻象与现实世界搅和在了一起,并且明显地把真相推向了幻象的一边。
在同一天,两场葬礼同时举行。一支送葬的队伍往小街的北面缓缓移动,另一支则往南移动。小镇上的人们坚持了他们古老的习俗,没有空中翻飞的纸幡和纸钱,也没有鞭炮和香炷开辟死者的超生之路,在众花寂灭的腊月,他们几乎砍光了山坡上刚刚引种不久的冬樱花树,一人扛着一棵,把整条小街装扮得极其凄美、妖娆。“持美而夭,何其绝美!失我心骨,何其空茫……”低沉而灿烂的送丧歌,也似镶了金边的乌云浮动在只有几米高的空中。见识到这样的场景,那个崇拜老虎的人一再对自己说,这是多么的务虚啊,几次想扔下分发给他扛着地那棵冬樱花,让自己以外来人的身份呼天抢地的为两个年轻人痛哭一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里仿佛响起了一个声音:“请你安静一点,这冬樱花的海洋里最适合你藏身!”声音与虎吼时诱引外来人朝着池塘里跳的声音是一样的,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服从了,关上了自己令人讨厌的大嗓门。神秘的声音让他闭上了嘴巴,接下来胡吃海喝的丧宴带给他的印象一度又让他差点失控,幸好他早早地回了旅社。多么匪夷所思,落雪时,人们还爬上一座座山峦和绝壁去抓飞雪果腹,这时候,人们几乎杀光了小镇上所有的畜牲和家禽,几百张餐桌上肉食堆积如山,满眼全是张开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齿,嚼肉啃骨的声音就像有一群恶虎在撕吃爪下的羊羔……是的,两席丧宴把人们从幻觉中抓了出来,肉食和酒水终于成为了人们梦境之外滋养身体的“崭新填充物”,人们眼底的鬼影子消失了,那腹中的冷雪,一碗烈酒下去,马上就融化了,变成一泡热尿,哗哗哗地就冲出了体外。什么末日审判,人们沉浸在了末日的狂欢之中,直到自己找不到自己或一再把横卧在街边的别人当成自己为止。当然,也有两个人什么肉也吃不下去,一口酒没喝,他们分头离开了两个不同的丧宴,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一个池塘边。他们不是别人,两位死者的父亲。“知道吧,这池塘里死过很多人?”开口的是张佑太的父亲。猎虎队分队长没搭腔,递给对方一支纸烟,两人都点了火,坐到女人们用来洗衣服用的两个石墩子上,一声不吭地抽了起来。抽完了,又续上,冷冷的目光下,两个人的头上就像罩上了一团灰雾。其间有几个醉汉腾云驾雾地从身边飘过,见了他们,也总是把他们视为石墩子。“你说,这两条狗命怎么就这么没了?”沉默了两个时辰左右,也不知这话是谁说的,也没有另外的声音附合。随后,他们的对话像喷火艺人嘴巴里喷出的火焰,同样也分辨不出哪一束火焰是谁喷出来的。
“今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两个孩子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把我们之间的血仇告诉了孩子!”
“血仇?什么血仇?我们之间什么时候结下了让儿孙以死相殉的血仇?”
“请你不要装糊涂好不好。那一天,我们十多个猎虎队员,一人披一件虎皮进山猎虎。说好了的,大家分别埋伏在不同的地方,等着几只老虎从打虎峰上下来,我的哥哥,他就躲在两棵松树之间,根本不在老虎行走的小路上,结果,老虎还没来,你就开枪了,一枪就要了他的命!”
“不,我没有,绝对没有,你这是诬陷。那天晚上,月光那么亮,我肯定不会把人看成老虎。而且,那晚上,我一枪未放,老虎听见枪声,根本没从打虎峰上跑下来!”
“你还要抵赖?”
“我没有抵赖。我只听见有人放枪了,接着就听见了一阵乱枪。是的,你的哥哥就被打死了。”
“我知道你和我哥哥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你是借机除掉他!”
“你放屁,我他妈哪个女人也不喜欢,你哥哥喜欢谁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他的命?凭什么?噢,照你这么说,后来的一天,同样是进山猎虎,我弟弟也是被一枪毙命的,那开枪的人原来是你,是你在报仇啊!”
“不,我只杀虎,从来没杀过人。尽管我知道你杀死了我哥哥,我有一百次机会杀了你,我都没开枪。我为什么要杀你的弟弟?”
“你别装了,你不杀人,我难道没看见过你杀人?每个人都披着虎皮,我就亲眼看见你把一个埋伏在溪水边的人当成老虎,一枪就打倒在了溪水里。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唉,你真是血口喷人,猎虎队十多号人,老虎打杀完了,人就剩下咱两个,除了有五个被老虎撕吃了,有四个摔死了,其他全是误杀而死,我一个也没杀过,是的,没有。”
“照你的说法,全是我杀的了?”
“你杀过,死去的人里也有人活着时杀过,然后被杀。”
“我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杀过人,听好了,我从来没杀过!”
“哈哈,有哪个杀人的人承认自己杀过人?现在我终于见到了一个。这个人就是你!你不仅杀人,你儿子也杀人!”
“什么?我儿子杀人?你妈的,我真想杀了你,这一分钟,我真他妈想杀了你。我儿子分明是你儿子杀的,你把血水往我头上泼倒也罢了,现在你又来往我儿子头上泼!”
“哦,这个你也不承认?我儿子从来没有过匕首,匕首肯定你儿子的,他用它杀了我儿子。”
“你儿子会没有匕首,我相信你儿子生下来,口里就含着一把匕首。请你不要再洗白自己和自己的混蛋儿子了!”
因为有月光,池塘里倒映着打虎峰淡淡的倒影,说到猎虎行动和打虎峰,两个黑影还会伸出手指,对着池塘指指点点。那些秘而不宣的往事,仿佛已被他们联手沉入了池塘。事实上也是,两个黑影没完没了地互喷火焰,谁也没把谁烧焦,不仅没有动手,彼此还互递香烟,相互有着忌惮与默契。他们一直在说,说到黎明降临,揭发,否认,再揭发,再否认,说的都是对方的手上沾满了鲜血,而自己是清白的,罪恶没有可靠的证据,清白也没有可靠的证据。对于刘庆文和张佑太两个孩子的恶性死恨事件,他们都力图找出原因,“血仇”被找出来了,但血仇也是无人认领的,无非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为隐秘的一个话题,永远不可能向上小镇上的人公开。你不能说他们都彻底忘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身份,没有了老年丧子者的剧悲,说到他们第一眼看到儿子尸体那一刻的景象,其中一个人还捡了一块石头,恶狠狠地砸向了池塘里的打虎峰,另一个人则往自己脸上重重地击了一拳头。他们的悲与疼被他们藏起来了,不对,应该说他们的悲与疼,因为害怕别人从两个孩子的死亡事件中发现什么,他们就有意地回避开了。同时,当他们将两个孩子的命称之为“狗命”,又说明他们又恢复了自己猎虎队队员的身份,拥有着猎虎时代“猎虎英雄”和“两个光荣的幸存者”光焰之下那颗战士的心。作为父亲时,他们不相信儿子会以自己的死亡去了结“血仇”,其中必然另有隐情,可他们却又害怕深入的调查,毕竟他们经受不了调查。所以,当办案机构以杀人和自杀为结论草草结案,他们没提半点异议。可是,作为猎虎队队员,对于儿子以命了结“血仇”之说,他们是乐于接受的,了了,一了百了,这了可以彻底地埋藏所谓血仇,可以无奈地用“狗命”去抵冲部分血债。他们不是猎虎时代血雨腥风的掀起人,但他们是马头卒,以前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裹挟,现在因为拒绝觉醒而害怕审判。两个儿子的死,按说给了他们接受审判的机会,他们放弃了,反而用儿子的尸体去压住了打虎峰山顶的风雪。
葬礼之后,每天都有烈日,松树镇四周山上的积雪纷纷融化,流下来的雪水把每个池塘都填得满满的。开始的一两天,胃里面积压着从丧宴上获取的过量的肉食与酒水,人们又重归于梦境,人人都不想放下肩上扛着的那一棵冬樱花,还想继续行走在送葬者的队列这中。“持美而夭,何其绝义!失我心骨,何其空茫……”那个崇拜老虎的人从空荡荡的小街上走过,听见每扇窗户里都会传出梦呓般的歌吟。可当胃囊逐渐空掉后,渐渐才有人走出家门,提着竹篮子,准备到山上去寻找积雪。不曾想到,当他们来到小街上,还未走到山脚,就发现小镇上的池塘在阳光照射下,那铺天盖地的白色反光,已经令人头晕目眩。猎虎队分队长和那个崇拜老虎的人正在小街上跑来跑去,拍门打户的召集人们,号召大家人人动手,尽快把褐色的稻草和麦杆子撒到池塘里去,或者用大棚温室上一张张巨大的黑色塑料薄膜把池塘包扎起来。张佑太的父亲神色憔悴,一看就是几夜没有合过眼了,显然也是最早发现白光之灾的人之一。他已经把家族里梦游之中的十多个青年男女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下设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负责把两个葬礼上用过的冬樱花从墓地上运回来,扔到池塘里去;第二个小组负责把小镇上的黑煤集中在一起,倒进池塘,把水搅黑;第三个小组的工作比较难做,他们得动员小镇上的人们把黑色的衣物捐献出来,用铁线或者竹竿串成平躺的人样,然后铺架到池塘上面去。小镇从来就不缺少悲剧性,大家都穿黑衣服,可衣物毕竟有限,捐出去了,人人就得天天赤身裸体地躺在被窝里,发生了什么急事可就出不了门了,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但后患也很多,不愿捐献。张佑太的父亲见其它两个小组的工作搞得如火如荼,就是这个组难以破局,步履蹒跚地前来督阵。风雨见得多,乱象经历不少,解决难题的经验也很丰富,他稍作民意调查,立马就拍板:每一户人家,男式和女式分别留一套衣服作为急用,其它全部捐献。于是乎,很多的池塘上,迅速布满了黑色的人影。捐献了衣服的人们,乖乖地回家做梦去了,小街上,最后只剩下用黑色塑料薄膜严严实实地套住的三个人。他们一个池塘接一个池塘地去检查,担心有人疏忽了,某个池塘露出清澈的水面。三个人中,一个声音说,只要有水面露出,太阳的光就会肆无忌惮地集中到这片水面上来,水面的反光不仅会让白日梦里的小镇持续升温,将人们导入神秘无解的白色空间,继而呕吐、癫狂、迷乱,甚至燃烧。 同时,那座倒映在池塘里的打虎峰则会随之陷落为深渊,既有幽灵般的呼唤声从下面传上来,还会产生一种阴森森的巨大吸力,让人不可遏制地就往池塘里跃去……听声音,说话的是张佑太的父亲,但没等他说完,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这个声音明显是猎虎队分队长的,他说,听好了,你这个崇拜老虎的人,关键是,那太阳与水的反光一旦出现,特别是当小镇上的每一个池塘都有反光,这些反光将统一照射到打虎峰上,它们就像地狱之光那样,一眨眼就点燃了峰顶上那一座座红色绝壁,使之就像连绵千里的乌蒙山向天空升起的反叛的、不祥的巨大火焰。也正是因为这火焰,那些嗜血的老虎才朝着这儿云集,它们都以为,沿着火焰向上攀,它们就可以进入天空,成为天空的组成部分。然而,当它们来到打虎峰上,发现一切均是阳光与水面制造的幻象,哦,对了,这个你肯定是知道的,它们认为自己受骗了,幻灭之后,便对着水面上反射而来的白光,也就是松树镇的方向,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怒吼。那声音真的能满足人们对死亡的想象与恐惧,仿佛天上的魔鬼全都发怒了,想用自己的声音毁灭小小的松树镇。
太阳的光被人们阻止在了池塘之外,第二天,太阳就到其它地方去了,松树镇的上空先是来了几朵乌云,随后,雨就下了起来。猎虎队分队长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想事,旁边的老伴一再催他,说下雨了,太阳跑了,得去池塘里捞几件衣服回来,否则怎么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啊。他没有理会老伴,而老伴见他不动,只好穿上仅有的一套衣服,出了门。屋子里好静,像那个该死的崇拜老虎的外乡人所说,是墓地上才有的寂静。嗯,墓地,的确是墓地,闭上眼睛,就能感觉到屋子的地面、家具、墙壁、天花板、自己躺着的床铺,乃至自己身体的每个部位,每根骨头上,都有青草在嗖嗖嗖地冒出来,嗖嗖嗖地朝上疯长,嗖嗖嗖的长出了屋顶,而这屋子的正中央,分明摆着他和儿子的两具骷髅。不止一次,他看见儿子胸口上咕咕咕地冒着热血,站在床面前,脸上有新鲜的尘土,表情似笑非笑但明显的带着一股寒气。儿子满手的血也还没有洗掉,沾上了泥巴和草屑,衣服的皱褶和发丛中,白雪凝结成了深灰色的冰渣。第一次见到儿子,是葬礼后第二天中午,他躺在床上,想撑起身子去抱儿子却怎么也撑不起来,儿子似乎也不稀罕他的拥抱,冷冷地站着:“爸爸,是你教会了我杀虎的技艺,我一直想试一试。下雪那天,我去了打虎峰,奇迹般地遇上了同样去杀虎的张佑太。唉,在我看见了一头老虎时,抽出匕首,猛然扑击过去的时候,老虎金色的皮毛突然不见了,它竟然变成了张佑太。而当我以为自己杀了人的时候,张佑太又变成了一只死老虎,他们不停地变来变去,我一点儿也分不清,自己杀掉的是老虎还是张佑太。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也在不停地变,一会儿是老虎,一会儿是我,我仰面朝天,向腾空而来的老虎送出匕首,匕首却插进了自己的心脏……”儿子陈述的事件不乏惊悚,可口气始终冰冷,一字一句均斩钉截铁,话音未散,人就不见了,没有给他一分钟的提问时间。之后又与儿子见面,儿子一句话也没有,他问什么,儿子立马就消失。儿子说的杀虎场景,有那么几次,他都想与张佑太的父亲作个交流,特别是太阳之光刺激池塘的那天,他们都同时嗅出了松树镇空气中飘荡着一丝血腥味,甚至隐隐觉得乌蒙山中的老虎并没有赶尽杀绝,经过多年的繁衍,老虎早已成群结队,正在翘首观望,只等打虎峰上升起火焰的大旗。儿子的说法,契合了天象,与他们当年杀虎的景象也是一致的,而且他感到,儿子这一代人显得更绝决,绝决到了连给自己也不留生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有必要与张佑太的父亲说说。但那天事情多,又很紧急,猎虎队分队长也就打消了交流的念头。之后,见张佑太的父亲也不想在儿子之死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连惯常的经济补偿之类的话题都没提,他就把交流的念头摁灭了。再说,像松树镇这种依靠幻觉而存在的鬼地方,新一代人愈发依赖幻觉,这样的报应也无可厚非。如果哪一天打虎峰又聚满了老虎,相信人们也会焕发出嗜血的本能,无所顾忌的与之同归于尽。
那个崇拜老虎的人不久也就离开了松树镇。走之前的头一天,他约了猎虎队分队长和张佑太的父亲一起登上了打虎峰。三个人坐在峰顶上,看着四面的群山和天上的云朵犹如虎群奔突,人人心里都涌入了一只接一只的老虎,人人都又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只有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松树镇时,张佑太的父亲才对崇拜老虎的人说了一句:“是你把死讯从这儿带给了我们。”崇拜老虎的人不在意他把自己当成死神的邮差,笑了笑,掉过头对着猎虎队分队长说:“你暗示过我要重登打虎峰,后来我也来过几次,并没有找到虎吼的秘密,而你们说的那些,我是不会信以为真的。”说完,他就模仿老虎的吼声,对着松树镇大声的吼叫起来,他的嗓门再大,声音也像全力扔出去的一串点燃的鞭炮,转眼就爆炸光了,不可能传到松树镇的上空。待这人吼完了,猎虎队分队长拍了拍他的肩头,将脸转向张佑太的父亲:“你听,他这也叫吼?当年猎虎大队几百号人经常在此学习、训练、开批斗会,没事了,一人一个高声喇叭,就对着松树镇一阵接一阵的喊口号或者作虎吼,吓得镇上的人们天天都疑神疑鬼、失魂落魄……”他一说完,两个猎虎队员都笑了起来,笑声里夹杂着一丝丝虎吼的音质。那个崇拜老虎的人,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才知道了老虎是怎么吼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