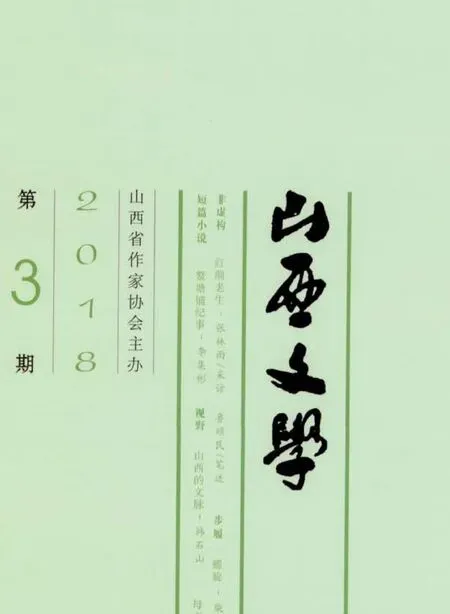心理暗示
(美)凯特·肖邦 / 著 荆素蓉 / 译
1
“当你今早见到波琳,她会很迷人,她会是房间里最漂亮的女人,也会是唯一值得你关注和考虑的人。”
这是唐·格雷厄姆施加在朋友费沃汉姆身上的心理暗示,当时他们俩一早起来正一块儿洗漱。格雷厄姆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个工作上进、痴迷于心理学研究的年轻人。他曾参加过催眠降神会,由此掌握了催眠术,水平可不一般,他时不时施展一下,总是颇为成功,尤其是用在朋友费沃汉姆身上可谓屡试不爽。比如,费沃汉姆早上起床后发现自己的黑外套上有一片醒目的猩红印子,他没有抱怨,也没有纠结要不要穿上这么一件惹眼的外套出现在众人面前,而是径直走到电话机前给格雷厄姆打电话:“喂!——你个欠骂的白痴!别再耍弄我的外套了!”有时通话内容是这样的:“喂!我早上又没能洗完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或是“我的咖啡又被弄坏了!岂有此理!希望这种事儿到此为止!”电话那头的一小群教授们由此感到心满意足,而这份喜悦是很难为从未体会过科学实验成功的人们所理解的。
费沃汉姆工作不算上进,凭着万贯家资和迷人魅力,他出手阔绰,尽显风流,无论男女都对他喜爱有加。他一直有一个似可原谅的缺点:他坚决避开一切使他厌烦的人物、地方和事情。而世上让他厌烦透顶的人之一就是其友格雷厄姆的未婚妻波琳。她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头发蓬松,戴着眼镜,在探究心理问题方面有着刨根问底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她自称喜爱艺术,却抱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去探究,并依靠开列数学图表来学习掌握。她是费沃汉姆厌恶的那种女人。她的镇定自若对费沃汉姆而言是一种反驳;她缺乏风情,不够迷人,没有女人味,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费沃汉姆认为波琳和格雷厄姆是天生一对,但也总不由得为他的朋友感到悲哀。因此,费沃汉姆总是回避着波琳,并且在他礼貌的本能所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冷落她。
他和格雷厄姆南下去了松枝,很多可爱风趣的人都打算在那儿度过十月。在十月的那个周一早上,格雷厄姆要返回城里赴约,而费沃汉姆则打算待到尽兴再离开。松枝有很多活泼可爱、志趣相投的女孩,多少能助其玩兴。那里的垂钓、泡澡和驾车的项目也都不错。
格雷厄姆站在镜子前系领结时,突然意识到他不在的两周里,他的小波琳一定会很无聊,这个想法让他不安起来。除了那位收集蝴蝶然后用大头针串起来订住的德国女士,就再没有一个志趣相投的人能陪着她了。他又想到驾车、航海、跳舞这些费沃汉姆热衷擅长的活动,若能诱得波琳参加,说不定能让她从费沃汉姆漠不关心的对象变成一个妩媚迷人的年轻女人。找了个借口,他走过去把一只手搭在了正系鞋带的费沃汉姆身上。“当你今早见到波琳,她会很迷人,她会是房间里最漂亮的女人,也会是唯一值得你关注和考虑的人。”
当格雷厄姆和费沃汉姆走进餐厅时,那里已经聚了好些人。有的已经就座,有的则三三两两地站着闲聊。波琳正在窗边全神贯注地读一封信,她心不在焉地匆忙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后就又接着与友人交流信的内容。信是一位艺术品经销商写来的,通篇都是关于他为波琳找到的一幅早期弗拉芒画派的代表作品。波琳正在以她惯有的严谨缜密的作风收集不同流派与不同时期画作的仿制品。她想方设法努力寻找的这幅早期弗拉芒画派的作品找到了,这让她终于安下心来。格雷厄姆坐在她旁边,他们头挨着头,一边吃着燕麦,一边聊着有关心理学和艺术的话题。费沃汉姆坐在他们对面,他不停地朝波琳看。他和旁边的网球女郎交谈着,但却在留意听着波琳的话。
“埃德蒙小姐,”他突然开口说道,他身体前倾以引起她的注意,“等我们回到城里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让格雷厄姆带你去我的公寓看看。我有几件去年夏天在苏格兰淘来的格拉斯哥学派的藏品,有一小块儿色泽柔和像是霍内尔作品的波斯挂毯。或许你会想看看它们。”波琳满脸通红,颇为惊喜。网球女郎见状往椅背上一靠,瞪着费沃汉姆。坐在桌子紧那头的高尔夫女郎则冲他扔了一块面包。格雷厄姆面带微笑,内心乐开了花,脑子里则做了些记录。
接下来在整个用餐过程中,费沃汉姆一直都隔着桌子兴致勃勃地和波琳交谈,同时心里也一直在想:“那柔和的棕色多么适合她的肤色和眼睛啊!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是多么甜美啊!那么深邃!那么灵动!还有什么能比她那自然大方的举止更吸引人呢?她是多么聪慧啊!哎呀!我必须得尽力而为才能配得上她。”格雷厄姆完全有理由祝贺自己试验成功。
然而,一离开餐桌他便吃惊地看到费沃汉姆陪着网球女郎信步走远,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想要继续了解波琳的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儿?”格雷厄姆思索着。“啊哈!明白了!我暗示他只是在吃早餐见到波琳时会觉得她妩媚动人。我得更改一下这个暗示的限制条件。”当他提着旅行包和随身物品离开的时候,波琳陪着他朝着大门走去。他们沿着满是落叶的石子路漫步,一路上格雷厄姆都沉默无语,很是奇怪。波琳疑惑地抬头望着他。
“亲爱的,我希望,”他终于开口说道:“你得让自己的思想听从我的指挥,将你所有的心理能量都投射进我的心理能量之中,让它跟随着我的暗示并避免其偏离方向。”若是高尔夫女郎听了这番话或许会怀疑说话的人脑子出了问题,但波琳不会,她已经习惯了他这样做。当他转身去和旁边的费沃汉姆握手时,波琳竭力让自己的思维变成一片空白并使其服从他的意志。而格雷厄姆在握住费沃汉姆的手时,心理暗示也随即成型,内容大致如下:
“波琳迷人、聪明、老实、真诚。她性格深沉,值得了解。”随后他和波琳一同静静地走到门口,在那里默默地握手而别。
格雷厄姆一边沿路走着一边回头望去。波琳已经转身,正要进屋。而费沃汉姆已经撇下那群网球女郎,正穿过草坪去找波琳。格雷厄姆又在脑子里做了记录,并在想象中拍了拍自己的后背以示赞赏。
2
几天后,波琳给格雷厄姆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她这样写道:
“我还没有开始写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记录,本应该现在就写完的!我真该挨骂,不过希望你能饶了我。事实是我变得很懒散,也很为现在的自己感到羞耻。你肯定是让你朋友费沃汉姆先生多加关照我了。你是害怕我会感到无聊吗?亲爱的,你的好心可真是放错地方了,因为他让我浪费了好多时间。今天早上我本要开始写那些冗长的记录,他却想在那棵大枫树下朗读丁尼生的诗给我听!我说服他换成了勃朗宁的诗。我必须得从这支离破碎的时间里挽回点什么!他读起诗来很令人愉快,声音不仅仅是好听,而且还醇厚柔和充满智慧。他惊叹于我们亲爱的勃朗宁的诗歌里传达的美感、洞见和哲思。‘你难道没读过勃朗宁的作品?’我有些惊奇地问他。‘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坦白地承认,‘你会带我开始一场发现之旅,让我结识这些不朽的英才,对吗?’好了,不说他了——如果你还没见过丁托列托画笔下的利林塔尔小城……”
没过多久,她又写信道:
“我现在越来越不务正业了。昨晚我跳舞了!你不知道我会跳舞吧?噢!但我会。两年前我们的‘礼仪习俗’课上讲舞蹈历史的时候,我学了一些漂亮的舞步。”
一周后,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相信通过非理智的途径传达给一个人的快乐情绪。一两天前的一个晚上给我留下了一种奇怪的印象。就十月的天气而言,那天晚上很暖和,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上。费沃汉姆先生带我出海,斗胆决定在海上多停留一会儿,比平时稍晚一点再返航。天色已晚夜也很静。除了船驶过水面浪花轻拍船帮的声音和船帆偶尔发出的拍打声,四周一片寂静。海风不时吹送过来岸上松杉的香味,浓郁扑鼻。我不知怎么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另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在那之前构成我生活内容的一切都似乎变得遥不可及,虚无缥缈。所有的想法、抱负和能量都离我而去。我想永远待在那片海水上,一直漂流下去,无所顾虑。我承认,整个经历是感性的,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两周快结束的时候,格雷厄姆收到了一张内容奇怪、杂乱无章的小便条,在他看来这个便条不知所云,完全不是波琳的风格:
“你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我需要你来帮我解读一下我自己,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我害怕生命中有些力量是我接受的智力训练无法与之抗衡的。为什么我们会受情感的摆布?如果我们从书里找不到任何武器来面对和对抗无疑实际的微妙存在,那书还有什么用?哦,亲爱的!亲爱的!回来帮我解答所有这些疑问吧!”格雷厄姆感到困惑不安起来。
3
他回到了松枝,一心想要夺回己有。他对实验的成功十分满意,本来这个实验就是他为波琳安排的一段消遣时光,因为他相信她定会从中受益。但现在格雷厄姆一门心思想要撤除施加在费沃汉姆身上的心理暗示,然后让一切恢复如常。
如果他对波琳的爱是盲目、炽热、苛求的,或许他就会这么做了,哪怕是情况改变之后面临重重困难。
“这也许是一时的痴迷,”她可怜地坦承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如果你希望——如果你认为最好最明智的选择是让我遵守诺言,你明白我会欣然履诺。但是事已如此,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整个性情似乎都变了。我——我有时——噢!我爱他!”说到动情之处,她没有像大多数女孩那样捂住了脸,而是直视前方。他们正坐在那棵大枫树下,正是在那里费沃汉姆曾给她朗诵过勃朗宁的诗。天色开始暗下来了。她的脸上却闪耀着一种他不曾见过的光辉,一种他从未能燃起过的光辉,它的源头藏在她的灵魂深处,那里他从未企及过。
他抓住她的小手,静静地抚摸着。他自己的双手却冰冷潮湿。他开口说了下面一番话:
“你是完全自由的,亲爱的,完全不用对我有任何承诺。别烦心,一点也别在意。”
他本可以说更多,但于他似乎没有意义了。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放下诸多过往:几许希望、若干谋划、历历情景、千般想法,他整个身心都在承受着分离的痛苦。
她什么也没说。爱情是自私的。她正体味着自由的欢欣,不想再拿那些老套的话语来安慰一个受伤的灵魂。
有好几个疑问困扰着格雷厄姆。他的暗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会如何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费沃汉姆仍处在暗示的影响之下,这一点他回来一见到费沃汉姆立刻觉察到了。但心理暗示的影响似乎已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想到已经产生的那些后果,他就不寒而栗。但目前没有什么办法在他看来是可行的,只能静观其变。除了拖延下去让试验顺其自然地完成,他也无计可施。那天晚上,费沃汉姆对他说:
“老兄,我明天一早就离开了。你要明白我是你的好朋友。我耻于解释,请宽恕我吧。希望下次我们在城里见面的时候我已振作起来,能够理解我何以能做出如此违背精神或道德的事情——或者——或者——该死,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明天早上我也会离开,”格雷厄姆回应道。“我不妨告诉你,人常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必须得同心同德,但我和波琳发觉彼此已不再同心同德了。要是你不介意,明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回城。”
4
几个月后,费沃汉姆和波琳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似乎标志着困扰格雷厄姆并让他煎熬度日的某种复杂疑问到达了顶点。“如果,如果,如果!”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当他工作的时候如此,当他散步、休息、读书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如此。
他记得费沃汉姆过去对这个女人是如何地厌恶。他意识到,这种厌恶已经被一种力量所驱散,而这种力量的局限性目前尚未可知,它的潜力他自己也全然无知,而它的微妙也超出他的能力可控范围。“这个心理暗示还能维持多久?”这个疑问折磨着他。万一哪天早上费沃汉姆醒来又开始厌恶他身边的这个女人怎么办!?万一他的迷恋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退,最后抛下她如残花败柳般瑟瑟发抖终日痛苦直至生命终结又该怎么办!?
在他们婚后的头几个月里,格雷厄姆常常去拜访他们。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理想的一对儿;这一次,人们说对了。无意识的冲动彼此磨炼、相互作用,最终将这两个人塑造成诗人梦想的完美“一体”。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格雷厄姆会暗中观察他们,偷偷摸摸地紧盯着,如果他俩不是那么只专注于对方,或许早已察觉进而讨厌他的做法。他离开的时候,总是暂时松一口气,庆幸点燃的导火索还没碰到地窖里的炸药。但这种悬而不决带来的折磨让他几乎无法忍受,曾经有一两次他去拜访他们时一心想着要撤销心理暗示,看看会发生什么,并弄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但是一看到他们心满意足、彼此体贴爱护,他的决心动摇了,看看他们就又离开了,怀疑和强烈的不安依旧折磨着他。
一天,格雷厄姆终于说服了自己。整日的忧心焦虑已使他忍无可忍。他决定在那天夜里撤除六个月前加在费沃汉姆身上的暗示。要是他发现这样行得通,那意味着如果他认为恢复心理暗示是最好的选择的话,那他也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如果费沃汉姆最终会醒悟过来,那何不让这个醒悟现在就来,立刻,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趁着波琳还没有用情至深之前,而他或许也依旧可以利用旧日的影响来慰藉波琳的智力与想象,即便不能慰藉她的心。那天晚上,格雷厄姆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波琳已经变了。他们围坐在桌边,他不时地看着她,无法描述那种明显的变化。她现在是一个漂亮女人。她的脸肤色红润,轮廓柔和,配着精心打理过的棕色头发,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夹鼻眼镜代替了那副古板的带框眼镜,尽管让她的脸上少了几分学生气,但却平添了一种极具魅力的韵致。丈夫足够有钱,她的衣服也是昂贵的,色泽十分柔和,说不出的和谐,使她和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
格雷厄姆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融入了这个小家庭,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他当然要对这种地位负责。那晚,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老族长要宰杀科学祭坛上的一个珍宝——一个贪婪的不可抗力的牺牲品。
格雷厄姆没有在愉快的用餐时刻而是在饭后晚一些的时候才再度发力。那种力量他曾同费沃汉姆开玩笑时用过,而那种力量就像某种不知名的毒物已经蜇伤了费沃汉姆。
他们昏昏欲睡地坐在壁炉旁,木柴已烧完,余烬泛着光,忽明忽暗。费沃汉姆借着一盏台灯的光朗读着优美的诗歌,诗行之美宛如膏脂融入了他们的灵魂,没有让他们有感而发展开讨论,而是让他们放松下来陷入了沉思。费沃汉姆凝视着炉火余烬的微光,耷拉的那只手里还拿着书。阵阵雨水拍打在窗玻璃上。格雷厄姆陷坐在松软的扶手椅中,盯着费沃汉姆。波琳起身在公寓里来回踱起步来,一会儿明处一会儿暗处,她的外衣随着她的走动发出阵阵柔和悦耳的窸窣之声。格雷厄姆觉得时机到了。
他起身走到台灯那儿,点燃了从兜儿里掏出的雪茄。他站在桌旁,貌似无心地把一只手搭在了费沃汉姆的肩上。
“波琳还是六个月前的那个女人。她没有魅力,也毫不迷人。”他默默地暗示着。“波琳并非六个月前初次去松枝的那个女人。”格雷厄姆在台灯旁点燃了雪茄,然后又坐回到了阴影里的那把椅子上。
费沃汉姆打了个寒战,仿佛一股冷气袭遍全身,他把躺椅往炉火跟前挪了挪。当波琳漫步经过时,他扭头看了看妻子,然后又盯着炉火,旋即又不安地回头看着妻子,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格雷厄姆目不转睛地盯着费沃汉姆,默默地重复着心理暗示。
突然,费沃汉姆猛地起身,书掉到地上都没注意。他急促地奔向妻子,旁若无人地将她拥入怀中,他紧紧抱着她,狂热且近乎粗鲁地吻着那羞红而受惊的脸蛋,一遍又一遍,如饥似渴。当他最终将她从自己热切的怀抱里松开时,她大口喘着气,脸色绯红,满是困惑与愠怒。
她转身走开,把脸掩藏在了一个椅垫里。“波琳,波琳!”他哀求道,“原谅我吧!”“别担心,亲爱的。格雷厄姆知道我有多爱你。”他转身朝炉火走去。他激动不安,一只手在额头上毫无意义地乱抓着。
“我真不清楚自己何时做出了这样的混账事,”他抱歉地低声对格雷厄姆说道。“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不得体的情感流露。但事实是我觉得自己难以为此负责,更像是有某种不可违抗的冲动念头驱使我如此果决地表露了感情。我承认这份感情不合时宜,”他大笑起来。“但超越控制的爱是我唯一的借口。”格雷厄姆没有再待多长时间就离开了。他如释重负——或者说一种解脱的感觉席卷全身。但他仍很疑惑,他想一个人好好地依照自己的标准把这种现象解释清楚。
他没有打伞,而是任由雨水肆意落在脸上,沿着被雨水打湿闪闪发亮的人行道大步走去。他走了好远,快走到头时,雨停了,几颗小星星冲着他眨眼,他才恍然大悟。他记得六个月前,他向费沃汉姆暗示波琳妩媚迷人,聪明真诚,值得关注。但关于爱情呢?他只字未提。爱情已然不请自来,它没有先问“你愿意吗?”或者求得“蒙您允许”再来。爱情占了主导,这让费沃汉姆足以应对宇宙中的任何力量。这的确是对格雷厄姆的一大启发。
他的思绪任意驰骋着,回想起刚才最后一个催眠暗示影响下费沃汉姆的异常举动,格雷厄姆欣然接受了这个猜想:爱情与心理暗示这两种力量在这个男人的潜意识里短兵相接,最终爱情胜出。他确信这就是原因。
格雷厄姆抬头望着那些眨眼的小星星,它们也低头看着他。他俯首认输了,爱情这种动力才是至高无上的,而这就是生活。
注释:
[1]催眠降神会(hypnotic séances),设法与亡灵对话的集会。
[2]地名,译文采用了意译。
[3]早期弗拉芒画派(Flemish School),从题材与风格方面,对古典主义绘画进行了较大突破,在油画和版画中运用了幽默风趣和虚构遐想的手法。其作品所具有的讽刺性以及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对后世的漫画都具有影响。
[4]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活跃在格拉斯哥的一批水彩画家和油画家。W.麦格雷戈(William Mac Gregor)和J.佩特森(James Paterson)是创始人,其他有关的人有D.卡梅伦(David Cameron)爵士,J.克劳霍尔(Joseph Crawhall),E.霍内尔(Edward.Hornel),E.沃尔顿(Edward.Walton)及(1884年后),A.梅尔维尔(Arthur Melville),受法国印象派的影响,他们把充满活力的画风与形式和色彩的装饰性效果结合起来。
[5]丁尼生(1809年—1892年Tennyson ,Alfred Tennyson Baron),英国诗人,生于林肯郡萨默斯比,就学于剑桥大学。1830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但反映不佳,1842年的修订本确立了他的声望,他的主要诗歌成就是悼念友人哈勒姆(A.Hallam)的哀歌《悼念》(In Memoriam,1850)。1850年11月19日,丁尼生就任英国桂冠诗人。
[6]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年5月7日-1889年12月12日),是一名英国诗人,剧作家,主要作品有《戏剧抒情诗》(Dramatic Lyrics),《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诗剧《巴拉塞尔士》(Paracel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