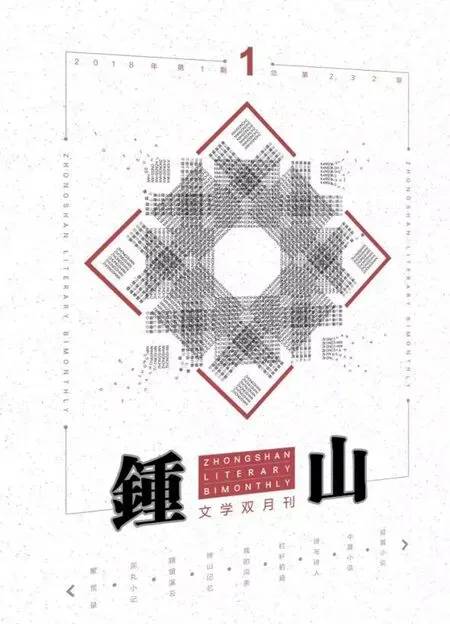韩东的诗
韩 东
白色的他
寒风中,我们给他送去一只鸡
送往半空中黑暗的囚室
送给那容颜不改的无期囚犯。
然后想象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孤独地啃噬。他吃得那么细
每一根或每一片骨头上都不再附着任何肉质
骨头本身却完整有形
并被寒冷的风吹干了。
当阳光破窗而入,照进室内
他仰躺在坍塌下去的篮筐里
连身都翻不过来了。
周围散落着刺目的白骨
白色的他看上去有些陈旧。
(2015-2-12)
斯大爷
天还黑着,我们开始集合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
二十年前也是这样
死者很年轻,但今天
离开的人已经半老了。
送别的队伍里仍有年轻人
大多是他生前的“滑友”
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这些年他迷上了轮滑
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党。他是
轮滑一族里身手矫健的“斯大爷”。
鼻尖上面有一点灵
后来转移到他的衣领上——
阳光透过雾霾辉映那镜框
回眸一笑看着他的队友。他比
二十年前离开的小夏还年轻
比我们想象的朋友更多。
斯大爷走好!
(2015-4-3)
狗会守候主人
狗会守候主人
小孩会等待妈妈
他领着一条狗走出去很远。
那时辰天地像是空的
田野里没有人,收工的喧哗已过。
他并不感到寂寞。一路看着西天
路却是向北的。
有一段时间他被晚霞吸引
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就像妈妈把他和小白留在了这世上
他并不感到寂寞。
我守候的人已经故去了
跟随我的狗也换了好几条
这里是多么的拥挤和喧闹。
在那空空如也的土地上妈妈回来了
推着她的自行车
我听见了铃铛声。
接着天就完全黑了。
(2015-4-11)
忆母
她伸出一根手指,让我抓着
在城里的街上或者农村都是一样。
我不会走丢,也不会被风刮跑。
河堤上的北风那么大
连妈妈都要被吹着走。
她教我走路得顺着风,不能顶风走
风太大的时候就走在下面的干沟里。
我们家土墙上的裂缝那么大
我的小手那么小,可以往里面塞稻草。
妈妈糊上两层报纸,风一吹
墙就一鼓一吸,一鼓一吸……
她伸出一根手指让我抓着
我们到处走走看看
在冬天的北风里或者房子里都是一样。
(2015-4-11)
藏区行
总是有辽阔的大地
但你不能停下
停下就有阻挡,身陷一个地方。
草在草原上扎根
田鼠在田里打洞
人活在村子上杳无音信。
必须有速度
有前方和后方。
掠过沉重的风景,让大山变远山
雪峰如移动的白云。
青稞架上还没有晾晒青稞
古老的房子里来不及住进新鲜的人。
总是有辽阔的大地被道路分开
有两只眼睛分别长在左边和右边。
总是有人不愿停下
像此刻天上的鹰
更像一根羽毛。
(2015-4-13)
割草记
那些不知名的巨草长在湖边的浅水里
船像云一样飘在它的半空。
船上的孩子跳进水里站起来
就没有那些草高了。
挥舞柴刀,砍树一样他们把草砍倒
拖上木船以前在水面漂上一阵。
几棵巨草就铺满了船舱
和仍然站在水里的草一样绿。
夕阳无一例外,给船和草涂上金色。
之后孩子们把柴刀和衣服扔上船去
开始在明晃晃的水里玩耍。
整整一个下午,直到
有人踩到了一块石头。
那股浑浊的红色冒上来以后天就突然黑了。
船上的青草失色,就像枯草一样。
孩子们上船,索瑟着。
船像云影一样漂过月下荒凉的湖面。
(2015-5-19)
电视机里的骆驼
我看见一只电视机里的骆驼
软绵绵地从沙地上站起。
高大的软绵绵的骆驼
刚刚在睡觉,被
灯光和人类惊扰
在安抚下又双膝跪下了。
我的心思也变得软绵绵毛茸茸的。
就像那不是一只电视机里的骆驼
而是真实的骆驼。
它当然是一只真实的骆驼。
(2015-5-31)
爱真实就像爱虚无
我很想念他,但不希望他还活着
就像他活着时我不希望他死。
我们之间是一种恒定的关系。
我愿意我的思念是单纯的
近乎抽象,有其精确度。
在某个位置他曾经存在,但离开了
他以不在的方式仍然在那里。
对着一块石头我说出以上的思想
我坐在另一块石头上。
园中无人,我对自己说:
他就在这里。
在石头和头顶的树枝之间
他的乌有和树枝的显现一样真实。
(2015-6-5)
给普珉
有时,我的心中一片灰暗
想找一个远方的朋友聊一聊
因为他在远方。
他的智慧让他卑微而勇敢地生活
笑容常在,像浑浊世界里的一块光斑。
走路、做菜、乘坐单位的班车……
他酿造一种口感复杂的酒
把自己喝醉了。
我常常想起他的醉态可掬、他的酒后真言。
他在一张灰纸上写了一个黑字“白”
我在白纸上写了一个灰字“黑”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聊一聊:
卑微的生活,虚无的幻象。
(2015-6-21)
致煎饼夫妇
时隔五年,这煎饼摊还在
起早贪黑的小夫妻也不见老
还记得我要两个鸡蛋、一根油条。
人生而平等,命却各不相同
很难说他们是命好还是命孬
只是甘之如饴,如
这口味绝佳的煎饼。
时机一到,他们就要回到故乡
干点别的,但绝不会卖煎饼。
他们会做梦:女的摊饼,男的收钱、装袋
送往迎来。
干这活的时间的确太长了。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
还是上班的早高峰
或是悠闲假日
总是推车而出,在固定的街角。
即使严厉的城管也为之感动
道一声:“真不容易呵!”
(2015-6-23)
我们不能不爱母亲
我们不能不爱母亲
特别是她死了以后。
衰老和麻烦也结束了
你只须擦拭镜框上的玻璃。
爱得这样洁净,甚至一无所有
当她活着,充斥各种问题。
我们对她的爱一无所有
或者隐藏着。
把那张脆薄的照片点燃
制造一点烟火。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爱一个活着的母亲
其实是她活着时爱过我们。
(2015-11-8)
黄鼠狼
一生中总会碰见一次黄鼠狼
可惜他已经死了。
漂亮的黄鼠狼,在人间的大马路上
奄奄一息。
巨足在他的前面停下
然后走开了。
我们感觉不到那可怕的震动
他也感觉不到。
唉,我要是一只黄鼠狼
就带你回家了。
我要是一只鸡就让你咬一口。
能做的仅仅是用一张餐巾纸
包住软软的你
放入路边的树丛中。
湿泥会亲近你
阴影会让你舒服些。
然后我也走了
穿过车声嘹亮的市区
为一部电影的融资奔忙。
在那部电影里也会有一只黄鼠狼
一瓶拧开的矿泉水淋向他
使其复活。
(2016-4-11)
果子
我吃到一个很甜的果子
第二个果子没有这个甜
第三个也没有。我很想吃到
一个比很甜的果子还要甜的果子
就把一筐果子全吃光了。
这件事发生在深夜
一觉醒来,拧亮台灯
一筐红果静静发光。之后
果子消失,果核被埋进黑暗
那个比很甜的果子还要甜的果子
越发抽象。
(2016-4-24)
生命常给我一握之感
生命常给我一握之感
握住某人的胳膊
或者皮蛋的小身体
结结实实的。
有时候生命的体积太大
我的手握不住
那就打开手掌,拍打或抚摩。
一天我骑在一匹马上
轻拍着他的颈肩
又热、又湿、又硬,一整块肌肉
在粗实的皮毛下移动。
它正奋力爬上山坡——
那马儿,那身体,那块肌肉。
密林温和地握着我们,
生命常给我一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