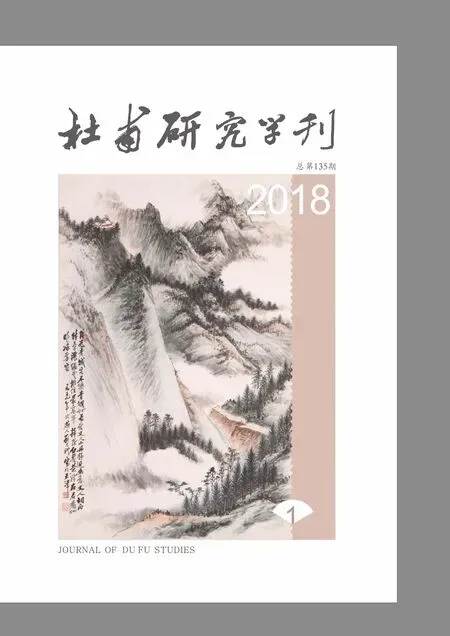记录与呈现
——唐代儿童题材诗歌的文化内涵
赵小华
儿童作为人类自然生命的开始,往往因没有独立思想和行动能力而被忽视。历史研究者总结儿童史研究的困境时指出:“过去的儿童不受重视,不值得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将儿童排除在外;儿童缺乏政治上的筹码和为自己争取在历史舞台上的发声机会;小孩本身留下来的资料非常少,造成研究上的困难。”事实上,在文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儿童既不可能是文学的独立阅读对象,通常也并非主要创作对象。由于儿童不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因此文学中的儿童形象是通过成人的眼光来描述的。一方面,成人是儿童的观察者和记录者,通常经由对儿童的观察引发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时光流逝的体悟,儿童在大人的注视下成长,承载了大人的无限期待;另一方面,由于描写对象具有的天真特性,众多文学作品又深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因此对童真的描写生动有趣,儿童在诗中呈现自我的同时也留存了不少意趣盎然的儿童行为和生动活泼的儿童形象,为儿童文学和儿童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唐诗在艺术和题材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其题材包罗万象,对儿童的描写和刻画便是其中之一。唐代儿童题材诗歌以其娴熟的表达手法、对儿童的充分关注而超越前代,在对儿童的记录和书写中思考人生、体悟岁月、回忆童年,在表达丰富多彩、充满童趣的儿童活动中深入生活、着眼日常,塑造了意趣盎然、迥异多姿的儿童形象。这些并非专门为儿童阅读而创作的儿童题材诗作,既是对儿童生活的观察和记录,又是儿童个体形象呈现与诗人自我感情呈现的载体;既有诗人个人的生活轨迹,又有社会文化的影子。这使得唐代儿童题材的诗歌具有了精彩纷呈的文化内涵。
一、观察和记录:成人注视下的儿童
在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儿童的成长也离不开儒家规范的方方面面。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学者概称为“缩小版的大人”。然而,深入唐代诗歌的阅读便可发现,唐诗中的儿童,除了定型于卓越超常、数岁能诗赋等儿童成长故事框架外,由于作者文化身份不一、创作情境有异,在成人观察和记录中的儿童形象,至少还寄托着家道失传的无嗣之忧、家道续传的殷殷期盼以及岁月不居的生命浩叹等三方面的文化内涵。
(一)家道失传的无嗣之忧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来协调社会关系,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的一个思想传统。在家庭关系的协调方面,孝道的倡扬无疑是传统儒家最大的着力点。唐人孝亲观念的形成,与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文化传统的继承、唐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等因素密切相联,并最终得益于唐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出于对孝道社会功能的认识,唐代历朝帝王高度重视《孝经》,唐玄宗更是亲注《孝经》,使帝王对《孝经》的重视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篇》)的要求自然被附加到了生育行为上,成为每一个家庭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等传统教条也成为了唐代士人须义不容辞遵守的义务和责任。而一旦没有子嗣传宗接代,家道可能失传的隐忧便会体现在儿童题材的诗歌中。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白居易。
白居易与杨氏初婚于元和三年,次年生长女金銮。其后,他与杨氏先后又生养四个儿女,却一个一个夭折。白居易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无子之忧、复在生命晚年遭遇失子之痛。作为一个父亲,他承担了太多的痛苦。元和五年,白居易三十九岁,在长安任左拾遗。长女金銮一岁生日便在此年。白居易作《金銮子晬日》云:“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生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从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无夭折患,则有婚嫁牵。使我归山计,应迟十五年。”年届不惑方为人父,又是个女孩,诗人的心情可谓百感交集:既欣慰于刚刚周岁、学坐学说话的女儿能宽慰自己目前的心情,又清楚地知道这种宽慰只是暂时的(“徒云慰目前”);既欣喜于中年得女,又明确提出孩子的性别所带来的身外之累——为了抚养女儿长大成人的最直接代价,便是“使我归山计,应迟十五年”。诗至此,似乎读到一丝“无子”的遗憾和隐忧。
客观地说,由于金銮是长女,白居易对她甚是喜爱,多次诉诸诗歌,为金銮而作的诗有五首之多。除了为女儿周岁所作的《金銮子晬日》,其他四首则是女儿夭折后的诗作。女儿夭折加上母丧及自身病痛,令白居易哀痛欲绝、长歌当哭,其《病中哭金銮子》诗云:
岂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卧惊从枕上,扶哭就灯前。有女诚为累,无儿岂免怜?病来才十日,养得已三年。慈泪随声迸,悲肠遇物牵。故衣犹架上,残药尚头边。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别是终天。
诗人怀念三岁即夭折的小女,看到女儿生前所穿的衣物和病中所用的药,不由得睹物思人、悲从中来。清代查慎行评价道:“‘有女诚为累’二句二语写得出,说得完。”此诗不无悲伤地道出“无儿”之痛,使得丧女之悲更添一层凄凉,诗人在病痛中交织出的父爱令人不忍卒读。三年后,白居易偶遇金銮的乳母,不禁想起亡女,感伤不已,遂作《念金銮子二首》。其一云:“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一朝舍我去,魂影无处所。况念夭化时,呕哑初学语。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伤苦。忘怀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伤心,因逢旧乳母。”回想起女儿牙牙学语的时候,天真活泼,惹人爱怜,而今阴阳相隔,令人心伤。而“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二句,仍然饱含无限心酸,更清晰地表明了白居易对于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遗憾。
这种遗憾事实上延续了多年。白居易后来连生三女,当然有为人父亲的欢乐,但一想到将来有嫁无娶、后继无人,他还是免不了心情苦闷。《自到浔阳生三女子因诠真理用遣妄怀》中说:“远谪四年徒已矣,晚生三女拟如何?预愁嫁娶真成患,细念姻缘尽是魔。赖学空无治苦法,须抛烦恼入头陀。”远谪四年、报国无门、回京无望,本已令人心灰意冷;这种情况下的连生三女,不但没给他带来能够超脱当下的喜悦,反而使他预先对将来的嫁娶产生了烦恼,以至于生发出“晚生三女拟如何”的浩叹。而嫁与娶的对举中,有女出嫁、无儿行娶,没有儿子续传家道的忧伤时时萦绕其内心深处。
这种“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念金銮子二首》其一)的感情,不仅在白居易的女儿诗里被反复表达,而且也一次次地形诸于其他诗篇,被一再申发。如通过直接抒发没有儿孙的悲伤来宣泄心中无尽的压抑与焦虑;用故作洒脱的调侃方式来表达没有直系子孙的无奈;通过对女儿、外孙的怜爱来反衬其没有男性后代的凄苦心境;通过对别人荣享儿孙之福、多子多孙的艳羡,来表达自己能够拥有儿孙的强烈渴望以及通过与友人的同病相怜,来表现自己没有儿孙的绝望。
(二)家道续传的殷殷期盼
正因为白居易的无嗣之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忧伤力度如此之大,在他对人生几近绝望的晚年时迎来的小儿阿崔,委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他把自己的欣喜异常写入诗中,与同有无嗣之忧、如今老来得子的元稹共相庆贺。《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为咏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其一云:“常忧到老都无子,何况新生又是儿。阴德自然宜有庆,皇天可得道无知。一园水竹今为主,百卷文章更付谁。莫虑鹓雏无浴处,即应重入凤凰池。”晚年得子,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更是家业的传承。诗人马上便考虑到了“百卷文章更付谁”的问题,甚至孩子还在襁褓中时就已经设想了他的未来,“弓冶将传汝,琴书勿坠吾”(《阿崔》)、“且有承家望”(《和微之道保生三日》),诗人的激动和喜悦跃然纸上。
唐人对孩子的殷殷期盼,常常通过读书扬名或建言立功的嘱咐体现出来。

那些“稚子齐襟读古论”(卢纶《晚次新丰北野老家书事呈赠韩质明府》)、“书从稚子擎”(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绪公》)的天才幼童,读书是其不二选择。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今年始读书,下口三五行”,并勉励小侄“勤勤不自已”,祝愿他“二十能文章”,最终达到“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的理想境界。在韩愈看来,学与不学,会造成人生的巨大差异。其《示儿》和《符读书城南》,皆重在劝勉学业、寄托厚望。《符读书城南》更铺陈两家儿童的成长过程,落笔于“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云泥之别,指出两家孩子小时候没有多大差异,而学习与否则带来天壤之别:“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同样是勉励儿子,韦庄在《勉儿子》中表达了身逢多难、担心儿子起步学习已晚的情况下希望他“辟疆为上相,何必待从师”的愿望。李商隐《骄儿诗》云“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以自己的生命为比照,仕途坎坷的李商隐不希望儿子读书求功名,流露了饱读诗书却不被重用的愤激。
(三)岁月不居、人生难测的生命浩叹
儿童,最容易让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从而提醒时间的流逝,引发人生的感慨。这也是唐代儿童题材诗歌区别于前代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在那些怀念亲人的感怀之作中,儿童往往成为家乡的指代对象,并引发作者年华老去、壮志未酬、漂泊异乡的羁旅之叹。如杜甫《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云:“消渴游江汉,羁栖尚甲兵。几年逢熟食,万里逼清明。松柏邙山路,风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又示两儿》:“令节成吾老,他时见汝心。浮生看物变,为恨与年深。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从诗题来看、诗是写给宗文、宗武的,但这些诗其实并非专为孩子而作。纯真无邪的孩子,在这里是无情的时间流逝之提醒者,所谓“汝曹催我老”;同时也是漂泊者思乡怀土的集中指代,其内涵可以从孩子推广到小家庭的妻子儿女、大家庭的兄弟姐妹甚至生长于斯的故乡。而萦绕着诗歌的感情和主题,还是年华老去的感叹和漂泊在外的悲怀。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诗人开篇便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那时身体健壮不知忧愁为何物;时光飞逝,转眼到了知天命之年,身体羸弱得大多数时候只能或坐或躺,甚至连一顿饱饭都不能让儿子吃上。身心困顿、穷苦潦倒,诗人内心的沉痛可以想见。细绎此诗的感情,将今时今日的困境与童年健朗蓬勃的生命力、无忧无虑的心态相对比,后者何其让人留恋。

往者十四五,岀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
与《百忧集行》中天真顽劣、淘气可爱的少年形象不同,杜甫此诗所刻画的是一个小小年纪便展露锋芒、天赋异常的少年。他诗书潇洒、性情豪放,有着出人头地、成为国家栋梁的无限可能。然而,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往往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如此优异的少年,经过人生患难的现实后,却是老病交困、潦倒不堪:“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天赋少年的人生道路没有沿着意气风发的方向发展,在远离朝廷不得重用、衰弱多病辗转奔波的现实当下回想光彩夺目的少年美好时光,其间的落差甚于《百忧集行》中顽劣少年与落魄老年的对比,诗人多舛人生的痛苦经历更加令人慨叹。
不管是从时间的流动还是生命的发展来说,成年都意味着与童年的永别。那些天真无邪、淘气快乐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而生命一代代传承,目力所见的儿童,天真可爱、不解世事,总会让诗人驻足欣赏甚至羡慕,并勾起诗人无限感慨。因此白居易发而为咏《观儿戏》:
龆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堂上长年客,鬓间新有丝。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童騃饶戏乐,老大多忧悲。静念彼与此,不知谁是痴。


二、儿童的发现:一派天真的书写
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每一个成年人的心灵深处都还保留着一点童真。同时,儿童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本性又强烈地吸引着成人。这使得作者为成年人的诗人群体在将目光转向孩子时,不自觉地会关注儿童生活、描摹儿童情态、表现儿童意趣,使诗歌摆脱言志、载道的沉重,从而呈现出一派天真的书写。
(一)深入日常生活

白居易一生,书写了大量儿童题材的诗歌,上至亲人生老病死的重大变故,下至日常琐碎的点滴小事,都反映在诗中。白诗以通俗晓畅的语言、白描般的细节刻画加强了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于细微之处表现的感情更富于人情味。如《路上寄银匙与阿龟》叮嘱阿龟“银匙封寄汝,忆我即加餐”,从吃饭小事上关怀后代,显得感情深厚。在他老年得子、喜不自胜的诗中,《阿崔》先叙吉祥的梦境,再细述“腻剃新胎发,香绷小绣襦。玉芽开手爪,酥颗点肌肤”,不厌其烦叙写小婴儿的胎发、体香、绣襦、小手小脚以及娇嫩的皮肤,细致入微的描述中,充满着爱不释手的由衷喜悦。
罗子是白居易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白居易有专门写诗给她以表父爱:
吾雏字阿罗,阿罗才七龄。嗟吾不才子,怜尔无弟兄。抚养虽骄騃,性识颇聪明。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我齿今欲堕,汝齿昨始生。我头发尽落,汝顶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婴。缅想古人心,慈爱亦不轻。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可以注意的是,诗歌没有丝毫的豪言壮语和意气纵横,对女儿娇态的刻画和宠爱都是通过日常小事的描写来实现的。如写罗子学母画眉、学自己吟诵诗歌来表达小女孩的古灵精怪、惹人爱怜;老年幸得一女的喜和忧,是通过自己掉牙而女儿长牙、自己掉发而女儿长发等细节对比来突出的,“老幼不相待“的感叹尽在其中。
同样是书写子女,李商隐的长篇《骄儿诗》明显承袭左思《娇女诗》的主题,开篇直言“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一个“骄”字,流露出父亲对孩子的无限喜爱。接着则从点滴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入手,不厌其烦地叙写儿子成长过程的趣事。先反用陶渊明《责子》诗意,叙述衮师未到周岁已知数数;再引用他人的话语,夸张地铺写其美秀无匹的样貌;接着用很长篇幅细写儿子与同伴互相追逐、绕堂穿林;或嘲笑客人脸黑如张飞、口吃如邓艾;或截了青竹当马骑、摹仿参军腔调呼唤苍鹘;或学大人礼佛拜佛;或沾蛛网、饮花蜜;或追蝴蝶、玩柳絮……所有这些,便是一个四岁孩子生活的全部,也都是日常生活小事。诗歌后部分言“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是李商隐对自我生命之曲折消磨的反观,充满了伤感与愤激。然而,诗歌对日常生活的深入描写和关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悲愤,从而使作者和读者都转入了对这个无忧无虑玩耍、成天叽喳笑闹的儿童长大后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多种可能的思考。
(二)意趣盎然
由于儿童懵懂无知、可爱无邪的天性,唐代儿童题材的诗歌,多径直白描儿童憨态,体现出童趣十足、意趣盎然的审美风格。这类诗歌往往不重笔法和技巧,诗人不介入书写,以近乎纯粹的观察和记录,让儿童在诗歌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呈现。
韦庄的《与小女》诗“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华。”用寥寥数笔的白描手法,将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娇态完全展示了出来:孩子以哭闹、撒娇的形式来表达自身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是其本性;而让他们哭之闹之的理由却又令人哭笑不得。相反,大人郑重对待的事情,在儿童那里却时常被儿戏化。这中间的反差,令人无可奈何。远别亲人、离家万里,对大人来说非常沉重,但孩子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初岁娇儿未识爷,别爷不拜手吒叉。拊头一别三千里,何日迎门却到家。”(杜牧《别家》)诗中的孩子因为年龄太小还不能体会大人的离情别意,对父亲要离家一事毫无概念。当大人身心憔悴却还要照顾儿童时,其难度也会大大增加。“数日不食强强行,何忍索我抱看满树花。不知四体正困惫,泥人啼哭声呀呀。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父怜母惜掴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卢仝《示添丁》)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孩,丝毫不理会大人的困顿,哭着闹着要去看花,又翻检案几上的墨汁、四处涂抹乱画,大人忍无可忍想要打他以示惩罚,他却因玩得高兴而开怀大笑。这样的诗,千年后读之仍然令人忍俊不禁。
年龄稍长一点的孩子,稍稍脱略了懵懂无知。为得到“已长大”的认可,常常有板有眼地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行为突出了他们主观愿望期待成熟与行为的稚嫩间的反差,更令人感到他们的天真与可爱。施肩吾的《幼女词》就描述了一个学大人行为的小女孩形象:“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诗歌选取“拜月”这一典型情节,用凝练的语言刻画了六岁的小女儿涉世未深、分不清巧与拙,却又装作大人、有模有样地学习大人的行为,浅而有致的语言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胡令能笔下的钓童则是一个形象更为突出的模仿大人举止的小孩儿:“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小儿垂钓》)这个头发蓬乱、学大人钓鱼的小男孩,为了不惊扰鱼儿上钩,老远就向问路的行人挥手,示意别人不要发出声音。丰富的体态语言让人看到一个煞有介事的“小大人”形象。
在写作手法上,儿童题材的诗歌多用细节塑造形象、以典型事件突出特征或白描儿童动态等手法,语言浅白凝练,虚实并用,开拓了场景生动、童趣盎然、留有空白的审美空间。杜甫《羌村三首》中“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北征》中“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都是以细节描写取胜的典型。前者以孩子见到久别重逢的父亲、担心他再次离家而紧紧靠着父亲的膝盖不肯离去的细节,深刻表现了战乱给无辜孩子带来的痛苦;后者以孩子拉扯着父亲的胡子絮絮发问来表达对久别归来的父亲的依恋之情。两诗都从儿童的角度入手,选择细节进行刻画,以儿童独有的动作和情态构成诗歌生动的场景画面,增强了诗歌的表达力量。“稚子无忧走风雨”(《秋雨叹》)抓住儿童喜爱淋雨的习性,以一个“走”字激活读者对雨中活蹦乱跳孩童的想象;“许求聪慧者,童稚捧应癫”(《从人觅小胡孙许寄》)令人可以想象儿童得到心爱的小动物时的欣喜若狂。白描手法的运用则令诗人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勾画中表达感情。“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杜甫在《泛溪》中刻画的,是一群热爱嬉戏玩耍的儿童形象。他们以游戏的方式来劳作,又将劳作看作游戏,因此兴致勃勃地捉鱼采藕,终至颠倒忙乱、一片热闹,诗人对儿童天真活泼的赞赏,尽在言外。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的这段时期,生活相对安稳舒适,因此其笔下的儿童描写也多了一份悠闲。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不难读出诗人放松的心情和美好的家庭生活。白居易《池上二绝》其二描写憨厚可爱的小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寥寥几句浅而有致的语言,近乎白描的手法,将小孩儿偷偷采莲自以为成功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诗歌刻画小孩儿采莲动作是白描、实写;至“浮萍一道开”嘎然而止,小孩子洋洋自得的心理、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及大人的忍俊不禁是留白与虚写。虚实结合,孩子天真淘气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三)留存丰富形象
千千万万的儿童在世间蓬勃成长,各有不同形象;同一个孩子的不同生命阶段,也有不同的行为动作和爱好习惯。唐代儿童题材的诗歌吟咏了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留存了形态各异的儿童形象。
作为白居易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罗子,在许多诗篇中一次次出现,其形象各有不同:“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罗》)、“唯弄扶床女,时时强展眉”(《新秋》),当是小婴儿时期处于对大人强烈的情感依赖阶段;“稚娃初学步,牵衣戏我前”(《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官舍》)、“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已隐约可见稍有独立行动和思想能力,会自己玩耍找乐了;“戏团稚女呵红手,愁坐衰翁对白须”(《雪中即事寄微之》)则见出天真无邪的孩子是大人们感情的慰藉;“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吾雏》)中的罗子,显然年龄更大些,画眉咏诗的行为,正是她展示自己脱去稚嫩的努力。


刘驾《牧童》诗有云:“牧童见客拜,山果怀中落。昼日驱牛归,前溪风雨恶。”牧童生活虽然辛苦,遇到恶劣的风雨天气更是恼人,但诗中的孩子仍然顽皮而可爱。为了礼貌地拜见客人,竟把怀中精心收集的果子洒落了一地。拜客的情景活灵活现,充满童心童趣。张籍的《牧童词》描绘了一幅真实的牧童生活场景:“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饥乌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垄头。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隔堤吹叶应同伴,还鼓长鞭三四声。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为保护庄稼,这个负责任的小牧童把牛儿赶到远离村子的地方吃草;为保护牛儿不被鸟儿啄它的背,要时时给它驱赶鸟儿;有时还一边卷卢叶吹口哨与同伴相应和,一边鼓动长鞭对不好好吃草的牛发出警告……这些清新平实的语言描绘出牧童的心理和牛的动态,构成了一副绝妙的牧牛图。牧童没时间玩耍的苦恼、与同伴吹叶互应的快意、对牛儿煞有其事的恐吓,都表现出孩童的天真与稚拙,尤见童趣。另一方面,有些牧童诗则着力描绘牧童的自在与悠闲。栖蟾的《牧童》可作为代表:“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自由潇洒地骑在牛背上,徜徉于青山绿草间,吹笛唱歌、月明而归、无忧无虑,颇有些自得其乐。成彦雄《村行》曰:“暧暧村烟暮,牧童出深坞。骑牛不顾人,吹笛寻山去。”所刻画的牧童的悠闲愉悦,似乎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卢肇《牧童》:“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牛背上不仅可以吹笛唱歌,技术高的还可以躺着休息。这些诗化了的牧童生活画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人对悠然自得生活的追求,寄托了诗人超脱人世、快意潇洒的理想。

三、父亲角色的回归:亲情环绕的世界
唐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之朝。躬逢其盛,唐人以其剑胆琴心和诗酒风流指点江山、歌咏盛世,体现出奋发昂扬、求取功名、潇洒不羁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然而从儿童题材的角度检视唐诗会发现,诗人在进行儿童题材诗歌的书写时,往往脱略功名、回归亲情,流泻平日藏于心中的父爱,抒写慈父对子女的骨肉亲情,以对儿童的包容和温情显露出对家庭的珍惜,展现了非常珍贵的人性光辉。
“诗仙”李白以其汪洋恣肆的才华、俊发豪放的性格、天马行空的性情、自由飘逸的洒脱吸引了众多读者,然其儿童题材的诗歌却简朴平实、感情真挚,体现出李白慈父情深的另一面。《寄东鲁二稚子》是李白漫游金陵时写给寄居于东鲁儿女的诗: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值得注意的是,慈父书写集中出现在几种情况下。除前所述陪伴成长、远方思念或因事触动外,一旦遭遇丧子之痛,唐人往往行之歌咏,在诗中抒发对早殇儿女的伤惜之痛,为后世留下不少字字血泪、句句真情的悼亡之作。
中晚唐著名诗人孟郊生活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时期,贫困的折磨、仕途的坎坷及狷介的性格让他极为痛苦,晚年接连遭遇的丧子之痛,更使他身心受到极大折磨。《悼幼子》《杏殇》(九首)便是他老来失子、内心悲痛的集中体现。《悼幼子》曰:“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诗歌起句便直接描述儿子离世的残忍现实。身为父母,都有过“独有开怀处,孙孩戏目前”(权德舆《早春南亭即事》)的快乐体验。相较之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风一般飘散不见、尸骨无存,“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则特别令人难以接受。从孩子的角度说,父母养育之恩未报;从自身感受言,千行泪也流不尽心中的伤痛。悲从中来、凄怆欲绝的感伤笼罩着全诗,令人不忍卒读。《杏殇》九首,更是将诗人内心郁积的痛苦倾泻而出。诗序曰:“杏殇,花乳也,霜翦而落。因悲昔婴,故作是诗。”诗人由零落于寒霜中的小花朵想起自己夭折的孩子,悲痛不能自已。“零落小花乳,斓斑昔婴衣。拾之不盈把,日暮空悲归。地上空拾星,枝上不见花。哀哀孤老人,戚戚无子家。”花儿尚未绽放而凋零,给人留下虚空一场、一切成空的感觉。诗歌接连用“空”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失子后空洞无依、空寥孤寂的内心。“哀哀孤老人,戚戚无子家”“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失芳蝶既狂,失子老亦孱”等句,更是将老来失子的凄惨、白发人哭黑发人的悲恸细细道来。这些情感真挚、意象哀婉的诗,激起了许多人的感情共鸣,如王建有《哭孟东野二首》“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本杏殇诗”。孟郊以诗歌倾诉自我的不幸,也因至真至性的真情流露为人所怀念。
中晚唐诗人元稹,学界多将目光投及其悼念亡妻之诗,而对于他悼念女儿的诗较少关注。元稹有十多首悼念孩子的诗,非作于一时一地,时间跨度长,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爱女樊在他乡染病去世,元稹痛作《哭女樊四十韵》以示怀念。他看着嬉戏的小外甥,想起女儿扶床学步、对镜呵气、筝前试弹等生活场景,细数小女情态,一一还原往日生活;而就在这种活生生的还原中,历历在目的欢乐回忆与女儿已不在人世的强烈对比,令人悲肠欲断。《哭子十首》也多采用渲染父母悲情和回忆日常生活的叙写方式。如“尔母溺情连夜哭,我身因事有时悲。钟声欲绝东方动,便是寻常上学时。”夫妻二人因丧女之痛而哭泣难过、彻夜无眠,不觉东方将晓,孩子该去上学的时辰又到了。诗歌至此,令人心里猛地一紧,能够想象诗人伤心欲绝的日日夜夜了。

唐代儿童题材的诗歌以对儿童的描写和刻画为主要内容,忠实记录了诸多儿童生活方面的情况,同时又不自觉地让儿童于诗中呈现自我。诗人既是儿童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也不由自主地在诗中呈现自我对童年和人生的感悟;涉及到亲情的儿童题材诗歌,更是诗人自我情感的集中呈现。唐代儿童题材诗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值得更进一步发掘。
注释
:① 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宄的回顾与展望》,陈恒主编《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②对中国儿童的历史及形象的研究,西方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两部专著。Anne Behnke Kinney,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Earl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主要聚焦汉代及以前的儿童发展情况。Anne Behnke Kinney ed,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这部论文集收录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儿童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其研究年限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其中收录的PEI-YI WU,Childhood Remembered: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China 800 to 1700 ,对韩愈墓志铭和李贽“童心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相较于国外儿童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及国内学者对于汉代和宋元以后的研究,古代文学中的儿童研究比较薄弱。以唐代而论,虽然相关论文陆续发表,然其体系尚未完整化。近年来,陆续出现几篇以唐代儿童为研究主体的硕士论文,如刘燕歌《唐诗中的少年儿童生活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王丽《唐代儿童诗研宄》(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李巧玲《唐代儿童若干问题研宄》(安徽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阎莉颖《唐诗中的儿童形象》(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力图从诗歌及其他史料来还原当时的儿童生活。学界对杜甫、白居易等诗歌中的儿童较为关注,有系列单篇论文与此相关。但就系统研究唐代儿童题材的诗歌而言,除了收集和整理相关诗歌进行宏观描述外,还需仔细分析诗歌中的儿童类型和不同形象、研究儿童性格和心理、解读儿童生活、勾勒诗人家庭与婚姻等,唐代儿童题材诗歌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③日本学者浅见洋二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儿童与童年如何被认知与表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通过分析六朝陶渊明、唐代杜甫、北宋苏轼与黄庭坚、南宋陆游与杨万里等人的相关作品,对中国诗歌中的儿童与童年有精彩分析。见《中国诗歌中的儿童与童年——从陶渊明到陆游、杨万里》(《人文中国学报》第22期),限于篇幅,他在唐代只分析了杜甫。
④参见赵小华:《史、诗中的唐代孝亲观念:以两唐书〈孝友传〉与唐代孝亲诗为中心的解读》,《唐史论丛》第十九辑;《唐人的孝亲观念与孝亲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⑤(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3页。本文所引白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⑥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版,第261页。
⑦肖伟韬:《“元、白”的无嗣之忧及其文化心理意蕴》,《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
⑧(唐)杜甫:《宗武生日》,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3页。本文所引杜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⑨(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