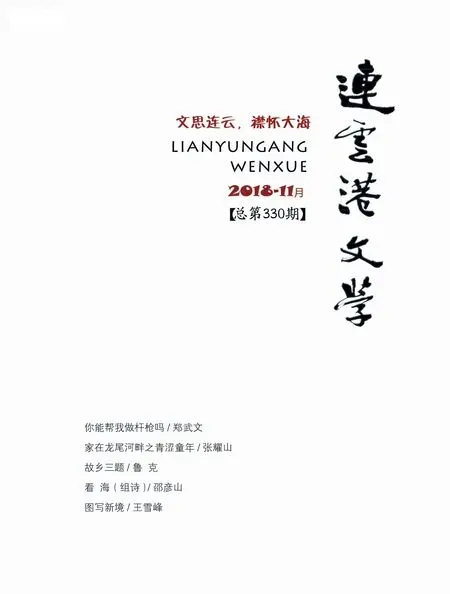十六岁的告别
来山
一
21世纪初年,在夏蔚镇唯一的中学里,我进入了一个叫作青春的时期。中学坐落在省道的北面,每天有成百上千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从大门前经过。那些卡车带着轰轰隆隆的声音来,带着隆隆轰轰的声音去,只留下一阵阵浓烟和遥远的回响。道路南边是一个水库。学校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其余的教室皆是平房。进入校门,一圆形花坛明显地住在校园的中轴线上,花坛中间矗立着一棵雪松,周边种以月季。学校的布局和构图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
站在学校的三楼,向南望去,近处的水库和远处的丘陵尽收眼底。白色的风吹过水面,粼粼波光泛起耀眼的金黄,一条孤独的小船在漂浮摇动着。远处起起伏伏的丘陵像海上的波浪,摇曳中讲述着关于青春的故事。我们以迎风的姿态,推开青春期红色的大门,享受着青春所带来的澎湃激情。
在那所中学里,我从少年跨入了青年,我的身体开始发生一些莫名的变化:喉结开始凸起,过去熟悉的声音消失,稀疏的胡子像是一首前奏。那些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住校从那时开始。周日,花一块钱,乘上屁股喷着浓烟的小客车来到学校。下周六,再坐上挤得满满当当的客车回家。学生像是沙包,被胡乱地堆积在车里,每一个学生就是一块钱,堆得越多,就是更多的一块钱。周六的乘车就像打仗,少年的身体在挤压中得到了淬炼。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步行回家。从学校向南行进,走过水库的大坝,穿过几个村庄,翻过两座山,全程大约需要三四个钟头。山路上,桃树、杏树、梨树、樱桃树和柿子树,一年四季变幻着不同的风景。春天,山花开满两路,蜜蜂围着花蕊震动翅膀腾起透明的小雾;夏天,蝉鸣响彻山间,路上走累了捧起一掬山泉消掉半路的炎热;秋天,柿子高挂枝头,身手矫捷的同伴会攀上高枝炫耀摘取的成果;冬天,寒雪覆盖山岭,天地之间一片茫茫我们走在其间像是朝圣的信徒。
走过四季,我感受着时间的触角带来的震动,观察着轮回产生的代谢枯荣,听着少年的骨骼如春笋破壳般生长。在那条山路上,我从13岁走到了16岁,在那条山路上,我度过了独一无二的中学时代。
宿舍只能用简陋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木板搭建起的大通铺,上下两层,一个宿舍挤着三十多人。我运气还不错,睡在仅有的两张铁床的下铺。开始,脑袋正对着门口,风吹得我脑袋发蒙。后来调换了方向,身体和门口成了直角。然而,无论如何躲避,到了冬天,寒风还是会顺着夸张的缝隙挤进来。班主任给窗户和木门钉上了塑料布,意图将宿舍打造成塑料大棚,把我们当成蔬菜一样培养。
一切都是徒劳!风的刁钻胜过人的智慧。那拥挤、逼仄、透风的屋子,简陋地承载着三十多人的青春。我们就在那混合着汗臭、脚臭以及饭菜味的空间里,进阶到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
我所在的班级是四班。初一入学时,班里有60人。进入初三,退学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自知中考无望或是厌倦了读书的同学,会渐渐地离开。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学,他们安静地收拾被褥、书本、脸盆,像货郎一样把东西挂满全身。他们和几个要好的朋友道个别,有的甚至连道别也没有,就悄悄地从那个班级消失了。我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开始感受到:青春并不全是光彩炫目的亮丽,青春还有着残酷无情的一面。
从此,我们将仿若繁花,四散天涯。那些写在同学录上的话语,那“勿忘我”的铮铮誓言,都湮没在了无边的岁月中。自那以后,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很多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过早地进入了那个叫作社会的地方,从事着五花八门的职业。他们过早地结婚生子,在自己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就已经抚养孩子了。
二
王宝是初三时到班里的。他是复读生,在中考中失败了,对求学的渴望支撑着他再来一遍。教室里,他坐在我左手不远处,宿舍里,他睡在我脚的右前方。多年过去,记忆斑驳,我和王宝在空间上的位置,我只能记得这样的大概。但王宝的样子,我是记得清晰的。
他的身形是精瘦精瘦的,目光是尖锐的。后来我读苏童的《妻妾成群》,看到苏童形容陈佐千“形同仙鹤,干瘦细长”时,脑中立即浮现出王宝的身影。可惜王宝没有陈佐千那样的好福气,不用说妻妾成群了,他连女人都没有摸过。
王宝不仅瘦,皮肤也是黑黑的,脸上肌肉的线条分明,像是用笔从额头一条一条画到下巴。他走路有些驼背,笑起来时,脸上挤出和年龄不符的皱纹。他那种留守儿童式的神情,和他接触的人难免有些心疼。
我和王宝熟悉起来,是因为他借了我一张光盘。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过,借书是恋爱的初步,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推而广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在借与还之间产生关联。王宝借我光盘,我们在一借一还、道谢来回中,交流就多了起来。
2003年,卓依婷已过了她最红的时期。王宝借我的光盘,录的是卓依婷翻唱的歌曲,主打歌是《潮湿的心》。我把光盘带回家,放入父亲从深圳买回的VCD。画面中,卓依婷穿着中式斜襟的翠绿小褂,撑着油纸伞,一边在雨中徘徊一边唱歌。母亲看到画面中的女子,直夸长得好看。就像小时候的某一天,母亲、妹妹和我在吃早饭,电视里播放《摇太阳》的MV,一个年轻女子又唱又跳。母亲对我说,这个女的长得真好看,你以后要是能取个这样的媳妇就好了。我听到母亲这么说,羞愧地低下了头。
青春期的我们,开始懵懵懂懂地感觉到,和异性接触会让我们无故的开心。我和王宝曾聊过关于异性的话题,但那也仅仅局限于哪个女孩子长得好看,谁和谁走得比较近。少年的爱慕是简单而纯粹的。据我所知,王宝并没有谈过恋爱。
学校教学资源有限,初一初二的学生在教学楼上课,初三学生在平房上课。三排平房布置了九个班级,后面是职工宿舍。语文袁老师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屋里藏有很多经典名著,《祝福》《骆驼祥子》《红楼梦》。我喜欢到小屋里去看书。那间房子,正是我文学启蒙的摇篮。
有一段时间,初二一名漂亮的女孩常常从我们教室门前经过,因此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每当她出现,我和王宝等人会趴在窗户上看着她,看到她从东走到西,直到拐过墙角从视线中不见。她留着齐耳的短发,脸上干干净净的,五官小巧精致,倒像是南方的女子。多年以后,回想起一群少年趴在窗户上的情景,我还是禁不住会心地一笑。那时,异性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谜,看不懂也猜不透,明明知道很美好,却不知道该如何与之相处,带着自以为是的不在乎,远远地欣赏。
乡镇中学升学率低,班主任管理严格,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的娱乐活动。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彻底释放了少年的天性。那天下了很大的雪,雪越积越厚,整座学校被裹上了一条巨大的、厚厚的白色毯子。风一吹过,雪花纷纷扬扬从枝头跌落,落到少年们的脸上、颈上和心上。
雪仗忽然就开始了。没有征兆,已经无从考察是谁丢出了第一个雪球。第一个雪球勾引起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以至无数个。所有人在雪地上奔跑着、追逐着、喊叫着,不停地攒起雪球不断地发射攻击。我看到王宝双手冻得通红,他在衣服上擦一擦,将热气呼进两手中间。感觉到温暖后,他又兴奋地投入战斗。那是我们中学时代难得的一次嬉戏。
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班主任从远处走了过来。我们像一群逃兵一样匆匆跑回教室。班主任戴着一贯的黑脸,愤怒地巡视着我们。我们坐在位子上不敢出声,我看到王宝手里的雪球化了,水顺着手指滴到了地上。
三
如果王宝还活着的话,今年该有31岁了。他应该已经结婚,甚至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想象着他结婚的样子,他一定带着那标志性的笑容,眼角的皱纹又深又长,黑瘦黑瘦的他,吃力地从车里抱下新娘,走向长长的红地毯。
然而,那样的画面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样的情节,也只能生发于文字里。王宝的生命,终止于16岁的春夏之交。
中考之前,为了应付体育考试,学校安排课外活动让我们锻炼。那天下午,王宝和同学相约去操场拉单杠。王宝虽然瘦弱,拉单杠却是一把好手,我们以前就见过他在单杠上的轻松潇洒,仿佛不是他在用力,而是单杠在拉他。
就在那天下午,王宝还是像平常一样走向了操场,就像无数个重复的白天无数个重复的黑夜一样。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任谁也不知道,他走向的竟然是生命的最后一站。
天色尚明,操场上人来人往,王宝一跃而起抓住单杠,动作轻盈。王宝上下拉伸几下之后,忽然像一只没有抓住树干的鸟,从枝头跌落下来。同学们焦急地呼唤着他,他没有任何反应。同学背起他就往镇医院跑去。
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王宝在同学背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离去了。同学气喘吁吁的奔跑,也没有救回他。
王宝就这么猝然地、轻易地、戏剧地、永远地离开了。
王宝被安置在医院躺椅上,等待父母来接他回家。王宝的父亲先赶了过来,那个高大的男人怔怔地站在王宝的身边,一言不发。王宝的母亲来了以后,看到儿子躺在椅子上,责怪王宝父亲,为什么不给孩子打点滴。她以为孩子只是睡着了。
在此之前,王宝曾在操场上晕倒过一次,因为王宝身体瘦弱,大家以为他是低血糖。他打了两瓶点滴,休息了半天就继续上课了。后来我们听说,王宝曾晕倒过不止一次,一直都以为是血糖低。这一次,她的母亲依然这么认为。
当王宝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睡着了,而是已经死掉了的时候,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然后就昏倒在医院的地面。
王宝去世的消息,是袁老师告知我们的。当天下午,同学们只知道王宝被送去了医院,以为王宝与上次一样,打过点滴就没事了。晚间,袁老师动作缓慢地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那首诗一共五句,可惜我只记住了后面三句,十几年过去,那三句诗我仍牢牢记得:
风霜雨雪见真情,生命归自然,阳光更灿烂。
我们看着袁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几句诗,不明白他的意图。袁老师两手撑着讲桌,沉重地宣布:王宝同学在今天下午因为脑溢血,已经离世了。袁老师说完,教师里经过短暂的静寂,接着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哭声。
十几岁的我们,意气风发的我们,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的我们,从未想过身边的同学竟会死去。我们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直面死亡。原来死亡不只是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死亡会发生在任何年龄的人身上。与其说同学们是为王宝的离去而哭,不如说是被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吓哭的。
王宝的父亲来到教室,收拾王宝的物品。王宝的抽屉里只有一份吃剩的辣皮,一种用大豆做成的,表面撒着大颗粒孜然的五毛钱一份的辣皮。那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喜欢的食物,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菜。王宝的父亲看到辣皮时,那个高大的男人一下子流下了眼泪,他用克制的、隐忍的哭泣,来哀悼自己的孩子。
那个男人流泪的表情,像是被人拍摄下来,永远地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王宝出生于1987年,逝于2003年,他只有短短的16年生命。他的离去并没有给这个世界造成什么影响,也没有给历史的进程带来什么改变。2003年有太多需要记录的事件,非典席卷全国,伊拉克战争爆发,张国荣和梅艳芳两位巨星离世,那些事件看上去都比王宝的死亡要轰动得多。那一年我也只是一个少年,连记录王宝一生的能力都没有。
他的离去,只给几个爱他的人,带去了长久的伤痛。
王宝离开没几天,教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课上,大家认真备战中考,下课了,大家热烈地聊天。王宝的床位空了出来,虽然宿舍拥挤,但没有人睡到他原来的位置。
王宝的离去,在班里也没有留下长久的伤痛,甚至还带来了一点禁忌的味道。
王宝已经离开人世足足15年了,这个数字几乎接近王宝去世时的年龄。他还能被我们那个班里的多少人记得,我不得而知。这些年我和初中同学聊天,没有听到谁会主动提起他。他没能等到读高中、读大学,没能和女孩子在大学里谈一场恋爱,甚至连女孩的手都没有牵过。
这些年里,我读大学、读研,辗转多个城市,走过长长的路,经过无数的桥,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社会,我努力找寻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我也很少会想起王宝。只是在听到关于初中的事情,或是初中同学群又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王宝这位故人。我一想到他还没有经历什么就离开了,一想到他的生命未曾彻底绽放就凋落了,一想到我和其他同学已经比他多活了15年,我就感到无比的悲哀。
王宝的少年早逝,让我对人和世界的不对等关系,有了痛苦的总结。
当说到“世界”这个词汇时,我的意识里就会出现地球这个意象。世界这个词汇在我的概念里,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纸面上的有限,而是无边无际的。我就像一只小小的蚂蚁,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球面上爬行。
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已经存在了40亿年,而人类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70万年。而我个人存在于这个球体的时间,在漫长的40亿年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望向过去,过去深不见底,我望向未来,未来深不可测。我太小太小,把我扔进那漫长的岁月,不用说水花了,连水雾都溅不起。
王宝16年的生命,在时间的坐标轴上,连一个微小的点都算不上。我的生命能够延伸到哪一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虽然比王宝多走了一些路,但在那无限绵延的长轴上,同样连一个点都算不上。人生往长远了看,都免不了以孤独和渺小收场。
作家史铁生对他的地坛说过,要是有些事我没说,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有些事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王宝16年的生命,我写的有限,那些没有写的,就珍藏起来吧。如今,我站在30岁的渡口,能清晰地看到生命的流向,那遥远未来的终点其实一直树立在那。故人只能追忆,未来变数未知。有一天,我也会满脸沧桑,也会步履蹒跚,但我不会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不会温顺地任凭光明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