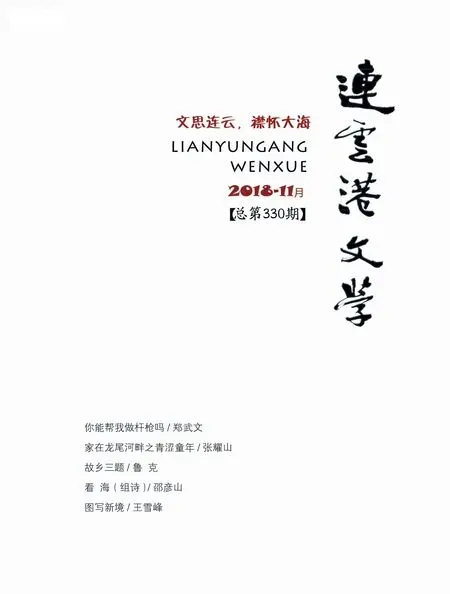你能帮我做杆枪吗
郑武文
我去找三孬焊刀子,三孬不在,他做门头的东屋门虚掩着。推开,静悄悄的,穿过东屋,里面就是他的院子,散乱生长着几丛暗红的月季和见缝插针冒出的杂草。土坯的正房和西南角的猪圈,与外面处处展现的繁华格格不入,好像穿越到了几十年前。我们有一个好面子的乡政府,临街的房子大都统一贴了瓷砖,最起码也刮了刮大白,涂上统一黄颜色的涂料,比如三孬的临街部分,掩盖着这背后的破旧和颓废。
沿着夹杂荒草的小径,我推开他北屋的门,一股潮湿的土腥气迎面扑来,屋子里很暗,适应了一下才看清摆设:无非一张床,一张小桌,一个橱子,橱子上一台黑白电视。我喊:“三哥,三哥!”我当面不敢叫他三孬。
三是排行,孬是他的性格特点。这小子从小就坏,偷瓜摸果,偷鸡摸狗,上树掏鸟蛋,别的孩子做过的调皮捣蛋的坏事他都做过,别人没做过的坏事他也做过,比如往老鼠身上泼上煤油,然后一根火柴点着,一团火苗在田野里呼呼乱跑,看着老鼠疼得“吱吱”乱叫,他哈哈大笑,还称作是“点天灯”。有几次还引着了田里的草垛,火苗熊熊燃烧。在柴草是主要燃料的年代,其损失也是巨大的。柴垛主人用脚后跟想也是三孬做的,可是没有证据,见着的人也不敢作证。就是有证据又能如何?一个柴垛不够他去蹲局子,下一步可就不一定是柴垛着火了。三孬的拿手好戏就是拔苗助长,他腰不疼腿不酸,几分钟的工夫,一行青苗就高了不少,太阳一照,软软地耷拉下身子,苗子没变样,其脊椎骨早已是断为两截。当然他还做过给麻雀扎瞎眼睛,看它在空中痛苦飞翔的缺德事,提起来就让杨村人不齿。
不但如此,三孬口德也不行。在杨村,成年人被叫乳名被认为是最大的侮辱。曾经有一个锔锅补盆的工匠在三孬门口吆喝生意,三孬说:“由此向里第四个门,有家大缸的脚坏了,到处找人补呢,你去给补补,别说我说的哈。”杨村的习惯,缸底叫“缸脚”。补缸的找进去,正好有个汉子站在院子里,就问:“你家有个大缸吗?”那人没看到补缸的工具,只见这么一个风里来雨里去饱经沧桑的老人,以为是远房的长辈,就点了点头。补缸的又问:“听说它的脚破了?”汉子又点点头。最近他下地用锄头把脚划破了,刚要抬起脚来给他看,补缸的已经飞快地跑出去把工具拿了进来,汉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一脚把工具给他踢倒了,大声吼:“是不是三孬使坏?”补缸的挺委屈,我哪知道三孬啊?一溜烟就跑了。这位乳名大刚的汉子还是三孬的本家二叔呢,气得把三孬好一顿臭骂。
三孬没人敢惹,大家都躲着,可是在心里恨着呢。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被媒人介绍的姑娘一打听,杨村人不自觉地都统一了口径。孤独终生也就成了他最好的结局。
北屋没有,我又去猪圈那地方喊。猪圈是兼顾厕所的。那几丛乱蓬蓬的月季张扬地伸展着腰肢,自己冒出来的植物和杂草则在每一个空隙爬行。院子南面有一棵柿子树,虽还不到寒秋,那柿子却啪嗒啪嗒往下落,摔到地上屎一样黄,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院子里被鞋子踩出几条不很明显的小路,到处乱哄哄、阴森森的。我刚朝着猪圈喊一声,跑出来一只大花猫,嘴里“喵喵”低吼,身子弓起来,身上的毛根根直立,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刺猬的模样,眼睛里满是敌意。看到它前腿弓后腿蹬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姿势,我急忙后退……
我在院子里的动静惊动了三孬北屋最东面一间里理发的小于。他家东间是硬山隔开的,临街开了一个门,不过对着院子有一个窗户。平时这窗户拉了一个窗帘,小于拉开窗帘喊我:“不在家。那猫刚生了小猫,护崽,你别让它抓着。”小于租他家这间屋理发,能够观察到院子里的情况,对猪圈那块看得也比较清楚。
我又从东屋穿回到街上,转到小于屋里,问小于:“三孬去哪儿了?”小于体态丰满,胸前波涛汹涌,又穿着一件暴露的衣服。听到我问,就坏坏地说:“老光棍,你说上哪?”我打趣说:“老光棍,院里就有这么好的美女,没必要出去吧?”
我自从自己买车床以后,需要的刀具比较多,尽管市场上有焊好的成品卖,可是质量总是没保证。而如果我自己上气焊的工具,造价挺高,最主要是我不会焊。三孬人不怎么的,干的活倒是挺细密。他再坏,给他送钱总不能往外赶,我就买刀杆子和合金刀头让他给焊,一次十来把。这个需要气焊,用铜焊条,硼砂做黏合剂,一把一把焊好需要大半个小时,还需要冷凉再拿走,等着的时间,我就到小于这里理发,一来二去,倒也都熟悉了。
小于从姑娘时候就理发,如今快三十了,见识形形色色的人,敢说形形色色的话,听到我这么说,咧开嘴哈哈大笑:“美女才更不能将就啊,总归有个底线,况且你妹我又不缺父爱。”
我坐到理发的椅子上,故作暧昧地说:“既然三孬不在家,就从小于的服务开始。”
小于先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细烟,说:“哥,先抽一支?”我看了看烟盒和烟,白盒,没商标,就说:“什么烟啊?不会。”小于低声说:“这可是好烟,一根的价格你理发的钱都不够,保你抽上一根神仙一样快乐。”我看着她裸露的前胸,哈哈笑着说:“我看着一座座山就神仙一样快乐。”
小于说:“免费请你不抽,就后悔吧。”一边说一边穿上工作服,在淋浴盆里放了水,手脚麻利地拖一个凳子放到下面的洗手盆旁,说:“来,先洗一下。”我过去坐下,把头伸到淋浴盆底下。小于说:“你就不知道三孬多讨厌,总是向我这屋里偷窥。你看,这南面窗户原先没有窗帘,我自己装的。你说看啥看,有事进来说就行,真是讨厌……”
洗好了头,我去椅子上坐下,小于问:“什么发型?”我说:“你是发型设计师,你的地盘你做主。”听到外面有动静,小于向我嘘一声,低声说:“可能回来了,大概是去弥河滩抓鱼喂猫了。真是讨厌,以前我还到他院里上厕所,现在弄一群猫,龇牙咧嘴的,被抓着可是要打狂犬疫苗的。”我说:“去他那厕所,再被猫抓破了屁股,喊一声三孬去帮忙,哈哈,你这是美女往野兽嘴上送啊。”
小于憋着气哈哈笑:“本姑娘可是吃肉的。你算不知道这个三孬有多抠,他每天的日常消费大概不会超过五块钱,顿顿馒头就咸菜,常年连身衣服也不买。头发长得披到肩膀了,才来理个发。我觉着他是房东,收别人十块要他五块总行吧?心疼的他啊,像剥皮一样。他就不想想,他做的是生意,我做的就不是生意了?”
我说:“你说人家光吃咸菜不对啊,他抓鱼的本事可是一流的,煎个鱼喝个小酒那也是挺美的。”小于说:“他倒是每天都去抓鱼,你知道他抓鱼做什么?喂猫。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我说:“三孬是抓住麻雀都要扎瞎眼的主,他会喜欢小动物?别逗了。”小于说:“就是怪,还养了一大群。有一次太多实在养不起了,用化肥袋子装起来,骑着三轮车跑了十几里路到弥河滩上游放生了,你猜怎么着?他回来的时候,那一群猫整整齐齐蹲坐在门口迎接他呢……”小于忘了小声说话,哈哈大笑。
我的头发理好,出来发现三孬正在摆弄我的刀子。我说:“隔行如隔山啊,你弄的角度不对,这样焊出来磨刀子就费力了。”我重新把刀头和刀杆位置摆好,问他:“去哪儿了?今天咋没锁门呢?这可不像你的风格。你以前出门甚至蹲在家里都把门锁的连个耗子都跑不进去,东屋里外两道锁,大门还把高门槛堵严。这次咋不怕人家把你的存折偷去了?”他抬起眼,斜斜地看我一下。突然问我:“你做的产品是装载机配件吧?生产装载机的厂子会不会往云南送货?”我说:“会啊,云南正在大开发,销量还不低。”三孬说:“我嫂子的弟弟在云南一个县里当副县长,我想去找找他,办点业务,可以坐着厂里的车去吗?你帮我打听打听。”
三孬有个本家哥哥也是一把年纪了说不到媳妇,后来跟着一群闯云南的人去买了个媳妇,不过精神有点问题,整天疯疯癫癫的。好处是那些精明的云南媳妇都是放鸽子的,一个个偷着跑了,她却一直在这里安安稳稳过日子,还给他哥生了一个精明的闺女。副县长应该能量很大,只是对于他所说的业务我没反应过来,况且三孬喜欢扯大旗,是把五块钱也称作一笔款子的人。就顺嘴说:“你要把维修业务拓展到云南去啊?大志向。”他咧了咧嘴,他很少笑,这算是笑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说:“小于可是说你总是从窗户里偷窥她。是不是有这么个春光灿烂的租户动了春心了。”三孬抬眼往小于那里看看,低声说:“她让你做神仙了?”我一怔,这个跟刚才小于说的话如出一辙啊!刚要问,三孬又说:“这个女人厉害,我亲眼看见李八子搂着她摸她……”我想原来是这么做神仙,就说:“人家租着你的房子,让你赚钱,你要帮她才行啊,做点生意要有回头客不容易,个别人动手动脚,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谁像你,为人民服务还耍大爷脾气,人家找人干活第一个不找你你还就不干了。”因为南面还有一个维修点,我亲眼见有一个维修轮胎的骑着自行车拿着轮胎去南面,结果南面的人不在,回来再找他,他就说干不了,愣是不给人家修。可恨之人必有难以理解之处。
三孬把头往我面前凑了凑,低声说:“你能帮我做杆枪吗?”我一怔:“做枪?你要去弥河打野鸭子吗?”三孬停下手中的活,后来干脆把焊把子关了,低声说:“我打黄鼬子。”黄鼬子就是黄鼠狼。在我们杨村一带,有两种动物不能惹:一种是家蛇,那是宅神,镇宅的,关系到风水财运。如果实在害怕这种动物,可以放生到村外野草里,这样也许并不影响运道。另一种就是黄鼬子,那是一种通彻天地的动物,亦正亦邪,它们是住在家里修行的,为了得道成仙。其实也确实奇怪,修行的黄鼬子如果不惹它,是不会去给鸡拜年的,彼此相安。但是如果惹了它,那么抱歉,不光是鸡,犬也不会宁。但是成精的黄鼬子如果看中了你的家,你却要给它腾地方,否则它还会用法力害人的,这就是传说中邪的地方。
看我沉默不语,三孬站起来,起身进屋。我不说话,其实是想枪这个东西政府控制可紧,一不小心派出所就会请去做客。三孬从屋里拿出打磨的铮亮的一截钢管,还鬼鬼祟祟让我进去看做好的木质枪托。他压低了声音:“我已经弄了差不多,可是精致部件还需要床子加工。车床、铣床、磨床你都有吗?”我从他那黑乎乎的东屋出来,打着哈哈:“这个可麻烦,你给我焊刀子别要钱,工夫互换,差不多了我就给你干。”
三孬脸色涨红:“亲兄弟明算账。我先收着你的钱,咱们各算各的。”我抬眼盯着三孬看,三孬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两鬓的头发斑白了,眼泡红肿,满脸皱纹,感觉与记忆中那个满嘴刻薄一脸坏相的人恍若两人。
三孬说:“我家院里有一窝黄鼬子,不只是一窝,足有二三十个,光是黑毛的就有五六个。”黄鼠狼的毛是黄色的,但是年龄大了就变黑了,据说也就快介于半仙之体了。三孬继续说:“每天夜里,它们就在院子里出操,排着队,从南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南面,有时候还在一个黑毛黄鼬子的带领下做体操。我知道哪一个是头,可是我冲不到它面前去,我还不等走到它跟前就会被别的黄鼬子包围。因此我需要一支枪,有了枪,我一枪就能干掉它”我的脊梁骨嗖嗖冒凉气,说:“可是它并没有惹你啊?”三孬说:“不惹?那是我的一群猫保护着我!它们在我身后,炸着毛,瞪着眼,时刻准备着为我拼命呢。”
我感觉这个话题太过荒诞,就催促他:“先焊刀子吧,我家里可是还等着用呢。”三孬重新把焊把子点燃,瞧了瞧小于那边,低声说:“有一次夜里八九点,一个面包车停在了小于门口,下来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我仔细看,可不就是一个黑毛黄鼬子?他贴近小于的窗户往里看,小于出来看了看,两人嘀咕了几句。小于四下瞅瞅没人,就把电动车推到屋里,锁上门,钻进了那个男人的面包车。”
我笑着问:“是她老公来接她吧?”三孬说:“她老公来过,我认识。这个绝对不是。而且他们没回家,直接去了河滩的草丛中,面包车在草丛中晃了一个小时。”我哈哈大笑:“那是人家情人啊!什么年代了?人家搞车震你去跟踪了?怪不得想去云南呢。你这真是想媳妇了。”看着我肆无忌惮地笑,三孬的嘴咧了咧,又朝小于那边努了努嘴,说:“真是黄鼬子,要害人呢!”
看到我的刀子已经焊得差不多了,家里的电话打来,说是有客户在家等我,我不等冷凉,放到车上一片残瓦,用钳子把刀子一把一把放上去,给三孬工钱。三孬说:“做枪的事,别忘了。”我说:“这是个精细东西,你要给图纸啊,没图纸,我无从下手。”三孬没说话,茫然抬头,看着我驾车远去。我心里呵呵一笑,我傻呀,做枪?那是会坐牢的。不要说就我的技术根本做不了,能做也不敢做,做点小生意不容易,我可不想自己毁了。
大约二十天后,我又去找小于理发。小于的理发馆有几个染着黄头发的青年,却也没理发,看到我来就走了。小于神秘兮兮跟我说:“你知道吗?三孬被刘大宝打了一顿。”刘大宝是我们村的村主任,年轻的时候也是道上的人,剃光头、文身,左青龙右白虎的,胳膊上还用烟头烫出一个“忍”字,可却是很少忍得住,在村里横行霸道。可现在当了村主任,基本能忍住了。一个是现在治安好了,派出所每天学习文件打击村痞路霸,不大敢与这些人称兄道弟了,再则当干部了,要好好表现,村主任可是人民群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能把三孬打一顿,那肯定是占了天大的情理,让别人说不出啥闲话来。果然,我问:“咋回事啊?”小于说:“还能咋回事?三孬又去给刘大宝拔苗助长了呗。”我说:“这个三孬,一把年纪了还没数,做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该打。”小于说:“好几天了,没出门口呢,就靠他一个在近的侄子给送点饭进去。”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问小于:“你从这南窗户看出去,有没有发现三孬院子里有黄鼬子?”小于说:“黄鼬子没有。就是他那十来只猫,开春的时候叫的那个瘆人。”我看着小于那裸露的一片雪白的胸,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三孬可是说有个黄鼬子精用面包车拉着你去河滩草丛里搞车震呢。”小于的脸一红,尴尬得笑了笑,说:“这个三孬,活该被打,真是一片坏心眼,偷偷跟踪我,还说是去网鱼呢。不过那次多亏他,我们的车陷进泥里出不来了,他拿着个渔网钻出来,说是网鱼经过,好歹帮我们把车推出来,弄了一身泥。”我说:“这个黄鼬子精是谁啊?我认识吗?”小于的眼一白:“跟你有关系吗?别再打搅我啊,再打搅我给你剃成光头了,这一推子又往上了。”
理完发,我去三孬屋里看了看,一推门一股巨大的臊臭味,显然是屙尿都在屋里。屋子里很暗,三孬倒无大碍,我说:“听说此次战役失败告终?胜败乃兵家常事,实在不行拿出对付老鼠麻雀的本事来,看谁还敢惹你?”三孬喃喃说:“那都是害虫,四害之一。”又问我:“做枪的事,别忘了。黄鼬子精,越来越猖狂了。”
我说:“好好好,你什么时候正常营业啊?我的刀子可是快用完了。”
以后一段时间,三孬到我的厂子里找过我几次,不是脸上有瘀青,就是走路一瘸一拐的,无非是问我做枪的事。邻居总是告诫我:“这个人少打交道,可是坏,跟他交往就像农夫与蛇,不小心就会被咬着。”看着这么一个像是风烛残年的老头,是蛇也是一条秋后的蛇了。可我也不愿惹是非,就告诉他:“你也看到了,我很忙,订单都做不出来,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你想和我合作就要等,等个三月两月或者一年半载,等我不忙了再说吧。要不你就去找别人,没办法啊!”每次三孬都失望地走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已经进入了腊月,街上零零散散响起了鞭炮声。我因为都换了数控刀子,刀杆和刀头都是用螺丝拧住的,所以也很久没找三孬去焊刀子了,有次急需一把焊接刀,我也是去买的成品。我不愿意听他没完没了的叨叨,更不想惹事。派出所是好惹的?造枪?我可只想过安稳的日子。
腊八那天,出奇的冷,滴水成冰,“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西北烈风呼呼乱叫,我不想出去,也不想干活,车间里没有保暖设备,冻得手脚像猫咬,杯子里的水都成了石冻冻。我就在屋里喝茶看电视,我的厂在村东南两三里路处,突然听到村里一阵喧哗,出来门口一看,北面涌着股股浓烟,空气中一股烧焦的味道。
村里一定失火了!这可是大事,我穿上棉袄,拿了一张铁锨就去救火。
远远看见,烧的就是三孬的房子,大家远远围着,却没人靠前。村主任刘大宝比比画画在说着什么,近了才弄明白:原来是三孬自己在屋里用火药做子弹,不慎爆炸,如今火药多少尚不能确定,而且大火迅速蔓延到了处于院子东南方的他的门头房,门头房里有两个液化气罐两个氧气瓶,都是易爆物品。三孬的房顶是麦草的,里面用的木质大梁和檩条,借着火势迅速燃烧。好在周围邻居都是水泥浇制屋顶,并不易引燃。人命最金贵,刘大宝的建议是正确的,迅速获得了其他村干部的赞同,围成一圈不让任何人靠近救火。
十几分钟后,液化气罐和氧气瓶果然爆炸,掀起一片带着火星的麦草飞向空中,如同放了一个巨大的烟花……
又等了大半小时,救火车狂叫着赶来,救灭了余火。半条大街流淌着黑乎乎的脏水,周围建筑也蒙上了一些脏兮兮的灰烬。三孬的房子只剩下几堵泥坯墙,和它们连在一起的小于的理发店也全着完了,门子没有了,椅子烧焦了,那面大镜子照着街上探头探脑往里张望的人们。
刘大宝用一根棍子挑出了三孬烧焦的尸体,还有他养着的那十几具猫的尸体。怪了,猫是多灵巧的动物?怎么会没跑出来呢?难不成真像三孬说的:关键时候能帮他的只有他的猫?
转过年来,乡里又要求新农村建设,重新粉刷公路两边的墙壁,清理杂物,整修路面。三孬的破院子就在公路边上,正好是杨村的脸面所在,三孬又是光棍一条,村里要求地基充公。喇叭里下了几次通知,谁愿意要的可以去村委报名,据说去了几个,刘大宝都跟他们谈了话,大家也就都对这不祥之地不感兴趣了。最后还是刘大宝勉为其难,接收了这个烂摊子,几个月就沿街盖起一溜门头房,贴了瓷砖,安了铝合金大窗户,卷帘门,很现代、很气派。这几年刘大宝不工不商,看来底货还不少。
几个月后,门头房最北面的一间,小于的理发店重新开业了。我的头发也正好长了,就推开安装着磨砂玻璃的门,小于正在和刘大宝拉拉扯扯打情骂俏,看着我进来,两人收敛了一下,我说:“房东正在和房客交流感情呢?”刘大宝看我一眼,对着小于说:“我先走了啊,晚上溜冰别忘了……”
新房子又亮堂又宽敞,而且里面还有了一个专做按摩的暗间。天气又暖和了,小于穿了更暴露的衣服,两个乳房呼之欲出的样子,下面则是很短的短裙,漏出雪白的大腿,脸上也是浓妆艳抹,戴了假睫毛,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眼角画得很长,有一种狐狸的妩媚。
她用裸露的胳膊蹭了我一下,说:“发什么呆啊?”我说:“现在是阳春三月花儿开,刘大宝傻X啊,约你去溜冰?”小于哈哈笑:“白天不懂夜的黑,让你做神仙你又没口福。”我又问她:“三孬着火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当时我还四处找你。”小于说:“我那天正好没来。”我说:“没来是有事吗?”小于顿了顿,说:“没事,就是不想来。”我说:“腊月,可是最忙的时候,人家都加班呢。”小于的脸红了。
突然想起什么,我瞪着小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听到传言:有人从你原先的窗户里往三孬院子里放了一只点了天灯的老鼠……”小于勃然变色:“这是谁造谣?证据呢?”
我说:“你们是黄鼬子精吧?我在帮着三孬做枪呢。”我用手指做出了一个枪的样子,对着小于“叭”了一声,反身推开门,走了。
几个月后,几个警察突然钻进我的厂子,一个瘦子问我:“我们找你调查点事,请配合我们。”我说:“不用调查,我没做枪,啥也没做。”警察怔了怔,说:“我们是调查一件你村刘大宝贩毒案,有人反映你知道一些情况……”我说:“不是我不配合,请回吧,我真的啥也不知道……你看我的屋顶,是PVC复合板的,不抗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