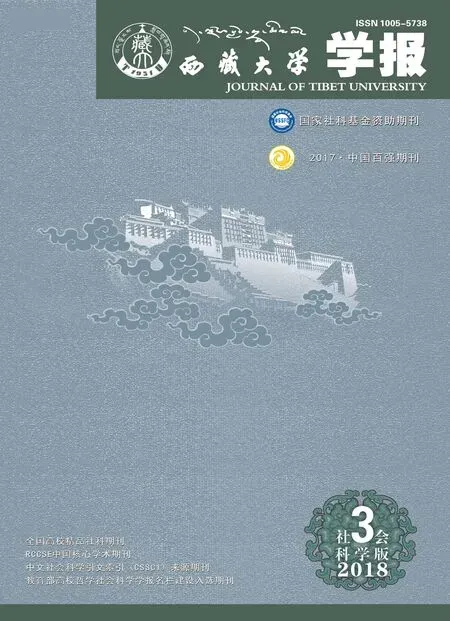光绪石印本《西藏通览》研究
王丹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武汉 430072)
一、《西藏通览》概况
(一)成书经过
创作于20世纪初的《西藏通览》(以下简称《通览》)一书,是由我国学者在日本东京发现后带回国并翻译成中文印发的一部方志。此书被收录在《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史料汇编》中,由于经过多方转手修订,其成书概况可以根据题识和先后序言中的内容来考察。书名下有题识:“桐城方旭署”。两篇序文:第一篇作者《自序》,文末题写时间地点“明治丙午七月著者识于四谷之寓所”;第二篇《序》的文末题有时间和序文作者“明治四十年七月中旬步兵少佐黑泽主一郎”。两篇《凡例》:第一篇《凡例》列出成书原因、不足和所引用的文献,最后对助力编纂的“黑泽主一郎及佐佐木一也”表示感谢;第二篇题为《译印西藏通览凡例》。前两篇《序》和第一篇《凡例》为日方创作时间、地点和编修者信息,《译印西藏通览凡例》则交代译本的来源:“在日京购得即觅留学界为译出……发印”,文末有题识“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有二月井研吴季昌权奇甫识”,正文标题下题“日本陆军步兵大尉山县初男编著、日本陆军步兵少佐三原辰次校阅”。故收入《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史料汇编》的《通览》由山县初男在明治丙午七月(1903年)写于日本四谷,黑泽主一郎于明治四十年七月中旬(1908年)作序,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十有二月,吴季昌、权奇甫从日本购得,并组织翻译、编写《凡例》。书名下,签署名字的方旭在《通览》的翻译发行活动中所做的具体工作从《序》和《凡例》中并未得见。方旭,字鹤斋,晚号鹤叟,又号鹤侪,方苞后裔,安徽桐城人,清末进士,清末曾赴日本视察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任夔州府代理知府,能诗、善书、工画,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方旭因在地方勤政有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四川省学务处提调身份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期间,孜孜研求,回到四川后任学务公所总办,不久署理提学使。”[1]方旭在新学改革上致力颇深,他强调要兴办学堂,提倡“以开风气,敦实业,造成明毅忠爱之人格为主义”[2]。吴季昌是与方旭同时期的四川教育家,为四川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在有限的资料中看到,他积极提倡教育改革,与同盟会成员有所接触。权奇甫其人事迹不见记载,与吴季昌并见题跋,应当也是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故此书当是从日本购得后,由方旭、吴季昌、权奇甫等人在蜀中组织翻译印刷。编著者山县初男和审阅者三原辰次二人都来自日本军方。
(二)文献来源
在阅读《通览》时会发现,作者山县初男对西藏风物、地理了然于胸,原因在于他参考了大量的中国本土方志,同时也借鉴了日本国内的研究成果。他列出了参考书目,分为两类:“一主要参考书:《西藏纪》清人著(著者不详)、《大清全帝图》三省堂、《清国通商宗览》日清贸易研究所、《西藏图考》黄寿菩;二可为参考者用但未得见:《藏行纪程》杜昌丁、《卫藏图识》盛绳祖、《西藏志》果亲王、《一部图》帷乍了、《西招图略》松文清、《一统舆图》胡文忠。”[3]由此可知他是在中国学者、官员等所作的藏志基础上进行资料重组。其中,后几种书未得见,但都是清代影响力巨大的史地著作。若以《西藏图考》为例来考察《通览》的参考文献,《西藏图考》是清光绪年间黄沛翘所纂的平目体藏志,其编目次序为:西藏全图附小引、沿边图附说、西招原图附说、乍丫图附说、西藏源流考、续审隘篇、内地程站考、西藏程站考诗附、诸路程站附考、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名山大川详考、藏事续考、艺文考[4]。黄沛翘在《例言》中说:“修边徼书莫要于图,而莫难于图,西藏文字不同,若非修省志者具有县府底稿之可采”[5],故他在修纂《西藏图考》时以图入志,注重地图绘制。后人对此书有较高评价,尤其称赞其地图绘制之功:“博采群书,详加幕定叙次颇有条理,考证亦多精核。地理山川、绘图系说,尤清眉目。”再反观山县初男《通览》中对西藏地理地貌详尽备至的描述,可知这些本土文献对这部书的作用。他甚至在十五章(交通)中,罗列了境内从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11条入藏路线;境外从印度、锡金、克什米尔等地7条入藏路线,而这种全方位的视角,显然来自于中国本土人之手。黄沛翘《西藏图考》刚出版不久,就被山县初男纳入了参考书目之中,并详加利用,可见他对中国西藏史地著作保持着高度关注。丁士彬在为《西藏图考》所作的《序》中表达了著书目的:“英圭黎常思开通藏路以达中国……然则今日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害数倍,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之急务也。”[6]。他指出由于英国屡次进藏,加之西藏局势日趋严峻,需加紧对西藏地理之考察。本是为了防御外敌入藏所写的一部应急之书,却被外国军队拿来作为进入中国的指南针。
(三)编纂目的
山县初男在《自序》中说:“伴世界之进步而交通四达。抟抟地球,何处无文明国人调查探考之足迹?所谓秘密国者,固不许存在,此自然趋势之内也。夫西藏非素持锁国主义者乎?于河山天险之中,别成一特造之乾坤,亦自夸称为佛陀之天国。”以文明进步为由头,以世界趋势为借口,目标锁住西藏。又说:“英阳枯哈子达磅达大佐之远征军队,无端而撤其帐幕,抉其藩篱。藐兹片壤,今后将为大陆竞争之角逐场,加之其国富于金银珠玉、宗教之盛,风物之奇,无一不为学界研究之好材料。”讲述了英军前期对西藏的入侵,以失败而归。指出西藏即将成为清朝内陆利益角逐之地,将目标锁定西藏的另一个理由是西藏富于矿藏。如果说山县初男在《自序》中还打着文明传播、文化研究的旗号,紧接其后的黑泽主一郎的《西藏通览序》则显得更加直接:“忧患四逼急甚,燃眉而不自知觉者,非西藏耶?英国之奇杰阳枯帕司德者,抱盖世之雄,拥提远征队捣入中央之国都,拔去闭关之锁钥,即被蹂躏以来,而佛国灵皋遂为世界视线之集注点。西力东压之大势,如滔天激浪奔涌而来。藐兹蕃民乏力摈拄其深闭固藏之宝库。亦将变为群虎奔噬之通衢之倾向。”讲述了英国对西藏的入侵事实和西藏成为列强逐利之地,直指西藏紧迫之局势。“虽西藏素在清国领域之内,然僻处西隅,清政府鞭长莫及,而蒙昧蛮野之藏民除虔奉喇嘛教以外,曾无有就他事而研究之者。”此处讲到西藏地处边疆,清政府也鞭长莫及,本地百姓对即将发生的局面也不甚了解。因此,他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假令扶植其文运,开拓其富源,岂独东洋经济发展之上一利薮也乎?然则就其真相堪破而讨论之,查覆其国势判断其将来,供经世之论。”即以文明开化为借口,展露入侵西藏之手段,掠夺西藏之物产,以资助日本国内的经济。在这前后两篇序文中,日人的企图昭然若揭。再看吴季昌《译印〈西藏通览〉凡例》,说“是书在日京购得即觅留学界为译出。”“原书各图均系电印,蜀中印刷业未发达仅有石印,今即以石印出之。”“原书译出地名人名不易分辨。”“原书附有藏文字母及拼音今译成汉文,请深于藏文者核校。”“原书之中英日藏猓猡语音差别表,以石印出之。”“是书为近今新出,其分类研究足供教课书用,阅者幸勿忽睹。”六条中,五条是讲《通览》的来源、体例,只有最后一条提到翻译印行此书的目的:以之为学校新学科目分类的教参资料。当时,方旭、吴季昌等人正是在蜀中大力提倡教育改革的优秀学人。另外,除了在《序言》中透漏的信息外,在章节分布上也可以清楚地显示著书目的:风俗16节、政体11节、兵制12节、贸易4节、物产4节;交通有18条入藏路线;都邑记有14个城市。第二章全文描写西藏的探险者和西藏与英美俄的关系。这些数字无一不述说着著述意图,即详细考察西藏经济、军事、交通、宗教和国际关系等,以备日本军方入侵之资。
通过以上两组序言的对照,以及章节分布数据统计,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岌岌可危的边疆外患处境,先觉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巨浪冲袭下所做出的积极的反应,以此可瞥见西学浪潮下中国教育改革之一角。
二、《西藏通览》内容和体例创新
从内容和编纂方法上看,《通览》是记载西藏地理、人文、宗教、农业、军事、历史、时局的一部别于传统方志的新体方志。之所以称之为新体方志,则是因为其分类编目增设了现代类目。此书分上、下两编,其分类结构见表1。

表1 上、下两编,其分类结构
由表1可知,《通览》维持了传统方志中的地理、历史、都邑等固有类目,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现代新类目:人种、政体、语言文字、教育、贸易以及对外关系。在子类目下增入了植物、动物、矿产、贸易输入和输出等。在上下两编内容分布安排上,也体现出了和传统方志的不同,它不同于以往中国人的重史观念,开篇叙述史料,而是将史放在了第二编,而且以一小节来简单地论述从唐代到清代的西藏史,其后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第一编占据本书的大部分,主要是自然、地理、风物、军事、宗教、矿产、交通等实用性内容。《通览》在内容上淡化甚至取消了传统史书中人物志、艺文志的内容,而新增加了与时事、民生相关的条目。《通览》中的新类目以及它不同于以往方志风格的篇幅建构,体现了20世纪初史地学在西方知识风潮下发生的学科分类体系的转变。“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7]它在提倡新史学的历史环境下,被转译到中国,本身就是被当作一种新史学方法来借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方志编纂方法,在面对现代知识体系时,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样貌。《通览》正体现了这一过渡时期的痕迹,从类目上增加了现代学科分类类目,同时,也保留了传统内容及文言表达方式。但同时新类目的运用会出现各种复杂难题,在《通览》中也存在条目难以明了的情况。如:第五章“风俗”类却将“职业”“医药”“历法”归入其中。第十章“兵制”类将“边疆要地”归入其中。当然这在新旧交替时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依然可以由此窥见20世纪初方志编纂实践中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已经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及自然科学化。
三、《西藏通览》之史料价值
《通览》不仅记录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城市、行政区域及交通信息,而且详细记载了藏区的职业、衣冠、饮食、家屋、婚姻、丧葬、占卜、医药、宴会、哈达、典型动物、植物、物产、寺庙、边境贸易往来、语言文字等。虽然由于受到编纂目的局限,记载不是面面俱到,但依然可以从其或详或略的记载中看出晚清西藏的大体情况,体现出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民族史、宗教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史料价值
在政体变迁、宗教权力迁移等方面,“西藏自古政教一致,国君即喇嘛法王,清代即平其地,因置驻藏大臣,凡文武黜陟及其他藏地事物,皆得干涉以分喇嘛法王权力。”①参见: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史料汇编·第三辑·西藏通览[M](以下简称《通览》).北京:线装书局,2015:1049.“达赖喇嘛在喇嘛僧中有宗教上无限威力,至大至高,为众庶所尊重……然其政治上权力每被制于驻藏大臣,不能专生杀予夺之权也。”②参见《通览》,2015:1053.“驻藏大臣之始,当时第以维持秩序为主,尚不至于干涉番人政治,及乾隆中叶渐居于监督位置,至于今日,总握藏中政权。”③参见《通览》,2015:1089.根据以上材料,清政府从中期开始不断调整对藏策略,保持达赖喇嘛在宗教上至高权力外,通过设立驻藏大臣来干涉西藏政事活动,逐渐形成政教分离的局面。
在各类盛大宗教活动方面,《通览》记载了从正月至十二月的各类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集娱乐和宗教信仰于一体,是上至达赖喇嘛,下至普通藏民全民狂欢。“正月元日,土人着红绿衣服为跳舞及其他种种技艺,达赖喇嘛坐高殿观之,大小官吏皆入布达拉宫。”出席阵容庞大,舞台搭建奢华。“二月十七日举行宗教上之舜踏祭,初则有人执旗二十四本翳舞台出……右握金刚杵左持铃,披黄冠……中庭长约三百码,幅约百五十码,四周有露台,数层高……大喇嘛席在第三号台之上层,后藏贵族头领等……第四号台则设席以坐蒙古巡礼及日喀则绅商……次出者为四天王,次出者为天王子六十余人。”④参见《通览》,2015:1025.除了各种“驱魔”祭祀表演,还有盛大的晒宝会。“三月一日,陈列达赖喇嘛所有器宝物于外,许士庶纵览,宝物中最惊人目者为一大佛像,画长几三十丈余,复有达赖袈裟一袭为历代所遗,皆以珍珠穿成,大者如人指光华灿烂,夺人视线真稀世之物也,此日观者不下六七万。”⑤参见《通览》,2015:1033.
社会等级制度及税制方面,“西藏人社会阶级分上中下三等。”⑥参见《通览》,2015:1093.“藏人纳税率以物品,达赖、班禅直辖地方及各庄田主所纳物以麦豆、小麦、荞麦、牛油、干乳等为主,有税关地方则所纳为珊瑚、珠宝石、布类、绢、罗纱、干葡桃、干桃、干枣……最为奇特者,则达赖班禅所用收核牛油衡量约二十种,收量谷类升斗亦有三十余种,探其何故如是?则收税时酌量纳者种类,或用其大者,或用其小者。譬如,法王出身地方人民或与达官大吏声气互通者俱用小量……”⑦参见《通览》,2015:1092.
西藏官制变迁方面,“前藏官吏混用僧俗为之,后藏则俱用喇嘛僧人,组织极为简单始,仅有官制形状而已。”⑧参见《通览》,2015:1088.体现了西藏后期宗教权力的收拢。
对外关系方面,“西藏输入重要物品为木棉类、毛织物类、毛锦杂织、珊瑚、玉、蜀黍、燐寸、绢织物、烟草、阳伞、毛皮、茶等。其内燐寸(洋火柴)、洋伞、日本制造最多……自四川方面输入者则为茶砖哈达……自云南输入者则为茶米……自甘肃新疆输入者则为茶、宝石……自克什米尔方面输入者则为砂糖干果……自尼泊尔方面输入者为米、铁……自西金之亚东方面输入者则为西洋杂货、西洋毛织物、日本杂货。”⑨参见《通览》,2015:1130-1131.“西藏输出物品一为……二曰麝香……三曰砂金……四曰红花……五橄榄……六曰紫草……肉桂、黑白香、佛像、嘣纱、盐。”⑩参见《通览》,2015:1133-1134.由此可见,西藏并不是一味地封闭自守,完全不与外界互通,它与国内外长期保持着相当的贸易往来。主要从国内外输入茶、糖等,输出物主要是羊毛、药材和金矿。由于大量的茶叶消耗,英国人通过印度对西藏进行大量的茶叶输入,几乎控制了西藏的贸易,在藏区形成了可以和内地商业抗衡的力量。这也是在西藏经济贸易史上值得关注的地方。
另外,书后附图主要有:西藏之男女图兵和兵卒图、老人图、羊牛、西北部藏家畜牧之生活状态、西藏人之宿营、狩犁牛用犬、西藏人之祈祷所、西藏人之天幕、喜马拉雅东麓、土人穴居之所、西藏兵所带武器等,图文并茂地展现了西藏高辨识度的特色风物。“历史的解释的价值是与我们对有关事件的知识所了解的准确和详细程度成正比的”[8],以上资料的保存,为西藏民族史、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二)近代史、国际关系史价值
《通览》保存了关于西藏历史大事的资料,为近代史、边疆区域史研究提供可靠助力。
西藏之领土归属。《通览·史略》记载了从唐到清代史志关于西藏的序跋,主要有《附唐吐蕃传拔萃》《蒙古源流考拔萃》《五代史吐蕃拔萃》《四川通志拔萃》《元史百官志拔萃》《明外史西蕃拔萃》《明外史传拔萃》《清圣武记拔萃》《清与藏之关系年史》《康輶纪行拔萃》以及《西藏纪拔萃》。从这些序跋中可以看到西藏一直就是中国的领土。
法、日、英、俄在西藏的探查侵略活动及其手段。《西藏探险者》一节中作者描述了十一位进入西藏的探险者,有法、俄、印、英的传教士、学者、官员、军队等,前赴后继前往西藏进行探险、调研、传教、贸易及军事活动。由此可见,晚清欧美传教士在西藏活动之频繁,他们在布道传教的过程中,扮演着为侵略者传递信息的角色。
清政府在西藏事务上对俄、英的妥协策略。《西藏与露国》(此处“露国”即俄国)记载,“清国若国家濒于危急则以西藏之权利让与俄国,俄国应以其代偿尽力于清国之保全;清国当内乱若以自力不能勘定之时,俄国应派兵代清国勘定之;俄国应置官府于西藏,代清国管理西藏事务。”《西藏与英国》记载,“《天津条约》其特别条款中含有清国政府允许英国派遣使节游历西藏一条,此后英之图实行此规定者无日或忘。印度民政厅吏员可儿曼马苛伦得本国政府许可欲游拉萨,向清政府请求旅行护照,马苛伦从北京、伦敦间两面周旋后,卒由清国总理衙门发给旅行护照并得种种利益之许可……藏人闻之极力反对彼等之人入藏,有宁以干戈相见而不辞之势,于是清政府处此两难。”
藏英战争缘由及战败原因。“英灭西金,复遣马苛伦入藏,华人有识者,方窃窃然忧其祸之将及于藏,而藏人见马氏之不能达其目的也,反谓英人易与,一八八七年拯救西金,入其国内林东之地建城设堡。翌年三月,英出兵攻之,藏兵败走。”①参见《通览》,2015:1397.“林东者……道路险恶、空气稀薄,人马有登者数步一休,藏兵据此为营,然卒见败于英人者,实由武器恶劣之故。”②参见《通览》,2015:1398.由于参与锡金和英国的战争,西藏被英国攻击。由于武器的落后导致了藏军的失败。
达赖出走青海。“一千五百西藏人拔刀突袭英军……其不足当英军之新式利炮,甫一交锋全军遂溃死伤七百,余悉遁走,英军追奔逐北入江孜乃止,拉萨驻藏大臣通牒请斥达赖喇嘛速委任西藏全权官吏来开谈判,此时达赖尚欲依赖俄国,不允与英国开交涉……英军至陆续入前藏者其总数已达四千六百人,并运到巨炮十二门,藏人知事已无济乃扬降幡……达赖喇嘛之亲自谕难为诺否之确答,至是其炮垒附近汲汲皇皇有益修战备之状,是为最后休战之五日正午时也,西藏使者卒未就议和一事作何等回答……英军沿途所经接炮火……西藏讲和使者来言,拉萨为彼国纯然之宗教府,非商议国事之地,请将军队引还江孜在该地会商,大佐鉴于前言……振军队直捣巢穴……达拉萨目的地,而达赖喇嘛已于是日先出布达拉宫,走青海方面矣。”③参见《通览》,2015:1418-1421.此处,记录了英军二次侵藏,清政府妥协议和,而达赖喇嘛“依赖”俄国,与英军斡旋拖延,最后抵抗失败后出走青海的史实。
另外,还有清政府就西藏事宜与英国、缅甸、英属印度签订一系列条约,主要有《关于缅甸西藏条约》《关于印度条约》《阳枯哈司磅达大佐之远征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这些条约内容从多方面记载了法国宗教渗透、日本多次入藏、英人以各种理由屡次进犯、俄国在蒙古及西藏的宗教和军事活动等历史大事件。从以上条约附录里呈现出的英国和缅甸、缅甸与西藏、印度和英国、印度和西藏、西藏和清政府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里各国彼此之间、各国和晚清政府之间的利益斡旋与博弈。晚清政府群狼环伺、内忧外患的危机场面跃然眼前。《通览》保留了清政府陷入严重边防危机的历史记载,同时也说明了它自身正是这种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四、《通览》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彭红升在《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9]中将清代藏志的产生划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康末乾初(1720—1750年);第二个时期为乾隆末至道光末年(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三个时期为19世纪末至1945年。每一时期藏志的产生都与时代环境和学术风气有莫大干系。《通览》从1903年山县初男在日本完成到1908年被方旭、吴季昌等人组织翻译印行,正处于第三批藏志涌现的时间。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后,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治理下,列强虎视眈眈,而这个时期的清政府国势衰微,只能任人鱼肉。英国屡次进藏,和俄国在西藏进行竞争而后互相勾结,以西藏和内地的其他利益进行置换,由宗教活动入手,从进藏游历探险升级到通商贸易,挑起西藏内部的矛盾和汉藏关系,意图割裂领土,侵占藏区资源,获取在内地利益最大化,严重危害了我国领土主权和西藏的民族利益。西藏这一世外桃源就此被迫卷入近代化的浪潮中。
当时社会危机加剧,在内忧外患中,国人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于是,在这个时期,前往欧美和日本学习的留学生逐年增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展,在近代超过了中国,由于日本和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也非常多。“1896年3月底清朝首次派遣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1899年增加到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三千名,到了1906年竟然达一、二万名之多。据实藤惠秀的研究结果,1906年留日学者实数为八千名左右。这些留学生不仅有官费,而且有自费,不仅有维新派,而且有革命派。”[10]他们接受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后,回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爱国救亡活动,或提倡教育改革、文化改革,启发民智,或大刀阔斧致力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新的政体等。其中有一部分留学生开始了日书中译行动,通过介绍西学知识,提高民众之觉悟。潘喜颜《清末历史译作研究1901—1911》指出:“1900年前承担起译介和输入西方史学中介角色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可以视为‘西方传教士主译时期’。而1900年以后,西史译介的主力是留日学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主译时期’”[11]。《通览》正是由吴季昌去日本学习时购回中国,负责翻译的也是日本留学生。这一时期,留学生成为主流翻译群体,改变了西方传教士为翻译传播主体的现状,成为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篇章。此时中国官方、民间自发的向西方学习,改变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主体地位,中国文化交流拉开了积极面向现代化的序幕。谭汝谦指出:“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文学书,而中国译日本书却达到了958种,内容包括了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文学,也包括了地质生物、化学、物理,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近代知识。”[12]大量的日译书出现在晚清西学思潮中,而“这些思潮都带着浓厚的群体意识,期望把中国自此一危机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着一个未来的中国,并追寻通向那目标的途径。”[13]
时代巨变,中西思想发生碰撞,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也在此时走向高潮,《通览》“中—日—中”的来回转译形式和新类目编纂方法也恰好是思想史、文化史发展变迁的见证。
结语
《通览》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本土的西藏方志,另外一部分是来自欧美探险者和日本本国西藏探查者的日记。同时,它又是军方进行西藏侵略活动的指南针,所以,其中记载之材料真实可靠。它成书于新旧鼎革之际,在东西洋思想冲击下,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觉醒,积极吸收西学思想,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促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走上转型之路。因此,《通览》在方志编纂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