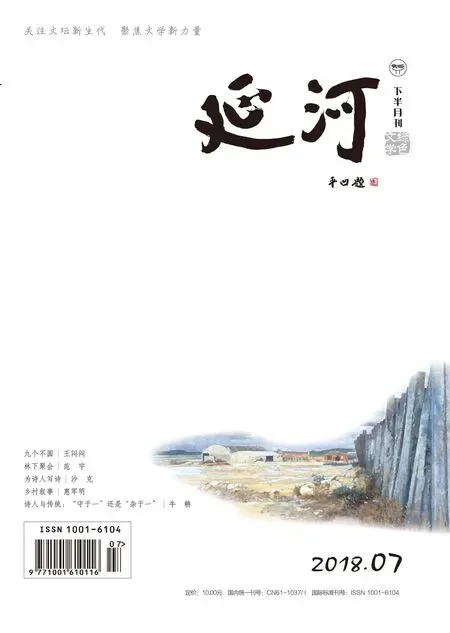诗人与传统:“守于一”还是“杂于一”
牛 耕
记得诗人长征在《我的诗观》中,有过这样一段表述:“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回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就在传统里;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忘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正在遗忘着。”这段表述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传统在我们每个诗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我们和传统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刻意强调的关系,不论这种“刻意强调”,是从“怎样才能回到”的角度正向地提出,还是从“怎样才能忘记”的角度反向地述及。
由此我想到,提倡“回归传统”的保守派和提倡“反叛传统”的先锋派,很多时候看似观点相逆甚或不共戴天,但骨子里的东西往往却又惊人地相似——都是拿着“传统”当招牌的“刻意强调派”,“传统”在他们那里,差不多都是可以方便地抛来掷去、穿来脱去的行李或衣装。
传统既然流淌在每个诗人的血液里,那么,每个诗人在写作中对于传统的呈现,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既不需要刻意地予以强调,也不需要刻意地予以淡化。事实上,在每个诗人的血液里,传统是一种活着的心理结构,其核心,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历史的意识”:
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的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依据艾略特的揭示,我们的“回归传统”,应该是归拢到一种深刻而宽广的“历史的意识”中去,而不是简单地拟古或者复古(比如,用格律体写出比杜甫《登高》更高的《登高》,或者比元白体更白的元白体)。那样的话,就背离了“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拆解了“自己和当代的关系”。对此,艾略特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现在进一步来更明白地解释诗人对于过去的关系:他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完全靠私自崇拜一两个作家来训练自己,也不能完全靠特别喜欢的某一时期来训练自己。”因此,对于一个正在写作的中国诗人而言,回到李杜或者重返盛唐,其实对他解决自身写作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或者说这是一件非常次要的事情。
为了方便,可以用举证法说明问题。就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欧阳江河为例吧(也许不一定恰当,暂且如此了)。欧阳江河以其玄学智性的分析性的系列诗作,开拓了中国现代诗新的经验类型和风格类型,正式出版物如《事物的眼泪》《如此博学的饥饿》等,均以“作为诗人,欧阳江河的写作强调思辨上的奇崛复杂及语言上的异质混成,强调个人经验与公共现实的深度联系”,来给出其诗学特征。按我个人的观察,欧阳江河的诗,不仅对大众读者,就是对于很多写现代诗的小众读者(包括我在内),也是极其陌生、极其晦涩、极其深奥、极其难懂的一族——即便有像敬文东一行等素质极高的专业批评家的深入开掘和不懈引领,“读懂”欧阳江河,对大多数人甚至是对大多数诗人而言也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如此看来,欧阳江河的诗,很像某些西化的翻译体诗歌,给人的观感大体是语言繁琐,表述晦涩,注重深度而不注重美感之类的。显然,这是无法回归到汉语传统的辖域里去的。也许,我们可以把此理解成欧阳江河不了解传统(就像一些人认为穆旦对于古典的无知一样)所自然形成的隔膜。然而,稍微举出两个例子,也许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其一,在一次访谈中,欧阳江河谈到自己的少年时期,曾经背诵过的古诗达到5000多首,如果加上熟记但没背过,读过但没熟记的,欧阳江河涉猎古诗之深之广是足可以傲视群雄的。其二,欧阳江河是诗人中的书法家,其书法在书画市场奇货可居,并且经常卖给日本等国外收藏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诗歌界里,我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讲,我的书法是最好的,我比最好的还不知道好多少。”(《南都周刊》访谈)书法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积蕴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欧阳江河精湛的书法技艺背后,一定也相应蕴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透理解。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些嚷嚷着要“回归汉语传统”的人群中,有几个人身上的传统文化积蕴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欧阳江河的写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西之间,是深思熟虑、相融相生、彼此打开的。其写作的基点之一是“为了获得现实感”,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诗歌中的现实感如果不是在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历史参照中确立起来的,就有可能是急躁的,时过境迁的”。似乎和西川所表述的“历史的个人化”相互叠映,也和前述艾略特的“历史的意识”彼此勾连,是一种“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他所创造的兼具分析性和玄学特征的诗歌语言,是一种在“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中深刻洞察、处理和回应现代性难题的语言。同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所采用的是一种介于书面正式用语和口头实际用语之间的中间语言,它引人注目的灵活性主要来自于对借入词语(即语言变体)的使用。这种使用就是语码转换,它从表面上看是即兴的、不加辨认的,但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
在我看来,欧阳江河的这种刚性十足而又挠度极大的诗歌语言,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重返了古典诗词的简约、含蓄和朦胧,而在于更及时更优异地拓殖了现代汉语的思辨力纹理和现场性纵深,为诗歌中的“现实感”,构筑了既能够与“现代性”深度对话,又可以迂回接应种种历史和现实的重负,并企图在悖谬中反思超越的空间和基石,从而深入回应了我们时代的种种人性诘问和生存难题。在此意义上,它是现代汉语自身的功能拓展和审美苏醒,它以“倒影”的形式,映示出传统汉语在某些区域的无力或无能。或者说,欧阳江河在“打通或者重塑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创造性关联”方面,恰恰是以让古代汉语在“现代性”的漩涡里消失为基本的结论或自然的结局——他以自己的“繁琐”和“晦涩”,标定了“古代汉语马车”难以涉足的疆域,并相应极大地扩充了“现代汉语机车”的马力和冲程。也许,这正是欧阳江河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的独特贡献,以一种对于“传统汉语”不无喜剧感的背离和更有自信心的握别的方式。
这样一来,传统的积蕴和禀赋在欧阳江河身上,似乎成了谜一样的东西,它们都挥发到哪儿去了呢?按我的妄测,一方面,它们升腾成一种温润而清迈的气节,注入了他的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成为他日常洒扫应对的生活经和哲学课;另一方面,它们又以性理积习的形式,悄悄潜入他的写作中,首先在技艺布局而非语言措辞层面,予以扫描和临摹,并最终影响到他对于作品的整体运思和形貌判断。比如,他写作中的对位法技巧、诗艺中的结构平衡能力,很可能得益于他童子功基础的漫长而勤奋的书法习悟。而且,按照罗兰•巴特“每个字词的下面都隐含着一个地质构造”的说法,显然,在词源学和语义学上,欧阳江河的遣词造句根本无法脱离他身上的传统文化操控。因此,落实到语言措辞层面,传统文化素养仍然如内丹吐纳一般,对他的诗篇进行着先验的导引和不懈的塑形,并最终留下他中国化的玄学印迹。
欧阳江河为我们贡献的悖论式语言,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纯粹”的,既不纯粹于我们伟大的古代汉语,也不纯粹于西方翻译体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异质混成”的。如果将欧阳江河在《马》诗中的那句“马之不朽有赖于非马”,挪用到这儿,将其戏拟为“汉语之不朽有赖于非汉语”,这样的矛盾修辞,也许可将我们带到更为古老也更为旷远的经文视域里——“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金刚经》)——来看待问题:我们传统汉语的优长和缺陷,其实是无法通过自身的封闭来加以检视的,必须引入一个强大的外在视域,方可在对比性的反照与实践化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一种彼此相参、互渗互化、内外交变、新旧相生的语言进化机制。最终,各种异质化的语言成分,“混成”于伽达默尔所言的“视域融合”,达成更高级别的思、言、在的新生和澄明。这种“视域融合”,这种更高级别的思、言、在的新生和澄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传统境界,也可以是融古今中外为一炉的一种崭新的境界。但不论如何,其前提应是:它并非固守在相对同质化的自身语言内部,而是以足够优良的异质化的语言,为“混成”提供出足够的内生力和驱动力。这正是柏拉图“杂于一”理念所揭示的方向——我们梦想所得这“一”,这新的澄明和旷远,必须以“混杂”作为前提:未有其“杂”,焉得其“一”?
我感觉,目前对这种语言进化机制最大的误解,就在于以“回归汉语传统”的名义,将正向的“杂于一”悄然易帜为反向的“守于一”,从而从内部移去了它进化的驱力和杠杆,变成一种纯粹单质化的自我复制和近亲繁育,导致形形色色的回归古典其实缺乏异质化成分的对撞和磨砺,其广谱的调适性、其对当代生活的洞察回应和精神塑造,缺乏一种敞开式的面向世界的广角与景深,以及相应的张力与活力。由于积习日久,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对此常常是习焉不察的。我们的现代汉语,目前已经走过了与世界上各种语言匆忙对接的草创时期,正处于与各种异质化语言磨砺震荡并深化融合的发展时期,或者说处于发展时期的上升阶段。提供一种也许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现代汉语目前的境遇,差不多相当于古代汉语在佛教东渐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只不过比那时面临的异质化语种更多,碰撞与磨合也更为激烈更为复杂罢了。佛教客入中国,既锤炼了汉语深度思辨的筋骨,又以自度度他的大乘气象,编构了汉语新的精神织体。这当然是汉语的新生而不是毁灭。
就此而言,一个他者的文化(比如佛教文化)在汉化的过程中,既有载体/符码的工具化转换,更有本体/精神的更生性再造,有其自然溢出/逸出/异出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许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收获,一种意外的惊喜,往往构成了“异质混成”最为重要的意义。就如我们目前对于所谓“西化诗歌”的阅读与学习,不仅有语言修辞这些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频频撞击,更有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层面的顽强改塑,比如,对于自由精神的倡扬,对于个体价值的维系,对于思维特质的强调,等等。这些,在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彰显,或是难于形成独立诉求的。对此,我们的“守于一”,我们常言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打底的说辞里,其实还是一种视域分离而非视域融合:只存他者之“用”而不现他者之“体”,只欣赏他人之“形”而不感应他人之“灵”,只乐见自我之精神而不喜睹他者之芳魂。而这,我觉得才是那种将纯粹的汉语诗歌进行到底的文化自信中所埋伏的最大的盲区,或是所布设的最巧妙的蔽障。
在我看来,当前阶段的很多“文化自信”,已经舍弃了那种打着“纯粹”的旗号将“不纯粹”拒之门外的涉嫌简单或粗暴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迂回之策——在“借鉴”或“交流”的名义下舍“体”求“用”,以“用”代“体”,从而导致了真正的“体”“用”分裂,让异质化的“混成”陷入“舍体求用,无用可求;以用代体,体用两空”的空壳化境地。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都是从“体”“用”统一、“体”“用”融合的视角去接受异质化语言文化的汇流和洗礼的,而且越是有价值的文化自信,越不惧怕世界范围内异质文化的洗礼和改造——只要你用中文写下任何一个字词,这个字词下面隐含着的“地质构造”,就同时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地质构造”本身的嵌套方式和广延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它并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别/国界现象。将原本隶属于心灵的嵌套和广延拘囿于国别/国界,是对于这些“地质构造”本性的反动和消解,一定会让我们削足适履,失去对于它们更为整全更为深入的把握和理解。在此意义上,博尔赫斯“我没有任何必要向任何人证明我是一个阿根廷人”,永远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扛着“纯粹性”大旗强调“回归汉语传统”的人们。
克尔凯郭尔曾说,“愿意工作的人能生出自己的父亲”。也许,对于判断一种写作是否有价值,“能生出自己的父亲”是一种潜在而不移的标准——虽然你生出的这“父亲”,很可能只纯粹于他自己,而无法纯粹于包含你自身母语在内的任何既成的人文传统。我想,立足于现代汉语写作的当代诗人,如果“能生出自己的父亲”,恰在于要向各类异质化语言包括古代汉语,自然而然地敞开和接纳的过程之中,并最终达成一个新的更高层级的“杂于一”的视域融合。任何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单向折回传统汉语的“守于一”的做法,或者以工具化思路舍体求用般的借鉴他者语言文化的做法,由于先天的认知缺陷和逻辑悖论,最终,都很难修成“正果”。
——刘国纬的《江河治理的地学基础》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