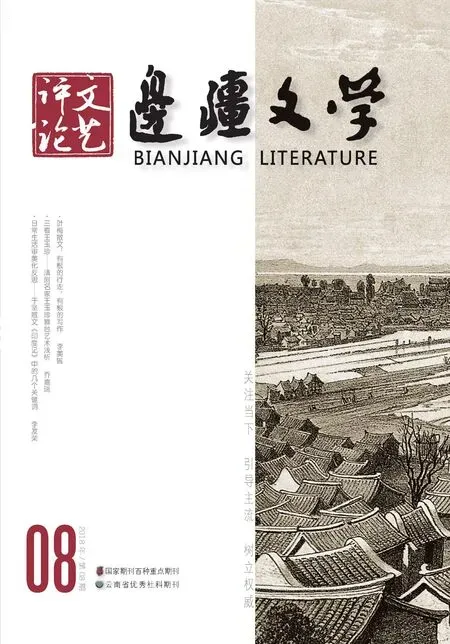叶梅散文:有根的行走,有根的写作
李美皆
叶梅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觉的作家。她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识跟她土家族的出身有关,还跟她长期在第一线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组织工作的使命有关。她的成长和阅历使她贴近自己的民族,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织工作又使她走近其他的民族。叶梅的散文涉及30多个民族的作家作品,简直是一部民族文学的感性百科全书。
叶梅散文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多民族的河流,沿着这条河流,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各民族文学的美丽丰饶。比如,她介绍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醒来吧,我的诗》:醒来吧,我的诗/苏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滋入惊醒的奶桶/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场……一个民族对于生活的热情洋溢扑面而来。叶梅还通过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了蒙古族对于诗歌的热爱。蒙古族是一个真正有诗性的民族,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在盛大的群众诗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一位老人竟因一个小伙子不知道诗歌节而结结实实给了他一巴掌,“连诗歌节都不知道?你还是咱蒙古人吗?”这一切,由一位热爱民族文学的女性写来,尤其散发着内心的温度。叶梅对于各民族文学的关注当中有一种古道热肠的东西,她生怕各民族文学的珍珠有遗落,所以,她要热切地通过自己的窗口,把它们展现给世界。
叶梅写后工业时代人对于农业文明的眷顾,是有着自己的真实感受的。作为土家族的后裔,作为三峡的女儿,她去写这些,与知识分子象牙塔里的写作相比,情感上自是不同。她的写作和行走是密切相关的,都是心之所系,足迹到处,心亦到了。《澜沧江边的一天》中写,她和同伴们几个小时冒雨爬着泥泞的山,遇见田房里的农民兄弟,主人愧疚除了煮大米招待客人,拿不出其他食物,不曾想,一串准备拿来喂牛的手指大的芭蕉,却成了肚饿的客人们的美味。客人欣喜着:“真甜,牛能吃我们也能吃。”叶梅还写道:不速之客的到来,让这小小的田房平添了许多热闹,他和牛都很高兴。牛一直在楼下哞哞叫着,似乎也想参与楼上的谈话。——这种朴素可亲的情感,仿佛就是对自家的兄弟,自家的田房,自家的牛。
叶梅的接地气,叶梅与农民兄弟丝毫不“隔”的情感,与她自己年少时的经历有关。她曾经作为一名在“文革”中受了冲击的干部的女儿,与好友彭力勤一同到幸福二队插队。她在《幸福二队》中深情追溯了这段知青生活。两个没有受过苦的干部家庭出身的少女,在幸福二队放下身段,完全融入村民中,不仅不以为苦,还为自己不被歧视而被接纳的幸福感恩着。她们砍柴拔草,卖力地与当地民众一样干农活,还养了一只叫“头子”的猪崽。“头子”给她们带来快乐和慰藉,晚上就睡在她们床下,两个少女与一只小猪,在同一屋檐下都睡得酣甜。这与知青通常的“苦难叙事”大相径庭。与人甚至与动物结下的深厚情感,使叶梅超越了苦难。她更看到,当地农民比她们还苦,所以,她不应该以自己的苦为苦。然而这种普世心同情心,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太多“知识青年”对于农民的姿态是:你是你,我是我,你的苦与我无关,我只叹我的苦,我理应因我之苦而怨恨生活不公。甚至对“头子”,她都有了亲人般的情感,当她离开幸福二队后,彭力勤把被匆忙杀掉的“头子”的肉送到了她家,她一口都没吃,尽管那是一个肉食极其匮乏的时代。她还扎心地写道,母亲说,那肉很嫩。这头猪不是作为宠物养的,她们养猪就是为了吃肉,可是,在相互依存的生活中,感情已经大于目的。在一个有情者的心里,天地众生皆通人情,皆着“我”之色,一种不忍就在所难免了。叶梅与彭力勤,更因这段共同苦乐的生活而成了令人羡慕的终生的闺蜜,成了没有血缘的亲人。她们都是极重感情的人,多年后回首,她们还为自己不能为幸福二队做点什么而感到过意不去。
叶梅曾经当过副县长,毫无距离地贴近过基层的民情民生。这种贴近感,她终生保留了下来。当作家们被号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时候,叶梅不用被号召就早已做到了,她是一直在“深扎”之中。曾经,我们一起去昭通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有一天,她单独约我去了附近农村的一个农贸市场。那是一个完全露天的黄土漫漫的农贸市场,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拖拉机和牛车满载着苹果,连绵成片。通红的苹果像小姑娘的脸蛋,她欣欣然在手凑近鼻子闻着,很陶醉,仿佛农民闻到了丰收的气味。热情的主人邀请我们品尝,我还担心没洗,她说,“不脏,干净的,放心吃”,就香甜地下口咬了起来。受感染之余,我不能不感慨:是什么使她无条件地相信,果农兄弟不会往这么美丽又美味的苹果上喷洒农药的呢?毫无疑问,是一种感情上的真正亲近。这苹果,在我眼里也变得不同起来。昭通在古代是乌蒙国,我带回几个特别红硕的苹果,对儿子说,这是乌蒙苹果。这苹果在孩子眼里似乎又有了一点历史的神秘与神话的晶亮。这一切,都是受叶梅感染的结果。在来回农贸市场的路上,她独具慧眼地挑选黄泥墙、老木门的农家院拍照。还特地下车迎着身背农具的大爷,询问粮食蔬菜的产量价格,每年的收成够不够生活,等等。我心里感叹,不愧是当过副县长的人!那种自然的攀谈,绝非单薄的“接地气”的问题,而是给人感觉,她就是深厚的地气本身。她的关心粮食蔬菜,与诗人的“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不可同日而语。
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应当不仅指身体的走出去,只有打破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才能真正走得出去;不是形式上的在“田野”足矣,而是要灵魂头脑都在。叶梅一向是身到了,心也到了,所以,采风文章她写起来不“隔”,带体温,有实感。她的“有我”的采风,与知识分子型的“无我”的采风,收获肯定是不同的。或许,那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采风,不是体验的生活,而就是生活本身。
《昭通记》中她写,三次去昭通,住的是同一家酒店,近旁的几条街都走熟了。我跟她同去的那一次,也跟她同走了那些街。店前做十字绣的女人,像老友一样地向她诉说着:有一件已经绣了三年,快绣好了,不知怎么被人拿走了!几乎要心疼地掉下泪来,叶梅跟她一样心疼唏嘘,并像大姐一样安慰着她。女人说,老公太喜欢了!这不,又买来重新绣。可见这夫妻感情很好,女人脸上幸福的光辉也说明着这一点。叶梅请她打开来看看,几个女人就一起站起来,把足有两米长的十字绣扯开,叶梅站在十字绣前欢喜地拍着照,那快要绣完的牡丹们映亮了她的脸,给她整个人都镀上一层光辉。我觉得,享受跟陌生女人们姐妹一般亲切邂逅的叶梅,很美。
叶梅在各民族地区行走,总是能够自然地融入当地人中。《舞动的山冈》中她写,在中缅边境的耿马,她去看一对新人,很自然地加入坝子上喜庆的舞蹈,与佤族傣族的兄弟姐妹们手拉手跳起舞来。我可以想见那是怎样的且舞且乐的景象,因为我也亲见叶梅在昭通的水边广场上,自然地与当地人拉起手来,加入了广场舞的队伍。她舞姿曼妙,享受其中,我都情不自禁地为她拍起了视频。广场舞已经作为“大妈舞”被打入了下里巴之流,但叶梅毫不介意这是不是有损于自己的阳春白雪。我想,伍尔夫、普拉斯是不会这么做的,几乎所有的精英女性都不会。所以,她们的写作也自是不同,这是两种路数的女性写作。
叶梅著名的散文《根河之恋》是写鄂温克老奶奶玛丽亚·索的,她把这位充满母性、慈祥温暖、柔和坚强、丰富传奇的女猎手,视为根河的化身,礼赞“她就是一条生命之河”。同时她又自省:走马观花式的接触是不是配不上玛丽亚·索生命的丰盈深厚,反而打扰了她的平静?“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根河,自己的玛丽亚·索,但我们这样匆匆地来去,怎么能有乌热尔图目光里的深沉呢?因为乌热尔图就是根河的儿子。”她要求自己以根河女儿的情感,去面对玛丽亚·索,以及玛丽亚·索所代表的鄂温克民族。她对自己的民族情感,有着至真至纯的要求。
她礼赞女性的伟大,同时也不放弃作为女人的小快乐。《棠梨花》中,她写自己在楚雄的彝人小镇的小店里,着迷于手工做的布裙、银器和各式各样的耳环。“有一种银子的叶片儿让我想到银杏老树的嫩叶儿,便掏钱买了下来,心里很欢喜。”这种欢喜我太熟悉,所以有种同喜的欣欣然。可是,在《丽江》中她又写道,她在去泸沽湖的途中受伤了,担心自己颅内出血后果严重,脑子里迅速盘点了自己的所有与所爱:“我的小小的积蓄,我的房子,我的漂亮以及不怎么漂亮的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但其实并不值钱的耳环项链,还有,一些虚名,都可以没有。”她盘点,是想说这些都可以没有,只要没有这一次受伤。但被她盘点到的东西中,必定有她的喜爱,其中包括那“银子的叶片儿”的耳饰。我看到这里,不由发出会心一笑,女人哪怕到了最后的关头,还是会惦记自己的美物。唯其如此,她们才更是女人。似乎,这是叶梅小女人的可爱的一面。可是,转头她又写,发现自己并无大碍后,她照样以受伤的脸庞参加着接下来的文学活动,享受着与民族兄弟姐们交流文学的充实与快乐。我在昭通见她时,应该是她这次受伤不久之后,可是,完全看不出她的心有余悸,这就是她的大气。她作为大女人的一面又展露无遗。那一次终未去成泸沽湖,泸沽湖,成了她最近的距离、最远的抵达。于是我们相约:以后同去泸沽湖。我是多么愿意跟着她有滋有味地行走,何况这是去女儿国,正如她所写:作为一个女人,怎么可以不去女儿国呢?
叶梅是个有心人,各民族地域的滋味,她都要亲自尝一尝。《一眼望不到边》中,她写自己在小城沧源,驻足于包着头帕的妇人的小摊前,耐心询问着香料的味道,并在亲自品尝后形容那苦涩感:“不管不顾的满嘴涩苦,像一个穿堂而过的妇人,阔大的裙边毫不文明地捎带着就将全场人都扫到了,但过一会儿会满口生津,顿时让人心生感激,觉得她有着豪爽的好意,只是不带做作而已。”每一个民族地域喜好的味道,其实都蕴藏着这个民族精神底蕴的密电码,叶梅品尝的是香料的味道,更是这个民族的内心。
一个民族地域的美,必须有心才能更好体会。初次与傣族作家禾素聊天,我就感觉她来自一个我有印象的美丽地方,究竟因何有这种感觉,却又一时说不出来。再次读叶梅的散文,我才恍悟:不就是因为她的《凤尾竹下》吗?“先到了德宏芒市,那是夏末时候,进城已是夜晚,由车拉入一簇簇凤尾竹摇曳的园子,月儿果真就挂在竹梢。只听周围人声喧哗,却只见人影绰绰,都被茂密的竹林掩住了;空气里散发出一股甜甜的清新,还有扑鼻的花香。”这些话,已经把芒市印在了我的心里,只等我去印证。叶梅的散文,使人可以按图索骥地去领略各个民族美好的风情和人情。
叶梅在行走中一直保持一种深扎的状态,所以,她的行走是有根的行走,她的写作也是有根的写作。《芦笙吹响的时候》结尾她写:“或许,人们对今天那里的生活早已司空见惯,认为从来就是如此。但要是知道过去那里曾是一个充满瘴气的地方,没有稻谷只有荒芜,没有人烟只有孤魂野鬼,没有歌声只有兽嚎,人们或许才会对眼前的栽种、养殖、读书情景,甚至行走的道路,都倍感亲切。也才会明白,那一刻芦笙的奏响,是怎样地让人泪流满面。”这种“肠内热”的深情,必须是根植于一个民族生活的纵深,与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冷暖共感,才会由衷生发出来的。
虽然行走了这么多民族地域,但叶梅对于各民族的文化,从来不会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上,她一定要深入一个民族的内心,去了解文化背后的所以然。在《丽江》中,对于被充分八卦和猎奇并涂抹上某种色彩的泸沽湖走婚传统,叶梅根据民俗学家白庚胜的介绍,给出了正本清源的文化阐释:走婚的摩梭人其实有着严格完整的婚姻习俗,三代近亲之内严禁走婚,走婚但不乱婚;男子可以选择自己的“阿夏”——也就是情人,女子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阿都”,但是不可以同时与几个人相好,只能选取一个。一旦双方感情破裂,断了关系后才可以与另—个新的情人开始走婚。如果发现有近亲走婚者,将被乡亲视为牲口,遭人耻笑。——对于一个民族传统习俗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正体现了一个民族作家的自觉和负责。
叶梅的散文还闪射着表达的机智。比如,她说自己“比较敬而远之地偶尔读一些当今的诗歌”,传达出丰富多重的意义含量。她写汶川地震后,汶川的羌族诗人羊子到海边的《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去,坐在海边沉思,“大家远远地看着,不敢去打扰,不敢去惊动他眼里常含的泪水,似乎一叫他的名字,那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她把一种纤细敏感的情感状态,准确唯美地表达了出来。她的《庐山捡石记》,既有着对于美的内在敏感,又有着浩荡丰沛的时空感:我载不动庐山的云,那是古来的云。走在牯岭街上,那云突然不期而至,从遥远的天边翻卷逐浪而来,果然是在瞬息之间,弥漫四合。动或如烟,静或如练,返照倒映,倏尔紫翠,倏尔青红。那云长袖善舞,软绵拂面,我抓拭一把,随风倏然而去。再探头向山下,只见云海滔滔滚滚,蓊蓊蓬蓬,红墙蓝瓦转瞬被云遮盖,几只白鸽跃然飞起,其光如银。但见三四老者于街头围石桌而坐,安心对弈,白云缭绕在他们的膝间,恍然片刻就如千年。——这样的文字,承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美文传统,把人带向悠远。
叶梅很少写个人感情,偶尔有之,则惊鸿一瞥,令人心动。《昔日重现》是叶梅怀念初恋——那个叫二子的男孩与男人的:“想到你就想到一条透明的小河。淙淙地流淌着不知疲倦,将一点点晶莹的浪花高高地抛向蔚蓝的天空。河水流过的地方,有碧绿的草地,开满了红、黄、紫各种颜色的小花儿,在轻柔的风儿里摇曳。我仍然是这样切切地思念着你,二子。你就在一片无垠的天地里,微笑着向我走过来了。……二十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世界在刹那间停止了所有的喧嚣,你在灯光下站起来。你说兰,我知道是你来了。……我说我到处寻你,茫茫人海之中偶尔会觉得找见了你,但一看又不是,一看又不是。二子,你就是你,天底下只有一个你啊。”这种惝恍迷离令人泪下的美好情愫,只属于懂得爱的女人。能够把曾经的爱这样清风白日地说出来,也唯有敢爱敢恨的豁亮的女人。这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叶梅。唯有多面,才让女人更加饱满丰赡魅力无限,如多籽多汁的石榴。
无论何时,我都愿意看见女性的美丽,并愿意与美丽的女性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