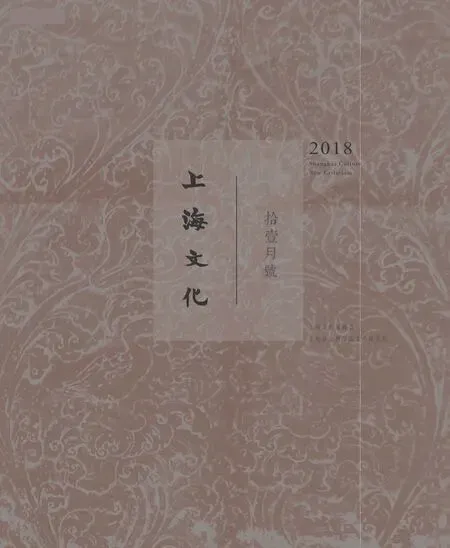浮云拾影(四)二十世纪中国摄影
洪 磊
袁东平的那些“精神病人”的照片,被吕楠的照片掩盖了,吕楠的组照《在路上》还掩盖了杨延康
40
“四月影会”后的1980年代,北京的摄影圈并不多。还在学校的高波和韩磊,还有袁东平经常在吕楠家聚会,谈论他们所能看到的摄影作品和艺术家。
1987年,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后,高波一个人去了西藏。据说,当时只有一条主要公路进藏,在西藏半年的时间,他大部分都是在路上,没有公路的地方就徒步进去。之后,又从西藏又翻进了新疆。
高波后来总结自己,“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我的生活是流动式的,我到处走,我的摄影方式也是流动式的,也是旅行式的,走走,看看。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把它拍下来,用我的语言来说,就是把它“偷”下来。“偷”一个影像和创造一个影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时候有一种年轻人的勇气,想告诉别人我是强壮的。所以,我要去珠峰,我要去阿里……作品里表现出来的,也是那种年轻人的勇敢……”
高波那个时候摄影,全然没有意识形态之下的思虑,与当时的其他摄影人比较,他的照片只是美学问题。他自我放逐,是要表达自我之勇敢,他对形式美的敏感天赋,只是流露在他行走的一路上,他并不在意。
1989年,袁东平听同学说,天津安康医院,每年春节会有医生,护士和病人一起联欢,很有意思。至此后,他和吕楠开始了精神病院的拍摄。
袁东平的那些“精神病人”的照片,被吕楠的照片掩盖了,吕楠的组照《在路上》还掩盖了杨延康。袁东平没有吕楠那么有目的,他没有准备。但是,在他那些不经意的拍摄里,有一些远距离的观看的拍摄,一些游戏中的“精神病患者”,那种荒凉感叙述人类境遇,他自己没有察觉到。
袁东平后来说,“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目的,所以也没什么困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照片会用来干什么,也根本没想到会发表,出画册那更是做梦都没想过。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困惑,完全就是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严格地说,困惑也有,就是后来拍得很平淡了,不得已就拍了一些特别极端的。完全是在形式上玩花样,最后看,这些刻意的也不行。”
41
1990年代,有三个河南人,几乎同时在用拍摄标本的方式创作。
顾铮认为,罗永进以一种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建筑本身,从而揭示了建筑与权力、欲望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艺术家对这一切的认知、反省、质疑和批判的立场。
大约1997年的时候,罗永进开始了《新民居洛阳》的拍摄,《新民居杭州》则是2000年之后了。不同于德国的贝歇尔夫妇,罗永进不是客观和冷静地纪录,他更多地介入了自己的情绪在照片里,或者是一种态度。莫妮卡·德玛黛说,“他的影像叙事弥漫着一种宿命感”。
姜健是一个练达持重的人,为人接物很有分寸。记得在那尔顿摄影节,姜健1990年代初的一组题为《主人》的照片,这些照片纪录了当时中原区域的农民家庭。作为广告,巨幅的画面悬挂在展场外。后来,我们每次去吃中餐,那些来自广东的移民老板,都会指责我们,“中国已经发达了,已经没有这些落后的地方了”,等等。
鲍昆评价说,“和身份同时变化的还有文化的面容与表情。那些和土地、阳光与柴灶烟火相生的农民们,被劳动和岁月形塑了文化的身躯与表情”。
姜健刻意于被拍人物的背景选择,这些社会属性,在他看来尤其重要。
庄辉从1996年至1997年间,先后洽谈了二十几家单位,最后有十二家机构单位同意。他用老式摇头照相机,拍摄街道、乡村、工厂、医院、学校和部队等大合影照片,记录下20世纪最后几年里人们的精神面貌。拍照的形式是用普遍认定的方法,让被拍摄者和相机的焦点形成180度角。拍摄冲洗出来后,被拍摄者在一个水平面上展开排列,形成了平行展开的画面。
这种影像模式,是1950、1960年代,各极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各项重大活动,纪念照片的标准模式。庄辉的这种肯定的否定之拍摄,后来被归类为“观念摄影”里了。
42
韩磊也是河南人,是高波的学弟,都学书籍装帧专业。
1989年之后,纪实摄影开始拒绝影像附庸政治使用。摄影开始记录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那个时间段的社会现实的视觉描述。这一时期,差不多每一个纪实摄影人,都找了自己的主题。找到主题的摄影人,力刻露于“作用”,一心让作品充满感染力。
也只有韩磊一个人,从来都未有过“主题”的念头,脱离了当时的思潮,或者是,他没有社会责任感。即便他的学长高波,散漫拍摄,也还是有“藏民”符号。韩磊什么也不在乎。
杨小彦说,“韩磊的镜头总是多了一层暧昧,一层晃荡,一层闪烁。韩磊拍铁路,拍陈旧的火车皮,拍灰暗的街道,以及街道上无聊的行人,他的景观出奇的平淡,平淡到让人心悸”。
现在,回看1990年代的中国。方力钧的油画,叙述了知识分子的无奈,却是用泼皮无赖的笑脸来表达。这样的表达是否准确?不在这里讨论。1990年代的文学,现在回看,几乎没有表达。只有看韩磊的照片,一下子将你拽进了那个年代,迷茫的人群,迷茫的眼神,迷茫的风景,都在平淡里展演。
很早听吴小军讲过,韩磊从不印照片小样,通常双手撑开底片,看了看,选定画面后直接放印。心想,他也太骄傲了吧?后来问韩磊,他说,“我一般不会连拍多张照片的,所以我记得每一张照片”。
1994年,汉斯给韩磊做了一个摄影展,名曰《疏离》,自那个展览后,与韩磊熟知起来。那时候,韩磊非常帅,身材修长留着长发,说话机智幽默。
有一次在王府井,远远看见韩磊迈着大步,匆忙走着,那潇洒的劲儿,至今记得。吴小军说:“韩磊,他就不该有安定的生活,他只有游走,他适合永远在路上。一旦他安定了,他就会不安,他就要去砸碎它。就像他的相机,没有一个完好的,新买的相机,不出三天准给丫摔破,你去问,他有一台完好的照相机吗?”
2000年之后,韩磊又开始了许多系列的观念摄影的试验,不过他散漫的拍摄方式,一直没有丢弃。
43
1990年代的文学,现在回看,几乎没有表达。只有看韩磊的照片,一下子将你拽进了那个年代,迷茫的人群,迷茫的眼神,迷茫的风景,都在平淡里展演
刘铮也是游走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之间的艺术家。大概是1996年的时候,他与荣荣一起做了一个地下刊物《新摄影》。那本刊物八开大小,均是以复印机复制,手工装订。在当时,只在小部分艺术圈内有些影响。一天,安宏告诉我说,荣荣在找你,想在他们的《新摄影》上用你的照片。
1996年初,决意放弃艺术。过年前,回到老家常州。在北京借钱欠了亏空,便要赚钱。开始了做广告方面的平面设计。心里还是惦念着往事,闲暇之余便学着美国艺术家科内尔(J0SEPH CORNELL)的方式,做了一些类似装置的东西。因为都是些即兴的摆置,那个时候,学生董文胜开有一爿照相馆,在他的帮助下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件《中国盒子》的概念,在1995年底就已有了想法和草图。这些东西,没有奢求,仅是安慰自己。
那个时候,安宏已经做了不少照片了。他将自己化了浓妆,扮演着类似密宗佛陀的造像,做着各种姿态表演。他说都是自拍,又做动作还要按快门线,很是不容易。他除了浓妆之外,均是裸体出演,有几张他是和一女生合演,做着欢喜佛的造型。
拜访荣荣,记得是在朝阳公园南边的一个胡同里。荣荣是福建人,那个下午,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院子不大,不是四合院,这里已经是四九城之外了,房屋有些年纪,应该是一般小户人家留下来的。
起初,不知道荣荣也做摄影,那个下午,大概谈了些他们的《新摄影》所需照片的要求之后,我们聊茶聊书法,他说他中学的时候,得过硬笔书法大奖,等等。之后再去北京,荣荣那里就是一个点儿了。那个时候,荣荣的女朋友,也是个日本人。
1997年在北京剧院,岛子策划了《新摄影展》。当时参加展览据说有十一个人,现在能想起来的是邱志杰,刘树勇,安宏,还有师若夫和我。邱志杰做的是图钉纳进身体,红色打字写过身体等等,是些被虐的图像。刘树勇展的都不是自己拍的照片,而是将萨尔加多,吴印咸等人的照片标上自己的名字。师若夫,则是学习基弗尔的方式,拍了许多圆明园的风景,然后用白色在照片上点点画画。
那次展览的研讨会,争论相当热闹,只记得老栗说的一句话,“这个展览只有洪磊的照片是摄影……”
《现代摄影报》1987年7月8日,刘树勇撰文《权利——关于“观念摄影”的对话》,第一次提出“观念摄影”一词。之后,“观念摄影”名词便传播了开来。
44
荣荣虽然是在纪录行为艺术,他很主观,很自我,有时候他的关注点似乎并不把行为者作为主角,画面散淡出阴郁来
“观念摄影”名词,后来解释上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被囊括为“观念摄影”之内的那些照片,现在来看,不是全都有观念。纪录行为艺术的照片,观念在行为者自己,而不是拍照纪录者。譬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那张照片,被认为是观念摄影很重要的作品,当年是由吕楠拍摄的,之后吕楠在暗房印了八张,分别给了参与行为的八位艺术家,每人一张。据说,吕楠当众剪毁了那张底片,他不认为这是他的作品。
佛家认为,观念是对特定对象或义理的观察思维和记忆。笛卡尔则把观念分为,天赋的,外来的和虚构的,三种结合为一体。
譬如,马格利特的油画《这不是一个烟斗》。这幅画有一个烟斗的画面,烟斗下方写有一句“这不是一个烟斗”。在这里,形象与文字内容之间产生了“矛盾”,但是,只表达了一个指意,所以又并不矛盾。福柯说,“马格利特的这幅画竭尽所能为形象和语言重设共同场地,但是本应作为图文联系点的烟斗飞走了,于是共同场所消失了。”
1967年,索尔·勒维(Sol Lewit)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观念艺术”这一名词。
我倒是觉得荣荣、刘铮他们的“新摄影”概念,或许准确些。1992年,荣荣入住北京东村。当时,住在东村的还有马六明,张洹和苍鑫,他们都是做行为艺术的。荣荣说,“因此很自然的就拍拍身边朋友们用他们的身体所完成的前卫艺术创作。”荣荣虽然是在纪录行为艺术,他很主观,很自我,有时候他的关注点似乎并不把行为者作为主角,画面散淡出阴郁来。我很喜欢荣荣的一些风景照片,可惜,那个时期他拍得不多。
1998年12月28日,朱其策划的《影像志异——中国新概念摄影艺术展》,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画廊开幕。朱其策划的这个展览的参展成员,原先大都是绘画,装置艺术家,都是学艺术出身。这一选择,是否不同于岛子?岛子所选择的成员,是符合他理解的观念的摄影吗?
就此,我问询了刘树勇,他回答,“简单说,我1993年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提出这个概念,因为我发现有些摄影作品过去的概念没法准确描述它们。然后请岛子策划了一个美术界的以摄影为媒介从事艺术实验的展览,并没有完全定义在‘观念摄影’的概念范畴内。岛子只是把用摄影媒介做艺术实验的艺术家,作了一个集合,然后展出了。艺术家是他选择的,我只是帮华子一个忙。朱其的展览基本延续了岛子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将以摄影为媒介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集合一处,做了个展览。没有什么原创性和建设性”。
45
顾铮在《观念摄影与中国的摄影之我见》中曾说:“观念摄影打破了关于摄影的传统定义,使历来的影像标准发生动摇。它给摄影家以一个参照,证明摄影其实是一种极其自由的媒介,同时也预示了影像价值标准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它在另一个意义深长之处是作品发表渠道的多样化,专业摄影杂志无法决定观念摄影家的命运。同时,它也促使摄影家认识到摄影可以是目的与手段两全的表现媒介。因为观念摄影引起对摄影自身的关注。它使人深思,摄影究竟是什么?摄影作品的概念是否需要改变或扩充?摄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摄影家所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1998年,台湾的《摄影家》杂志12月刊,介绍了中国新摄影的八位艺术家。介绍的方式,是阮义忠与八位艺术家对话,我坐了一夜的车才到北京。大概是第三天,我在住的一家小旅馆与阮义忠见了面。那天谈了有一个下午,记得最后阮义忠说,“你们大陆艺术家可真能说,什么都能往哲学上靠”。
那个时候,也的确没什么人愿意听我扯闲,有许多的想法和思考,藏在心底像垃圾一样,都发霉发臭了。有人愿意听,并确是采访,也就越发口若悬河,轻浮得厉害。
阮义忠的名字,很早是从吕楠口中得知,以为他是一个摄影理论家。他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我都买了,仔细研读了《当代摄影新锐》后,才得以全面展开后来的拍摄。2004年的时候,曾去他台北的家拜访,才知道阮义忠是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尤其他家的暗房之专业,设备之精良,真是长了见识。记得那个暗房里还有一套音箱,应该也是很好的吧。前些年,阮义忠来我的工作室,没坐几分钟,他便起身,关了我的功放开关,温和地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你这破音质了”。
“观念摄影”,或者称“新摄影”,这一概念在两三年里,持续被关注,很是讶异。展览活动与报道之观点,却各行其是,不免要生出疑窦,原因是八九十年代里,多少也接触和参与了些艺术活动,期间的人事争斗与名利争夺,看见不少,也被排挤被伤害。许是这里也山头林立?很是害怕被卷进某个圈子的是非里去。
有一天,刘铮电话我,说请吃晚饭,心里有些犹豫,衡量许久。然后匆匆简单地吃了点儿,去往刘铮家。那天,荣荣和他女朋友也在,主菜是一条鱼,还有两个蔬菜。我说,我吃过了。刘铮大为光火,即刻翻脸,大声道,“我他妈省了一个星期的饭钱,就为了今天请你。”场面很尴尬,荣荣他们则在一旁不响。我只好陪笑脸道歉,刘铮这才消了气。
的确,我很害怕进入一个圈子。不过,倒是很喜欢刘铮的那套《国人》照片。
那个阶段。刘铮刚完成了一组戏仿传统经典剧目的照片,在他家仔细地观看他的照片,心里暗暗叹服他的技术。后来知道,原来他是学光学的。刘铮的戏仿戏曲的照片,力刻露,于每处细节都做到精密完美,大有学习威金的方式。2015年威金来南京,刘铮也赶来,开幕当晚晚宴,刘铮异常兴奋,对威金说,“你就是我的父亲”。众人惊诧,随之哄笑一团。那一刻,我看到了刘铮的真诚,他理想主义的单纯,一直存留着直率,不去掩饰。
是的,我也是偶然买到一本杰夫·沃尔的画册,才懂得了表达的方法。
46
阮义忠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且坚持着报道摄影。他的摄影集《人与土地》里的照片,有一种质朴的温暖,一种对故土怀恋之柔情。
并不能了解台湾的艺术,虽然有些年与台湾的艺术家一起参与过展览,也与一些台湾艺术家成为挚友。但是,对台湾艺术的生成,以及那里的政治形态,不很了解。譬如昨天,与陈界仁交谈,他的视角均在政治区域内,他的思维缜密非常逻辑,这样的鲜明态度的缘由,无从察考来自哪里。所以,这里不会涉及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的摄影问题。
也不会讨论照相馆的照片,因为照相馆以盈利目的,刻意为之,虚假得厉害。
也不会论及商业摄影,譬如时尚照片。设计界柳冠中说,“我们有了工业,我们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倘若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思维,便不可能有当代设计,时尚也只是虚拟,时尚摄影在中国的现在,不过是个假托,抑或模仿。
1996年的时候,由于一些北京的朋友都说我的照片好,不过是些即兴的装置摆设,疑虑这些照片真的好吗?先看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那本书,随后托在深圳的韩磊帮我买了一台PENTAX120二手相机,想以后以摄影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后来,吴小军也托韩磊买了一台BRONICA120二手相机。椐韩磊后来说,他也是托安哥在香港买的。
吴小军说,“我就是看了你们都在做摄影,就捏些泥人拍着玩”。1999年,东京立川国际艺术节,《爱: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展览,吴小军的照片作为招贴使用,吴小军的照片,在于他自小乌托邦理想被破灭,自我反思,戏拟的方式,去追忆童年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并且用神秘主义的方式幽默调侃,政治事件被寓言化了。
应该是1995年,故宫太庙展览了一个德国当代艺术展,好像是博伊斯,以及他的学生的作品。那个展览上有贝歇尔夫妇的照片,古斯基的照片,还有托马斯·鲁夫的照片。当然,装置油画都是不曾相遇的方式。看完出来后,经过一面橱窗,里面正展示北京工人摄影爱好者的照片,急匆匆走过只瞥了一眼,突然便明白了摄影。不过,当时我还在苦恼自己的油画表达问题。
之前,一直与吕楠、韩磊在一起聊天,对摄影的思考,似曾相识。然而,我和吴小军,还有安宏,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做摄影,也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