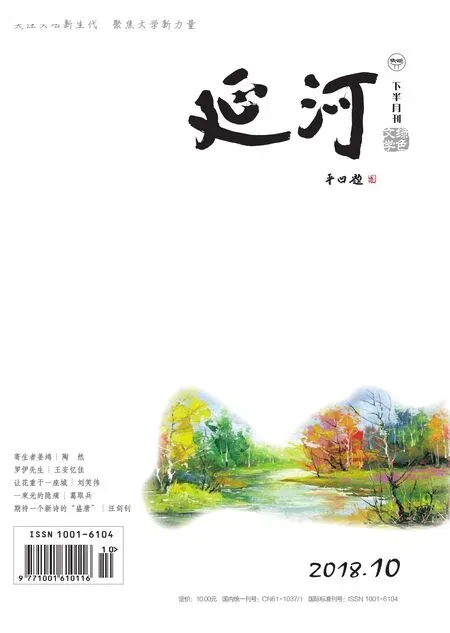谋心之道,艺术在场
——一瞥王安忆佳《罗伊先生》未曾启动的奔跑
阿 探
读王安忆佳的《罗伊先生》,惊喜有甚于多年前读徐则臣的中篇《西夏》。90后心灵的无碍,70后的负载与苛望,天地有别。
“90后”作家有着超常的自我创作姿态与审美执着,他们最明了文学空间的无限,因此更能进入自由创作的纯粹之境,几乎每个人都在构筑着自己的文学圣殿。他们的最大创造力在于,洞穿现实雾霾般物象的迷离,构筑无从寻起的艺术静谧之境。王安忆佳的短篇《罗伊先生》,以静美图景再造,扔下现实的喧嚣与纷扰,实现了内心与诗意共同构建的抵达。
艺术类别之间,同源而无界,通感对于文学创作尤为重要。王安忆佳精准把握了电影艺术表达与小说构建的同质要义,以镜头的不断切换,大音声稀之语言,重构了文学的新图景。小说篇幅精短,无意于心理刻画,却画面直指人心幽深层面。文本整体呈现文学静美之境,静美囊括了所有心理时态、动态,潜隐着人们隐秘的心灵动影。电影是流动的声与光影的文学,编剧有自己的构建,导演有自己的理解与构图,这种表达艺术回流到小说,则需要作家兼有电影创作几乎所有核心创意人员集合的智慧高度,这是年轻的王安忆佳所具有的。她的指尖在键盘上起舞的律动,穿透了喧嚣中的世界,从体察中生活印记点燃,以镜头的游弋,给予读者想象奔涌与享受的世界纯真面影,甚至以艺术的方式给冰释坚硬的尘世生活,完成对“现实”文学命名。 此作,不可不谓才情与意识流体的灵飞。
在镜头般的叙事流动中,亦清晰地表达了创作者与生活的关系,亦或说创作就是故事与编辑故事的积淀过程的历练。小说以镜头的切换,平行展开了四个故事,主次分明。楼下阿姨的故事是凡人喜忧常态,“宫崎葵”的故事是和美虚像下的管涌在心;陈立秋的故事在于人们只在乎眼前,过往常常被遗忘。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常态的生命的在场,只不过是被称作“罗伊”先生的少年无限精神空间的补叙、陪衬或底色。罗伊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或许是“她”艺术理想人格的化身,或若即若离的实与虚的映照。他力图穿透尘世物象阻隔的动影,叙事镜头中早已渐已清晰、明了。
凡人常态的他们,是罗伊先生在场的底色,那么“她”又是谁呢?“她”又要干什么呢?重放的镜头:“她”在重书一首“深蓝色的”歌,“那种不透气的蓝,像一堵墙”。“她”执着以求的是纯粹,堵住尘世喧嚣、纷扰、雾霭的墙的纯粹,是深沉、广远的蓝。“她”的歌,由意识里的“罗伊”先生来演绎,他未曾启动,或许已挥马扬鞭,奔跑向了远方。“她”是王安忆佳的强大心象的载体,在推出他人中和同众人,最后推出的或许是王安忆佳的文学雄心。
电影表现手法在精短的文本中得以完美盛放,有限场域延宕着无限的悠远,尘世的表象纠葛,无以埋没超越之心往。文本近乎至真地演绎了世俗生活与艺术纯粹的对峙,可贵的是小说的展开,始终与诗意同行。在平和、溪流般叙述中,艺术之心直指彼岸,如一场没有喧闹没有鱼刺的盛宴,欣赏中唯有纯粹享受的过程。心灵无碍,或许是90后作家重归文学高贵品质的坚实根基。
曾经的《西夏》被评家们热捧,被评家认定为“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有野心的小说叙事实验”,被感知为京漂生活的“如此脆弱”,“珍贵而温暖”……对于笔者而言,更愿意把它看作70后的灵魂写照。徐则臣之所以有如此“成年人的童话”,在于70后成长于纯澈的童话,成年遭逢时代性生活的颠覆,从内心来说并不放弃诗意,因此“成年人的童话”,不存在的理想之境,能更近人心。尽管有京漂小说的认定及诸多肯定,但依旧难以掩饰《西夏》逻辑硬伤,整体考量,所谓超强的构建只不过是徐则臣缺乏细密、用力过猛的意识奔突,呈现着艺术柔韧性的缺位。关于小说理想之境的构建,90后作家王安忆佳,找到了化刚为柔的灵动,她持有移形幻影的取景器,善于打破空间与世俗物质阻隔,似乎更胜一筹。
对于王安忆佳来说,生活本身大约就是艺术,她把理想追求化作了生活,生命本身成了她艺术行为语言。作为一个极具灵性的创作者,她文学观念与时间无关,她直奔现实的艺术本真而去。文学本是谋心的艺术,如时间无涯。谋心之道,艺术在场,90后的王安忆佳,也一定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