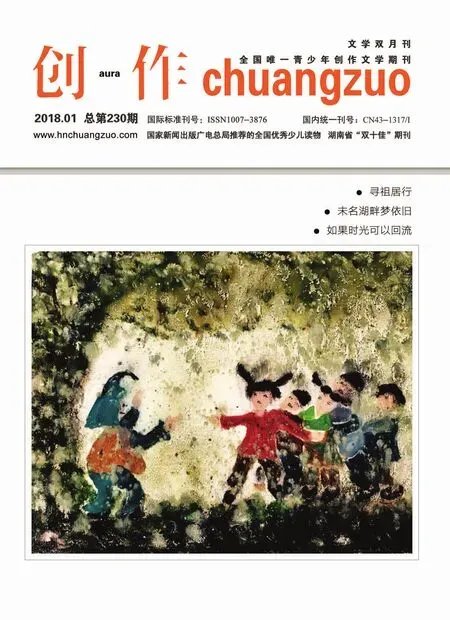英国纪程(组诗)
作者:丁一达
学校:湖南省株洲市二中
里 海
在蓝得很深的里海之上
云层是一大片珊瑚礁
你怎么知道这是天空
你怎么知道这是海底
没有时差 这时间的浅滩里
我们抛却 我们捡起 同一片蓝
如同机身一样的生命
在又一个太阳底下疾行
流汗与呻吟 海更咸了
于是有喇叭声
“一片死藻!一片烂泥!
一次次重复虚妄的意义!”
一片海域为浮藻遮蔽
他们夺过操纵杆谋划坠机
比起幽深的海底
他们更惧怕此时款款的阳光
他们骄傲得像先知一般
“我们愿意下沉!
因为我们渴望上升!”
没有价值便是最大价值
失去意义就是最高意义
海底就是天空
天空就是海底
我也曾被这样欺骗
相似的风景并非搁浅不前
行进间变化的毫末未曾被发现
上升者是为发现一片田野
比另一片田野更绿的快感托起
而非是以高低的诡辩逃避大地
那并非是同一片蓝
并非是同一片蓝
阳光是伦敦的另一种雾
阳光是伦敦的另一种雾
在晴天把一切烦恼都模糊
灰鸽衔来满树的风
河畔的孩子们多么满足
男孩扯了扯女孩的金发
掉了一地 从她的肩头抖下
大本钟慢下的几个世纪
都被泰晤士河流成一种
时间的宽裕 城市的安宁
人与桥与树与鸟
同一个拍子上的呼吸
大本钟也要咳嗽
仿佛凉意也是每隔一刻钟
在河畔吹袭
疑心在 这舒坦的天气
哈姆雷特为何还要
作生存与毁灭的叹息
船在航道谁在粼粼
莫非苦难
在温和湿润的环境
也更易生长
命运在此也更为戏剧
我仍情愿被这样的黄昏俘获
倘使我们太累 就在先贤的膝上
或是泰晤士河的长椅上
稍作休憩 等一场雨
风又缝合了我和世界
仿佛它缝合眼前的这条河
河又被吹裂
河又被吹合
入苏格兰
倘若思考需要
能把云层和草甸
冻结在一起的冷
苏格兰理应孕育哲人
北境是山羊所啃食不完
去种诗歌的土地
诗歌的肥料是荒芜
诗歌的肥料是贫瘠
诗人 就是瓶颈
他们不比青草聪明
自以为捱不过
没有温度的冬天
没有春日清晨
春风热烈而湿润的唇
那些青草 因为高空的
盘旋的鹰的一眼而苍黄
哪怕它是山羊
所赖以为生的食粮
鹰也无需高傲
因为在山羊的眼里
他如同他眼里的山羊
一样渺小
西敏寺
直言不讳有些教堂堆砌
纵然哥特耸立 尖顶
把天空紧逼
曾听说 这是哪位国戚
银制的烛台
金色的穹顶
主教的祝祷送他们归西
典礼像是在逃避
一个他们心知肚明的真相
人间的货币不再流通
哀乐奏到最后一小节
上帝不见踪影
而这里 在相同的建筑中间
上帝就在这里恭迎
神龛外富足的人们
即算对于天堂
他们并未心心念念
不只一个上帝
不只一重意义
缪斯都有九个
那是意外 说什么名望与敬仰
只是太凛冽只是太向往
生而为星辰
难道能不闪耀不荒凉
在时代的洼地
我们仍有无数座峰顶
长夜 有无数颗晨星
那样的海拔才有天国的栈道
那样的光亮才是尘世的福音
上帝 是把自己赐予给自己的
又把自己赐予给世人
喧哗的路都匆匆地走着
所谓瞻仰即所谓游荡
那些用生命的石头
敲出人类一个
又一个日出的人们
在穹顶之上
寂静地永生
查令十字街
街头到街尾 不过
一个酒吧两家花店
唐璜就老了
带上镶边的老花
雨刚过一阵 洗掉
街上午后的故事
在黄昏的人流里
准备翻台
这儿比泰晤士河更难靠岸
落寞的旅人在异国
只有夕阳是缆
没有风没有帆
没有越过大西洋
画在信纸上的图案
门推开 旧书店里书都觉得挤
没有一个是我的故事
与老花在诗柜前撞上
我猜衬衫与手上的书同龄
他微微颤动的嘴角
连接着他眼里伤感而澄澈的光晕
是伤心的一面书柜
还是遗憾的一句诗
看向我时 附带着雾翳
那笑容格外友好
问什么诗人是我在寻找
每一个堆满旧纸的橱窗
平分掉三个世界
我和你隔的是诗句
店门 与大街
我深自缄默
盼望我的声音能传得更远
我不鄙薄霓虹
不看低马路
可我的爱是闪电
我没法不去爱湖泊与山原
每一个推门进来的顾客
那些霜冻的心 无不
在柔和的灯光下自私地
“祈求着黎明”
我们是永远都睡不醒的人
彼此之外 谁又在乎谁的热爱
谁的悲哀与噩梦
晾干枕头上干也干不了的眼泪
不去迎接一个有着阳光和牛奶
写满清晨的未来
时间已经不早
我揣着一张不知该往哪赶的车票
我思忖是一个礼貌的道别
还是匆忙的悄悄
推开门的另一只衣袖被扯住
他递给我一本苍老的拜伦
城在爱丁堡
风蜷缩在海边的岩礁
涌动的石岸在城下呼啸
城市 被像黄油一样的午后涂满
北大西洋的暖流
也躲开你的高傲
高地的历史容易起雾
勋章尽被鱼虾衔走
炮台已老迈
与孩子含饴
遇着行人问问
先有城还是先有堡
潮声淹没掉讪笑
病痛也是没有的了
那些笑纳了无数
谎言或赞誉的伤痕
如今被修得很好
骑士们死在了你的囚牢
你死在囚牢的门票
奄奄一息 你将在
车流里失聪
误解与轻蔑的喧嚣
坏过当年的坚船利炮
他们口中的可敬
不就是比海浪更尽职的时间
卷携而来的屈辱
不就是历史和苏格兰
和你开的玩笑
船帆来自远方的海岸
再没有舰队朝你扑来
那些老去的砖石
是否也曾钦羡酒馆的地面
市集货台 小姐们要走的
林荫大道 而不生一身的海藻
听一生的波涛
夕阳染出一个英雄的影子
覆盖整座城市
每日入夜 城市失去的
岂止是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