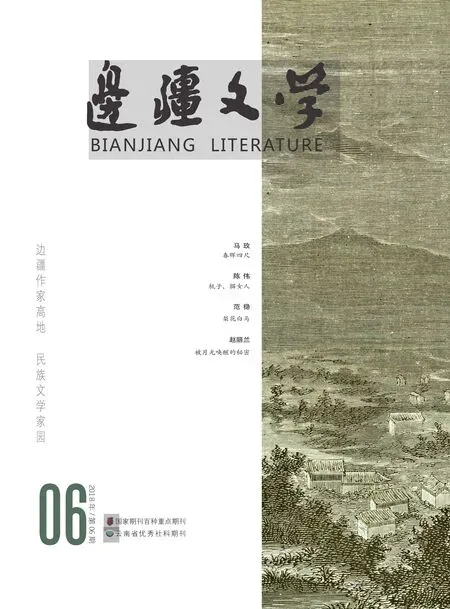梨花白马
范 稳
慵春,一白马与王子不知来自何处,误入梨花阵,与满树梨花浑然一体。王子于坐骑上翩然而下,如暗香来袭,梨花飘落;王子衣裾翻飞,英气逼人,搅动一树梨花骚动不安,山川为之动容,溪水不敢向前。溪边一浣洗少女,洁如梨花,眉含花蕊。恰似梨花之上更多一点的白,梨叶之间更多一点的绿。王子马放梨园,至溪边,与少女嬉戏调情。间或远望其马,不识何为梨花何为白马矣。乃问少女:“吾马安在?”答曰:“梨花像白马,白马似梨花。”天将黑,王子欲归,马早已远遁矣。唯见一树梨花,暗笑晚风。
此故事取材于南国哈尼族民间传说,略加改动。原传说是讲在人神不分的时代,一个叫“俄咀”的天上之人(姑且视他为骑白马的王子),来到人间过“苦扎扎”,这原本是一个哈尼人庆祝春暖花开的节日。且说那王子将白马拴在一梨花树下,与俗界人神共娱。尽管他在享受人间幸福时,还不时远望梨花园中自己的宝马,但他已经分不清哪是白马哪是梨花。等他想起要回到天上时,眼前却只有一园梨花了。后来白马虽然找到,但牵马的金缰绳却丢失了。天上之人回不了天,于是告诉村人:“马似花来花似马,花马难分难找马,从此春天我不至,待到六月我自来。”以后,哈尼人都在六月过“苦扎扎”节了,那时正处于家家柜中粮食告罄、却即将收割的关键时期,因此“苦扎扎”就成了一个勒紧肚子祈愿丰收、苦中作乐的节日。在哈尼语中,“苦”与汉语意义相似,有清苦之意,“扎”是吃之意。两个“扎”相连,相当于吃了又吃,多多地吃,这就是大吃了。在过去,吃或者大吃,是一种节日中才有的行为,因此也可将之理解为一个节日。但为什么在青黄不接之时还要大吃过节呢?我推测这或许与哈尼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越是清贫,人们越要欢乐。何况万一那白马王子冷不丁从天而降呢?人们把“苦扎扎”又称之为“六月年”。顺便说一句,哈尼人一年中要过两次年,还有一个“十月年”,是庆祝丰收的节日,有名的哈尼长街宴,就在这个节日里过。五月、六月间已进入夏季,气候变得溽热,一些疾病在魔鬼的引领下悄然而至,田里百虫活跃,庄稼病害滋生。过去哈尼人认为这些都是魔鬼在作祟,人们清扫水井,夜晚点燃松明火把,照亮屋内,驱赶邪恶,又将火把插到田间路旁,送走瘟神。人们还在节日期间杀牛(黄牛)祭祀,祭天神、土地神和祖先神。祭祀天地祖先后,再将牛肉平均分配,寨子里的人无论家里人口多少,户均一块。实际上“六月年”到今天已经演变成是哈尼族一个传统的农业生产节日,魔鬼已经远遁,天上的王子来与不来,都不会影响哈尼人在“六月年”里的欢乐。哈尼人荡秋千、打磨秋,年轻人唱情歌找对象,小伙子们个个赛王子,姑娘们都打扮得似仙女,就像过年一样的热闹。囊中羞涩和腹中饥馑都忘记了,在欢声笑语中有点像那个马放梨花园、分不清哪是梨花哪是白马的天上之人。
我听到的关于梨花与白马的传说在哈尼大山中还有不同的版本。有一则演绎成是天上的仙女骑白马来到人间,拴马在梨树下与心爱的小伙子幽会。小伙子为了像梨树拴住白马一样拴住仙女的心,就骗总当心马跑了的仙女说,梨花像白马,白马似梨花。我们可以想见:陷入情网的人儿,哪还分得清梨花与白马?或者他(她)根本就希望,他(她)的白马已经化作了一团梨花。谁不愿意在这人间仙境中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呢?当代哈尼诗人哥布曾经以此为题材写过一首诗,他在诗的结尾处写到:
“与其说仙女相信了凡夫俗子的谎言,
不如说是她自己心甘情愿,
出于对人间烟火的渴望。
正像日常生活中的绿女红男,
女人没有上当男人也没有欺骗,
只是凡俗的日子魅力万千。”
我惊叹于哈尼人对梨花与白马这一神奇意象的想象力。天上人间,花马难分,似与不似,亦真亦幻。抛开神话传说中的因素,它也既是一种朦胧之美,也是某种隐喻和象征。是满山摇曳多姿的梨花更像白马,还是奔跑的白马化作了随风起舞的梨花,已足以引发人们心中的神性与诗意。神性让人心生敬畏,诗意却常常来自于生命中的感动,来自于人与物不可言说的温暖,也来自于人心中的柔软——像一瓣梨花一样纯洁轻柔,也像一匹白马一样奔跑不息。
这是艺术创作中难以追求到的佳境。但在今天,年年开放的梨花,还有多少诗意可存?又与那段传说有关?我们已经懒于追问。每至春天,在水泥森林里囚禁太久了的城里人,大致都会去郊外看梨花,或呼朋唤友,或扶老携幼,驾着车,忍受着路上拥堵之苦,期盼着梨园的清澈与灿烂。但每每一株梨树下人比花瓣多,车比梨树多,欢声笑语中梨花无语亦无泪。花开树枝人相悦,花瓣飘落无人怜。我们早已丧失面对大自然、面对一棵树、乃至面对一棵小草的神性,因此我们的欣赏仅限于感官,只止于嬉戏。没有神性便缺少庄严,缺少韵致,缺少敬畏,甚至缺少文化。梨花树下没有了乡愁,没有了故乡的炊烟,没有了母亲的期盼,更没有了动人的传说。梨花只是梨花,梨花已非白马。梨花仅妆点了我们生活中表浅的浪漫,我们看不到隐匿在梨花深处的王子和仙女,想象不出在天上和凡尘,在人和自然之间,在人和神之间,还有一条浪漫的通道,将会引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条“浪漫的通道”,被英国享誉世界的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称为“内在的超越”。她在其著作《神的历史》中指出:“神就像富含启发能力的诗词和音乐一样,乃是创造想象的产物……神并非真正存在,但‘他’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真实”。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世界文坛巨擘托尔斯泰晚年为什么会对宗教如此痴迷,甚至呼吁人们要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一旦被赋予了神性,他的想象力的空间必然会辽阔深邃,他的文笔也大约也会“有如神助”。他会在梨花丛中看到翩然而至的白马,看到明媚皓齿的王子,看到一花一世界,看到一片花瓣的神性,看到人神共娱世界的美妙。不过,凯伦·阿姆斯特朗又说:“不要寄望神从天而降,而应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心中创造出他的意义来。”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处梨花园中,会有白马王子或仙女,随着梨花雨飘飘而下,但我们心中不应忘记“神”无处不在,他拓展我们的想象力,还催生我们生活中的诗意。就像哈尼人在梨花阵中看到了一匹飘逸的白马。
随着汽车文化的普及,乡野中的梨园越来越像城里人的后花园,每到春天“无人不道看花回”。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春天,我去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州个旧市郊的加急寨看梨花。“加急寨”这个名字很特别,与漫山遍野有条不紊、静静开放的梨花一点也不相配。急的倒是那些在路上争先恐后抢道、占车位的赏花人。梨园如果在平坝上,就难免单一、平面,缺乏立体感。加急寨的梨花却是开在山岗上,开在沟壑里,开在农人房前屋后,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加急寨的梨树不是刻意为之,仿佛是当年随处播撒,随坡就势,任其自然生长。这就在不经意间造就了自然之韵,和谐之美。阳光流转,从这匹山坡照到那匹山梁,光线斜射在梨树上,一团一团的白,似白云飘落,又像风卷千堆雪。农舍就掩映在这些泼喇喇开放的梨花阵中,令人怀疑此景只应天上有;也让人相信,传说中的白马王子,你抽支烟的功夫他就会从山道上转过来。在夕阳西下时,有炊烟飘拂在梨花上,有归去的农人出没在山道上,有牧童驱赶的牛羊悠闲的吟唱,有山歌的调子在晚风中隐约传来。这样的村寨是可以产生神话传说的,当然也催生诗人、作家、画家、摄影家、音乐家——梨花开得也如一支歌,它静静地开,你细细地听,绝对能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诗意,梨花白马的传说也让我想到了唐诗宋词里的那些佳句和意境。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和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吟唱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写得细致入微,带雨的梨花如流泪的贵妃,那是何等的凄美迷离,令人愁肠百结;一个写得宏大叙事、气势磅礴,以梨花拟边塞飞雪,又是何等的壮阔恢弘,叫人热血贲张。梨花可以拟贵妃,也可以喻塞北的雪。现在我知道了,它还可以配白马,让你身陷“梨花像白马,白马似梨花”的美丽迷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时间之河里,人与花已形成亘古不变又不尽相同的生命联系,梨花与白马也构成了某种大自然与神话传说的美妙意境。花开一轮,人增一岁,花开花谢,沧海桑田。花若有情,莫笑人痴。那说好的白马王子,不在花丛中,就在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