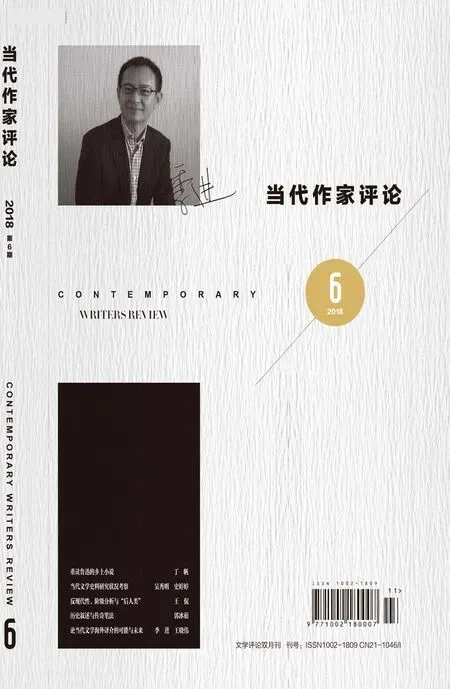万物之思:行在云端的心念
——鲍尔吉·原野散文创作论①
韩文淑
阅读鲍尔吉·原野(以下简称原野)的散文,你就仿佛走进了一座“秘密花园”。里面满是迷宫似的曲径,绿藤环绕;时而开阔无比、时而神秘惊奇;在你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某个隐蔽处或转角处会闪现出一二三四个人,让你猝不及防;待你与之微笑、点头、打招呼、交谈后,你又会放下内心的防备,因为这里没有怪兽和魔鬼。这里都是散落在人间的星子、天使、生灵,他们虽不完美,但他们都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存,他们都是宇宙万物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他们的存在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丰富、灵动、杂糅的证明。当你步履匆匆走出这座花园时,你总是会意犹未尽、不断回头,还想再次进入。因为当你深入其中时,你也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你也成为了天地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你也体会到了作为天地万物一分子的喜悦。这看似略带奇幻的阅读感受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于是我不断地反复阅读原野的散文,以至想在这座花园里安家——为自己的精神和内心,为了确证自己的身份。这里才是真正的“现实”,是我从原野散文中收获到的“现实”。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原野,以往就享有诸多褒誉,如“当代华语最杰出自然散文作家”、“短篇散文之王”等;他的散文被赞誉为“玉散文”、“生态文学中的奇葩”;有研究者称“他写活了他所属的原野”、“读他的散文,好像草原就在眼前”等,正是这些中肯贴切的称号和评价让我毫不犹豫地从书架上选择了他的书。然而当我真正进入他的散文世界后,我读到了比这些表述更丰富、更无限的精义,那是独属于原野散文的气息,是原野散文的特质所在。
一、鲍尔吉·原野的心意
读原野的散文,在那些轻巧灵动、妙趣横生、闪烁着光芒的文字背后,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心意。他想要与万物对话的心意,想要理解整个世界的心意,想要引领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意,更想要人与人破除隔膜、陌生,与自然沟通的心意。在《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中,他告诉我们“热爱故乡首先是热爱和谐生长的大自然,而不仅仅是热爱自己的出生地”。在《云中秘密》中,他写下“天有天的庄稼,云是天的大豆高粱。天有天的河川,云是河川”。还有“河流领着树和花奔跑,云朵在天空追赶”。(《激流河》)“风是草原自由的子孙,它追随着马群、草场、炊烟和歌唱的姑娘。”(《风》)“树是藏在暗处的音乐家”、“树收藏了自然界无数的声音”(《树木是音乐家》)这些朴素的自然真理在原野的散文中俯拾皆是,然而在现代人的生活词典中难觅久矣。他的散文中还到处充满歌声:群山、河水在歌唱,大雁、珊瑚在歌唱,荞麦面、土墙在歌唱……伴随着缭绕的蒙古民歌,我们的眼前是一场盛大的人与自然齐奏的音乐会。但是“沉睡的现代人”,他们沉迷于都市便捷的人造公园、假山楼亭、酒吧KTV中,不仅对生活本真失去了感觉,更对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自然万物漠不关心。可以说,原野的散文“拥有一颗真实和真诚,可以被读者触摸到的‘散文心’”。
这些美好、良善,其实是振聋发聩的心意并非如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而是一种散文的“实在”。这些美好的愿望在原野的散文中都一一实现了,也就是说是可信的。究其根源,这源于他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深入思考,源于他一直葆有的敬畏心——对自然万物的尊崇和敬意。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所缺失的一种自然信仰。这里之所以将这种“敬畏心”称之为一种“自然信仰”,是因为在现代生活意识支配下,当下人们常常淡化、简化,甚至曲解“敬畏心”的含义。其实,我们应该在天人合一和物我同一的语义下理解这种人对自然的应然敬畏。这是一种平等相依和肝胆相照之心,是人对大自然包容奉献给予一切的感恩心理,更是人自身的一种谦卑心理,其内里包含着对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的期冀。原野身上的这种敬畏自然万物的文化思想本性是与其蒙古族文化生长背景紧密相联的。对他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有,但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勃发以及丰富与表达却是在当他走出草原故乡,认知现代思想文化之后,又不断返回故乡、不断进行文化对比中产生的。“在草原俯仰天地,很容易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为什么信神,为什么敬畏天地。人在此处是渺小的。在暮色中,你若发现一个牧归的人在行走,那个移动的剪影,无异于一株树、一头不关四季变化的狼或狗。站在草原,会感到这里的主人决不是人,而是众生。在天地威严的注视下,人仿佛不敢凌驾于其他生灵之上。”(《行走的风景》)正是因为人对自然的这种信仰,草原风光才能与草原文化和谐统一,一直绵延不绝发展至今。原野曾用彩云般绵软的语言描写过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的草原人,那是一个无比温情的场面:“早上玫瑰色的云,晚上橙金色的云,雨前蓝靛色带腥味的云。他们的一生在云的目光下度过,由小到大,由大到老,最后像云彩一样消失。”(《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这种生死与大自然与共的情景是每一个草原住民的人生常态。
至此,原野的心意更加明晰。他的每一本散文集都可以看作是人语与物语的交流,是他与自然相互间的倾情告白。“露水的信”“芦苇为我指路”“群星的呼喊”“雨滴的闹钟”“夜空载满闪电的树林”“光的笑容”“云的事”“太阳在冰上取暖”“水是鱼的大地和天空”“山与树林的合唱”……原野笔下的大自然竟然如此的灵动、有生气,它们就是我们。它们有表情、有情绪、有温度、有颜色、有形状、会生活、有故事、会隐藏。原野不想错过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牛一马,他为它们赞美、祈祷、歌唱,他要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出万物的语言,他要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万物存在的重要意义。
二、植根于大地的满足
读原野的作品有一种满足,那种满足正像林语堂在他《生活的艺术》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想感到满足的,便是低低卧着,紧贴着泥土,跟草根接近。”“紧贴着泥土,跟草根接近”在当下这个高楼广厦充斥的城市文化中似乎是一种奢求,而能满足于这种状态的人心在现代社会更是难得。回归大地、回归自然、众生平等、毫无偏私的心态正是现代人所极度缺乏的。正如那地上的阳光,“一多半照耀着白金色的枯草,只有一小片洒在刚萌芽的青草上。潜意识里,我觉得阳光照耀枯草可惜了。转瞬,觉出这个念头的卑劣。”(《多快的手也抓不到阳光》)人的私念永远只是想着对己有利。原野用自己的散文宣读大自然的真情告白,宣读自己对人类的“审判”。让那些被欲望束缚,永远不知满足为何意的现代人汗颜。可以说,这是原野的另类启蒙,他在温情而又不失热烈的讲述中,消除了人类的戒备心——来自泥土终归尘土的人类应该知道“满足”。
在原野的文字中,一切都被大地、山川、云朵、树木、花草、虫鱼所铺满包围;被我们一呼一吸的空气、被氤氲我们周身的天空白云所铺满包围。他的文字让人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和而非疏远、隔离。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原来,我们并非是独居在狭小公寓楼中的有限个体,相反,我们就站在土地上、生活在自然中,我们就是它们的一员。在雨夜,他写道:“我站在林地,听雨水一串串落在帽子上。我索性脱下衣服,在树叶滤过的雨水里洗澡,然后洗衣服,拧干穿上。衣服很快又湿了。雨更大的时候,我在衣兜里摸到了水,知道这样,往兜里放一条小金鱼都好。”(《雨中穿越森林》)这只调皮未出场的“小金鱼”是否一下子打动了你?站在雨夜淋雨的这种喜悦,现代都市人多久没有感受到了?只有真正匍匐于大地、沉入大地的人,在大地面前足够坦诚、无私、谦卑的人才能得到这份喜悦。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满自大的现代人类,面对下雨的第一反应是躲雨,因为淋雨会使身体“不适”。他们逃避、远离大自然,好像大自然是病毒的集中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生活的世界才是“病毒”的集中营。“有时,当一个人沉醉在这土地上时,他的精神似乎是这样的轻,令他以为是在天堂里。”原野体会到的应该就是这种沉醉的感觉,他被这片大草原深深征服,于是他用自己的文字将这种感受分享给我们,可贵的是,他又并不盲目宠信于这片土地。虽然身居沈阳,但他的很多亲人都还在他的故乡内蒙古大草原成长、生活,因此各种因缘促使他不断返回故乡,可以说他从未完全意义上地离开过草原故土,他总是在走出与返回之间,不断进行跨文化的考量。大地文化或者说自然文化给予了他丰富的滋养,这些滋养使他的散文精神有力,充满气度。既有深广坦荡的包容性,也有剥茧抽丝的批判性。就像这片大地一样,既包容无私,也充满荆棘坎坷。一切生灵生存其上,在受到庇佑的同时也难免受到伤害。因此,我们看到原野的散文并不是一味地赞美草原,批判城市文化;也并非将草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草原人与城市人对立起来,他批判的眼光来自自然世界对人类世界的观照,是一种同情的批判、理解的批判、包容的批判。在展示生活温暖的同时,也展示了生活的无奈和苦痛。在《酒别》中,父亲与表舅喝酒后十里相送,互相送至天亮不忍分别,而小小的我则在这“永远的送别”中沉沉睡去,这类草原清贫生活中的人生乐趣让人忍俊不禁。人类生活的沉重并不因身在何处而有所减轻,这是一种生活必然的承受。原野清醒地告诉我们草原世界并非是世外桃源:“没在牧区生活的人会觉得草原之夜美妙而浪漫,事实上,草原之夜很糟糕。美丽的星月遥不可及,可及的是蚊虫叮咬。”(《火的弟弟》)那个从小就没有母亲的“格日勒”,那个单纯至极、没有心眼、光彩照人的“格日勒”一直受到家族人的排挤,在她父亲去世以后“格日勒站在孤零零泥屋前面,扭着手指,她那天真的笑容该向谁展露呢”?天地是最为慈祥包容的,然而人类世界却不是如此。即使在他歌颂赞美的被大自然眷顾的蒙古草原上,那些面对自然单纯无比的人,在面对同类时也显现出人性的弱点。因此,原野散文中的这种批判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对比后的“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自觉后的释然,读后令人不禁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
人类应该养成的所有美好品质,在大自然中都能找到。原野曾写到“雨”,他说:“雨不偏私,土地上每一种生灵都需要水分和清洁。谁也不知道在哪里长着一株草,它可能长在沟渠里,长在屋脊上,长在没人经过的废井里。雨走遍大地,找到每株草、每个石子和沙粒,让它们沐浴并灌溉它们。”(《雨的灵巧的手》)被人类称之为最伟大的母爱与这雨滴的滋润相比也是稍显逊色的。而要说真情,公鹿对母鹿的真情让人类也是望尘莫及的:“在公鹿心里,这一副美丽的鹿角是为母鹿而生的。它每一次生茸换角,全身都要换一遍血,这痛苦,但它心甘情愿为母鹿这样做。……它们俩一辈子都在恋爱,老是在一起,互相端详。……公鹿回头看母鹿的样子人心都化了;母鹿看公鹿的样子,好像公鹿是一个神。”其实,自然万物之间的情义都是相通的,天空落雪是为了满足孩童的盼望、云朵舞蹈是为了打破飞行员的寂寞、星月的陪伴是为了褒奖养蜂人的勤苦、沙子飞扬喻示了历史之河的奔流,“少年人如果投身大自然,栉风沐雨,他的生命会像野草一样蓬勃,像树一样顽强,心灵像马一样自由”(《火的弟弟》),即使是太阳也会在冰上取暖……原野用他的心、他的眼、他的笔向人类展示了至纯至善的自然之情,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世界的一种别样反思。
三、“会走路的字”的喜悦
张晓风曾在《草言草语·序》中说:“鲍尔吉·原野是一个好的散文家,而好的散文家是敏于观察、敏于剖析且敏于文字的(这三个“敏于”说来好像稀松平常,不过,要同时兼得,恐怕在一百个作者中也难遇其一)。”散文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更直接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它的语言。“敏于文字”的原野,其在汉语语言使用的丰富性、灵活度、充盈感上都长于一般散文。他在挖掘汉语语言的象形力、聚合力、表意力等方面不断进行着自己执著的努力。
读原野的文字总是感觉“新鲜”——“闪电更像一棵树,它的根须和树干竟然是金子做的。当雷雨越来越浓时,天空栽满了闪电的树林。一瞬间长出一棵。雷雨夜,天上有一片金树林。”(《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如果你从未想过闪电给天空种下一片“金树林”,那我们只能崇拜他运用语言的能力。当我们读过他的诸多散文集后,我们会有一种遇到“会走路的字”的喜悦。云、雨、雪、风、鹿、牛、羊、狗、山、树、花、草、星虫、河流、湖泊、故乡、草原……在他各个散文集中四处游走。它们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漫步,一会儿在夜晚歌唱,一会儿说着情话、想着心事。喀纳斯的云“飘到河边喝水。喝完水,它们躺在草地上等待太阳出来,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轻纱般的白雾”。(《云是一棵树》)在云的村庄里,“大云被风撕成小云,有的云被山顶的松树挂住了胳膊,有的云在山坳里睡着了。早上出门的云在晚上回家时,它们的数量、形状、长相都不一样了。”(《云的小村庄》)原野如此细致、耐心、贴切、有感情地不厌其烦地描画这些“云”,仿佛一个年老的外婆兴致勃勃、充满爱意地向外人介绍着自己心满意足的儿孙。这不仅不会让人生厌,其充满人生阅历的讲述反倒让人步步惊喜。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懂“云”,越来越不了解身边的自然。他的散文,每一篇看似相似的主题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结构、修辞、物境、意境、心境完全不同,传达出的情义自然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构筑起原野散文语言的根基——那就是“真情”。
正是因为“用情至深”,他与自己的写作对象才能相互坦诚相见。自然与人事在他面前都真诚地敞开自己。正是因为“情真意切”,他才能在通感的海洋里恣意徜徉,落笔时亲切无比,让读者体会到自然与自然本身、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合无间。那“白金色泽的玉米站满大地”,“如一片等待渡河的人群”。(《乌梁素海的海子》)在大雁的眼中,“天上长着人类看不见的庄稼与花卉,这些植物不需要土,它们的根扎在云彩上。”(《大雁在天空的道路》)乡村的土墙、泥墙,在原野的笔下也铸成一道风景:“命运选择那些土垒在一起,堆为泥墙。它们的躯体就是它们的肩膀,它们没有四肢,只有肩膀。”(《墙》)在原野的语言世界中,大地、海洋、天空是万物共同的存在,它们互相等同:“买一亩大海,就买到了一年四季生长的庄稼。”(《买一亩大海》)“看天空,浓重的蓝色让人感到自己沉落海底。”(《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云是天的大豆高粱”(《云中的秘密》)“马群在奔跑时如同一片云……他们贴着地面飞翔,比鸟还快。”(《马群在傍晚飞翔》)“北方的天空是站立的大海”(《蒙古高原礼赞》)类似的修辞如满天星斗遍布于原野散文中。不熟悉原野散文的人会被这种天马行空的具象性、想象力所吸引,而熟悉的人则会欣赏这语言背后所折射出的“观察视角”。原野观察世界的视角不是单维和主观的,他在极力避免,也在尽量克服、争取还原世界万物的多元视角。可以说,原野散文语言更深层次的作用是一种召唤,是对被遗忘的一种唤醒。原野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唤醒那些沉睡的失语症患者们,更准确地说是唤醒那些对自然生活、对世界本有的真实麻木已久的人。现代生活,内容日益丰富,但是语言表达却日益贫乏,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源于现代意识中大众文化对人的意识的单向度引导与规约。原野的散文热情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现代人离“生活”究竟有多远。人类已经不习惯充满诗情地描述生活了,有谁关心“屋顶的夜”、“黄昏落到哪儿”、“雨落进大海后是什么样子”。读过原野的散文你就会知道,其实诗并不属于远方,它就在我们身边。
色彩的构建是原野散文语言的又一独特之处。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颜色词的盛宴”,它使散文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虽然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不能与无穷无尽的颜色完全匹配,但是一个好作家永远不会失去对这种表达的欲望和挑战。原野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他不独偏爱某一种色彩,他爱自然赋予的所有颜色,因此他笔下的颜色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有灵性的、有温度的,有厚度、有味道、富于变化的,还是可触可摸可感的。通过他的运用,你会觉得颜色是充满生命的,它们就是生命本身。“黄昏的天边有过绿色,似乌龙茶那种金绿。有桃花的粉色。然而这都是一瞬!看不清这些色彩如何登场又如何隐退,未留痕迹。金红退去,淡青退去,深蓝退去之后,黄昏让位于夜,风于暗处吹来,人这时才觉出自己多么孤单。”(《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大自然中的色彩也在世上来来往往,如过客一般,它们有礼有序地按照自然的规律走完自己或短或长的一生。它们并不孤单,它们与自然万物相伴相随,已经融于万物本身,“黄昏里,屋顶一株青草在夕照里妖娆,想不到生于屋顶的草会这么漂亮,红瓦衬出草的青翠,晚霞又给高挑落下的叶子抹上一层柔情的红。”(《黄昏无下落》)妖娆的绿与性感的红如此和谐地统一于黄昏的屋顶,世界顿时充满柔情,那是光与影与万物相互搭配产生的奇异效果,而这种精彩时刻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夕照下的乡村,“白石房变成玫瑰红,黑石房有乌龙茶的金绿”,那有着如“铸铁围身”般黝黑的老樟树,那“大年初一申时问世”的浅黄小片新叶,那“稠黑”的林丛、“蜜汁一样”的暮色……
大地无言却充满声音,自然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声,这是“存在”的一种证明,是“生活”的一种表征。原野用自己的语言为万物发声,讲述它们的历史过往、悲欢离合,物情冷暖、岁月荣枯。“如果马会开口说话,吐露的必是诗一般的柔情,关于河流、草地和郭日郭山那面的马们的爱情。”(《蜜色黄昏》)
四、时间之外的探秘
每当打开原野一本新的散文集,就仿佛是与一位故人相见,里面的文字和记叙的内容似曾相识又充满新意。好像一位说书人语接上回娓娓道来,只是加入了新的人事与风景。不仅不会让你感觉陌生,反倒因为熟悉而更加亲近,更加被吸引。
不同于戏剧与小说的虚构性,散文“实记”的本性决定其更考验一个作家的心性与智慧。散文的写作是创作主体被激活和扩张的过程,经过写作者自我回忆、自我解读、自我阐释与表达,其人生经验才会转变为散文文本。读者可以沿着文本的轨迹找寻到作家的人生。原野的散文不仅有他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对世事人生的观察,也有他对草原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思考,更有对其所居住的城市生活的描摹,而这些创作主题的构架贯穿了他对世界存在本质的理解。他的书写一直隐藏着对世界物质真相的一种追问,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探索。他并不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范畴中探寻一种发展的轨迹,因为自然展示出的本性与规律是超时间的:“到牧区,城里人的空间与时间观念都被改变。牧区的一切都缓慢,像太阳上升那么缓慢。”(《牛比草原更远》)我们看到原野探索世界选取的是一种共时性的、去时间性的角度。在《屋顶的夜》中,他开篇就说:“夜是什么?首先它不是一个对时间的描述。时间是穿过夜与昼的钎子,既不是日,也不是夜。……夜像太阳和露水,每夜来到人们身旁,来到草的身上,站在大路两边”,“夜站在山坡,跟松树并排站立,看公路睡眠的表情。”(《屋顶的夜》)“夜”这个时间名词在这里失去了时间性,变身为“夜”这个物自体本身,它与一棵树别无二致,但是它能看到“公路睡眠的表情”。这种绝妙的体验与表达,只有在共时性——人与自然共存于地球之上的一种存在的共时——的范畴内才会产生。也正因如此,原野发现了很多时间之外的秘密,从而使他的散文散发出独特的神秘气息。原野并没有像其他地理文化散文家那样从自然景物中撷取宏大的历史时空意义、文化意义来进行阐发。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从人尊天重地对自然敬畏的真心实意出发来认识万物。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人的“无知”。虽然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科技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强大和“无所不能”,然而通过他的散文我们知道,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仍然“一无所知”。他们并不知道一片叶子的相思,一朵云的心事,不知道大海的愤怒,更不知道蝴蝶的表情。与人类共存共荣的大自然,是人类的永久伴侣,然而现代意识却造成了人类荒唐可笑的自负心理——对自然的无视与破坏。于是他不断地追问:夜是什么?沙子是什么?风里有什么?云是什么?马是什么?不断地寻找,不断发现人类的自大与无知。
在关于“云”的系列散文中,原野都是在时间之外展开对“云”的思考,讲述云的故事。于是作者提出了:世上有多少朵云?早晨离家的云与晚上归家的云有何不同?云到底在哪儿?呼伦贝尔的云是什么样子?等一系列问题,那些睡觉的云、喝水的云、走路的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会惊异于作者的想象力与思考力,其实这正是因为写作者打破了常规的时间的制约,获得了更广阔的思考张力,人的感受力和体悟能力也有所增强,于是“在秋天的早上,云朵在树林里奔跑,树枝留下了云的香气。夏季夜晚,白云的衣服过于耀眼,它们纷纷披上了黑斗篷。”(《云是一棵树》)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感同身受地了解自然,那么人类将没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原野的散文创作从这一方面来说,是特别而有力的。他要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到自然的本真,自然到底藏在哪儿?他想弄明白夜是什么,他要进入夜。“有几次,我后半夜在大街上走,遇到了更多的夜。它们站在玻璃幕墙的大厦的边上,趴在没竣工的楼房窗台上向外望。”(《屋顶的夜》)与大自然的每一次奇遇其实都是作家的精心安排,原野希望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奇妙,让人类重拾对自然的敬仰与尊重,对神秘的崇敬,对万物的真心。他的散文让人感受到的是,人对自然本应有的原初的理解,我们能对自然给予的最基本也是最应该的尊重和敬仰。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地误读自然,与自然越来越远,他让我们重回自然、重返自然、重识自然,希望打通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
对于世人的分类有很多标准,在原野这里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大自然捶打并塑造过的人,一种是远离自然的人。“被大自然捶打并塑造过的人有自己的一套心智和语言,他们心里装的好东西都不可用金钱衡量,比如月亮与泉水。他们信任并依赖月亮、泉水、露珠、青草和山峰,他们觉得人生的意义和终极目标都可以在大自然当中显现。”(《东泉》)以此反观我们现代“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离土离乡的农牧民,在时间历史的裹挟下日益失去了与自然相处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发现自然赋予人类的“真”“善”“美”的能力。原野以他的敏思、才情,以他散文家特有的智慧、把控语言的能力,将这些呈现出来。他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文字中,以最优秀的走马——“流水似的走马”鼓舞人心,不论脚下的路多么坎坷,都如行在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