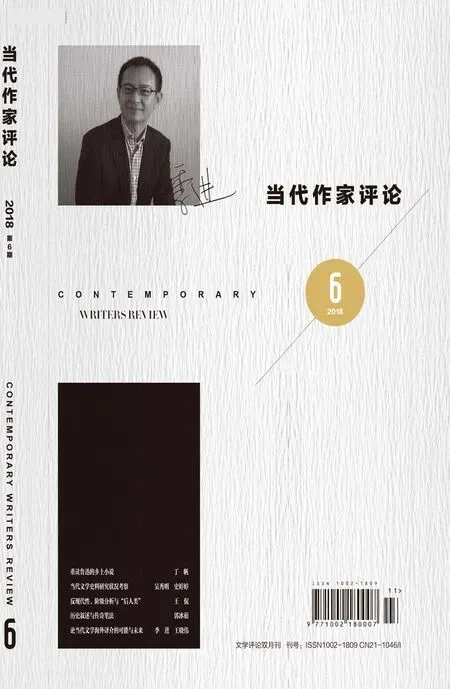重读鲁迅的乡土小说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丛书》序言
丁 帆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在它光环笼罩下的五四文学也算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雨洗礼,进入了百岁的庆典。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旗下的五四文学思想潮流呢?这个问题虽然争论了很多年,对其“启蒙”与“革命”的主旨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历经了许多次的观念转变,直至后来自己的观念也逐渐模糊犹豫彷徨起来。当然不是鲁迅先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而是那种寻觅不到林中之路的沮丧。
按照既正统又保险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以此类推的话,中国乡土小说也就是百年的历史。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这么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就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生来看,它显然是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白话通俗文学也在五四前就早已流行,将它们打入“另册”也是五四先驱者们过激的行为,其留下的遗患也是当初的先驱者们始料不及的。不过,为了适应某种学术研究生态的需要,我们对中国乡土小说发生期的断代保留着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设想,一切留待日后学术空间的拓展。
这套花费了七八年时间编撰成的300余万字的煌煌五卷的《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丛书》,恰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来临前一年杀青,也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的一个隆重的纪念和交代吧。
五四新文学发轫于两类题材,这就是乡土小说和知识分子小说。毫无疑问,仅仅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做为新文学白话文的开端,以此来证明这个带有模仿痕迹的作品具有现代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和晚清以降的讽刺小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同样是揭露黑暗,前者只是停滞在形而下的描写复制生活而已;后者却是注入了形而上的哲思。鲁迅小说的功绩就在于把小说的表达转换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表现形式。窃以为,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局限于他用生动的白话语言创造出新的现代文体,这一点其实在“鸳蝴派”的通俗小说中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鲁迅先生的贡献则是在思想层面的,作为一个对中国社会本质认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深刻、视野亦更加开阔的思想者,鲁迅先生选择乡土小说为突破口,深刻剖析和抨击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本质特征。我将他称作“中国乡土小说的精神之父”并非只认为他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而是将他看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用思想来写作的第一人!因为他作品中反封建的主题思想一直流灌于中国文学的百年之中而经久不衰,这是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抵达的思想境界,也是他的作品永不凋谢的现实意义。
我有时会用一种近乎愚蠢的思想和方法去归纳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作品,十分笨拙地提炼出一个似乎很不相干的“四部曲”来阐释:《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和《风波》是否具有思想和艺术的连贯性呢?是否恰恰构成一部长篇巨制的开端、发展、高潮和尾声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特征呢?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五四文学进入现代时空的第一声炮响,是以一种全新的人文哲学意识进入小说创作的范例,显然,它的思想性是大于艺术性的,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在此是用理性思维来构造乡土社会图景的,其背景图画是虚幻的、不清晰的,人物形象是模糊的,人物是沉浸在自我狂想的意念之中。之所以有人将这部作品当作具有现代派风格的作品,正是由于它的思想性穿透了社会背景的图画,呈现出哲思的光芒,也正是具有模糊而不确定性的人物狂想,让人们看清楚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特征,作品的关键就在于把一个亘古不变的恒定封建社会放大到了一个让人惊恐无措的语境,是一剂让人梦醒的猛药。但是这剂猛药有用吗?答案就在《药》中!
《药》是进一步用猛药来唤醒民众的苦口良方吗?这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是没有抱任何希望的幻想,从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的鲁迅。40年前,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给我们解析《药》的时候,特别强调作品结尾处的氛围,用他的学术观点来说,那种“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恰恰就是作品最点睛之笔,而并非是那个“人血馒头”的像喻。多少年以后,我才悟出了老师的高明之处。显然,这篇作品既是用“人血馒头”来宣示主题内涵,又是用十分清晰的背景图画来展现衬托人物悲剧,理性思维和形象表达的高度融合,让它成为百年文学教科书式的作品典范:突出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当然是题中之要义,而最后那一笔具象的风景、人物、坟茔、老树、昏鸦,构成的正是鲁迅先生在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的艺术选择,所以,那种简洁明快的白描中透露出来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无疑,《阿Q正传》非但是中国百年乡土小说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难以逾越的作品。尽管在鲁迅先生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乡土小说派”的作家,但是后来者只能望其项背,无人能够超越这样恢弘的力作,原因就是其思想的高度缺那么一点火候。这部作品犀利尖锐的思想性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以及艺术上的醇厚老辣,都是任何现当代文学作品无法超越的。阿Q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各个时间和空间中“共鸣”和“共名”的人物形象,它的生命力是鲁迅先生的光荣,却是“老中国儿女”生存的不幸;它的思想穿透力和审美的耐读性成为“鲁迅风”的艺术光环,却成为中国小说,尤其是中国乡土小说艺术的悲剧。至此,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已经达到了“高潮”的境界。但是,“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要比任何一国的国民性来得都更加惨烈,因为我们拥有的不只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拥有更广大的喧闹的庸众,那些个“倒提着的鸭子”似的、嗜好看杀头的大多数“吃瓜的群众”塞满了中国百年的时间和空间,是他们成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让这部作品永恒,然而,这是中国的幸还是不幸呢?!
健全并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使得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序快速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完成的效率,有利于企业的进步与发展。另外,健全并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蓬勃发展。
其实,阿Q也估计错了,他喊出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谶语,也是作者鲁迅先生对社会的误判,其实,根本用不着20年的等待时间,因为阿Q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坚韧的毅力,他们繁殖的速度和密度是空前的,前赴后继,代代不绝的精神让地下有知的鲁迅先生都始料未及。从这点来说,毒舌的鲁迅虽“不惮用最坏的心理”去猜度国人的内心世界,却还是没有看到国民性的种种行状流布弥漫在百年中国各个时空的每一个角落里。
虽然,《阿Q正传》已经是鲁迅作品的“高潮”了,但是,这个永远都解析不尽的Q爷,给我们留下的是永无止境的思考的悲剧!
我时常在苦思冥想一个鲁迅先生创作的无解之谜,那就是,为什么鲁迅会中断声誉日渐盛隆的小说创作呢?我以为,在两大题材之中,知识分子小说除了《伤逝》是绝唱外,其它作品并不是此类题材的扛鼎之作,其书写的衰势似乎可以成为鲁迅变文学创作为杂文写作的内在理由,但是,其乡土小说的创作并未衰竭,像《祝福》那样的力作还不时地出现,他完全有理由继续创作下去的。诚然,鲁迅先生认为用“匕首与投枪”可以更加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用“林中之响箭”更能直接抵达理性阐释的最佳境界。但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鲁迅先生已经早已预判到了中国的悲剧结局是无法改变的。
我为什么幻想把创作早于《阿Q正传》一年的《风波》作为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的“尾声”呢?其理由就在于此。
其实《风波》正是鲁迅先生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兴期,这篇小说无论是在写人还是状物上都有独到之处,但是,最不能忽略的是小说所揭示出的对国民性无望的悲哀,我们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都难以找到那种对鲁迅在此奏响“悲怆交响曲”时的心境描写:赵七爷法力无边的宗法势力主宰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同是劣根性毕现的“庸众”与“吃瓜的群众”虽表现形式不同,指向的则都是国民性的本质。七斤就是被赵七爷驯化了的羔羊,而七斤嫂却是一株生长在封建土壤里的罂粟,夫妻俩相反相成的互补性格,正是烘托出这个“死水”一般的社会已经拯救无望了,任何“城里的风波”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让鲁迅先生陷入极大悲哀的是张勋的复辟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彻底地失去了信心。在这里,鲁迅先生是无力喊出“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这样的诘问句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咒语虽然是指向了对“国粹”的批判,也是小说主题的重要核心元素,但是,它更多地则是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对现实世界的悲哀失望的情绪,是这首“悲怆交响曲”主旋律的重要乐章,它表达出的悲哀旋律一直回响在中国的大地上,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头顶上,遮蔽着人们仰望灿烂星空的视线。
我在这里絮絮叨叨地分析几部鲁迅的乡土小说作品,并不是想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梳理,而是想从源头上找出规律性的特征来:中国乡土小说从来就是沉浸在悲剧描写之中的艺术,唯有悲剧才能表达出这一题材作品的深刻性和现实性,这也是中国乡土小说为什么生生不息的缘由所在。
我们尊崇鲁迅先生是因为他用犀利的笔触刺中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要害,然而,我们并不希望鲁迅作品(包括杂文在内的一切文体)永放光芒,只有鲁迅先生的作品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褪去了它的光环,才证明我们的社会挣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走出了鲁迅先生诅咒的那种世界,也就无需他老人家的幽灵再肩起那“黑暗的闸门”了。
无疑,百年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梳理中国乡土小说研究自身的百年发展历史,总结其经验得失,辨识其学术价值,推进其发展,正是我们“研究之研究”的目的所在。因为,倘若真正想弄清楚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文学是“晴雨表”,而中国乡土小说则是这个“晴雨表”上最精密的刻度。百年来,中国社会是如何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以及如何走进现代文明的脚印都清清楚楚、形象鲜明地镌刻在这些乡土小说作品中了。
他们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学者,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批评家能够洞若观火地指陈这一现象,为乡土作家指出一条切入文学深处的“哲学小路”吗?也许,像我们这样的批评家,即使已经体悟到了这一点,也无法像别林斯基那样去面对惨淡的人生和熟悉的作家。
于是,在重新梳理文学史时,我们能否担当起客观评价这些特殊的文学文本的责任呢?这是我的冀望,但是,在这部丛书中的著作书写中,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要求和高度。这是让我们遗憾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强调种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亦即要明确乡土小说之所指,从而确定“研究之研究”的对象与范围。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鲁迅和茅盾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乡土文学”便成为批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在40年代的解放区,“农民文学”取代了“乡土文学”概念,一统天下。再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仅使用“农村题材文学”、“农村题材小说”的概念。从这种概念内涵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观和学术史观的分野。
中国乡土小说批评,最初是围绕鲁迅乡土小说进行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乡土小说批评紧紧追随着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脚步,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出产大量的批评文章,从而成为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文献最多、时代性最强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在梳理它的过程中,还是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遗憾,也就是说,中国乡土小说百年的批评和评论,能够真正毫无愧色地站在文学史舞台上的并不是很多的,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声叹息。
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研究,最早可以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起。胡适在这篇文学史论性的文章中肯定了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虽然胡适的这番话没有从“乡土文学”的角度去进行考辨,但是,他的眼光和气度,让《阿Q正传》早早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序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专家学者的眼光与客观评判尺度对后来文学史的影响。
但是,我们需要反省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史实问题。
整个文学史的构成既然把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如何看待既往留存下来的“经典”的批评和评论文本?我们必须尊重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就是说,不管你认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引起过反响的理论和批评都要纳入文学史的范畴之列,它是呈现历史样态的文本,从中我们才能拂去现实世界对它叠加上去的厚厚尘埃,看清楚历史的原貌。这一点是文学史家必须尊崇的治学品格,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进入历史的隧道空间来考察。所以,我对那些为了主动“适应形势”而把许多有价值的文本打入“另册”的做法不屑一顾,而对于那种迫于无奈用“附录”来处理一些文本的编辑方式,只能报以苦恼的微笑,因为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常识性的问题,但这确实是无法解决的史学障碍问题。
一言以蔽之,百年文学史可以进入史料领域的材料很多,只有建立史料无禁区的学术制度,才是保证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无疑,在我们编选这套丛书中的四卷之中,试图贯穿这样的史料原则,《中国乡土小说理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文选》《中国乡土小说历史研究文选》和《中国乡土小说流派研究文选》是尽力采取比较客观的史实态度,虽然,我们阈定的是狭隘的“乡土小说”的概念,排除了诸多的“农村题材”的概念和创作理论,但是,“农村题材”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恰恰又是对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一种补充,以及对其自身概念和口号的一种理论反思。比如我们遴选了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被后人总结为“现实主义深化论”,这其中的变异问题,至今仍然有着历史的现实意义。可惜赵树理提出的“中间人物论”却没有被收入,这也算是一个缺憾。而后面收入的浩然的两篇文章《寄农村读者》(1965年)和《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1975年),不仅是作者个人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且也是乡土小说在那个时段宝贵的史料,都是可以纳入中国乡土小说历史研究范畴之列的。
在这里需要检讨的是,由于七八年前制定体例方案时,连我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单单强调了乡土小说概念范畴的狭义性,导致了选编的偏狭,造成了一些遗珠之憾。
其次,史学研究者面临着的最大困境就是史识问题。
史识不仅仅是胆识,而且还得拥有较高的哲学思维和美学鉴赏的水平,只有具备了充分的人文素养的积累,你才有可能具有重新评价以往的作家作品的能力,才能获得对以往文学史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评论家的言论进行重新评判的权力!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具备了吗?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时常会侧目现存的文学史著作,同时在不断否定自己以往的文学史工作。我自以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只是提出了一种假想,离真正撰史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不能以强调外在的条件不成熟做挡箭牌,去遮蔽自己文史哲学养不足的可悲。
只有具备了史实和史识的两个基本条件,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好的文学史著述来。无疑,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先天优势,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初始的工作,我们正在不断地补充着自己的人文素养,以求将来编出一部真正既有史实,又有史识的鸿篇巨制的中国乡土小说史来,也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出现一部真正属于有史实有史识有胆识的中国百年文学史来。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史论和史料的工作总结只是一个休止符,我们期待下一部更有学术含量的著述的问世。
我不相信学术的春天是赐予的,春天在于自身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