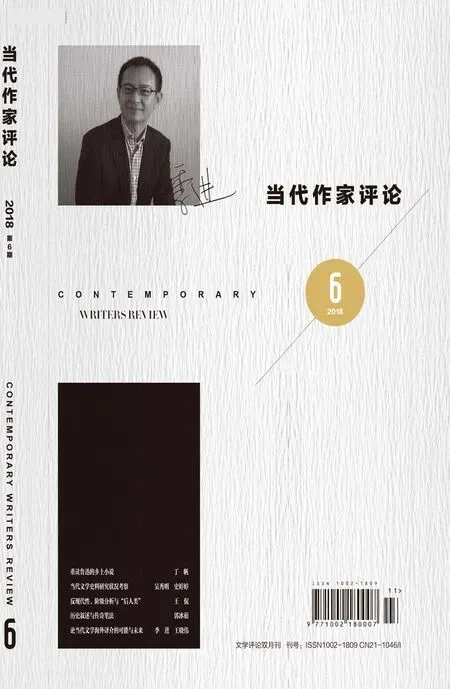丁帆: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孟繁华
丁帆有诸多显赫的头衔,最重要的大概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这两个头衔在当下大学体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毋庸讳言,这是一种学术权力。这一权力,可以在现行的大学体制中畅行无阻。能够在这种权力结构中保持一个学者的本色,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丁帆首先是一位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和批评家,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他诸多成果如《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的玄览》《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与许志英合作)、《重回五四起跑线》《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史》等专著,以及数量庞大的论文和评论,成为这个时代本学科重要成果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国乡土小说史》和《中国新文学史》,是本学科相关研究以及博士、硕士论文引用率较高的两本著作。如果说这些专著材料扎实、言必有据、持论合宜,显示了一个学者在学术层面真实地展开人生的话,那么,他的部分评论、演讲等则表现了丁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个性。比如他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更不要谈知识阶层了》(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讲座)、《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及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生态素描》等这些文章,丁帆一直在拷问一个关键词:良知,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不同学者对现实社会关注方式的一种表征。在丁帆看来,当下中国已“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更不要谈知识阶层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沦陷早已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语。知识分子不仅让这个阶层全面沦陷,而且有意无意地培养他们的继承者。他援引拉塞尔·雅各比的话说:“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士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他进一步发挥说:
这是雅各比描述的美国60年代后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情形,这俨然也成为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针对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种种行状,包括自我的反躬叩问,我以为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丧失了对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在许许多多重大事件中“缺场”,造成大众对重大事件缺乏提供一种有批判深度的价值参照;即使“不缺场”,也只能是作一些趋炎附势的、期期艾艾的、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发言,绝少有那种犀利的批判锋芒文章和言论出现。与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大学里被体制和文化豢养的一群知识分子就连仅存的一点乌托邦的精神也被自我阉割了。所以,你就别指望他们会喊出连封建遗老还能吼上一嗓子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他们只能像阿Q临刑前那样憋屈到死,就连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的勇气和浪漫精神都丧失殆尽。
知识分子的这一状况,与自身没有建立起伟大的传统——或者与这个传统的极其脆弱有关;另一方面,现实也确实没有提供培育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空间的环境和可能。这也诚如丁帆所说:“我们不反对对国家民族的歌功颂德,也不反对给英雄唱赞歌,60多年来,我们给作家的待遇让全世界羡慕和瞩目,它在体制上,甚至在法律层面就规约了作家和艺术家享有的至高的荣誉和权力……问题的关键则是,在中国,这些荣誉和特权基本上是授予‘歌德派’的,在几十年的训导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歌德派’才能在这个体制中获取更大利益,反躬自问,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的所谓作家和艺术家,没有谁一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发出良知的呐喊,因为几十年来的由文学这个政治风云的晴雨表记录下来的痛苦经历,已然将奴性植入了作家和艺术家的血脉之中了,我们没有苏联时期‘白银时代’留下的文学传统,所以我们不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站在一个作家良知的立场上去抨击斯大林时代的残暴行为,同时也不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丁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一判断所言不虚。在我们的当下经验中,这一群体、特别是学院的教授们,谈论最多的是又拿到了什么重大项目,有多少科研经费,如何争取了一级学科,如何应对了评估;接着是抱怨科研经费如何难以使用,财务的脸色多么难看,教授如何斯文扫地尊严如何受挫等。这样的场景在不同的大学屡见不鲜。我们得承认,体制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少有人能够抵御体制对我们的规训。同时,一个巨大的悖反形成了难以超越的怪圈:一方面,他们是这个学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占有了各种学术资源,他们无形地在维护这个学术体制;一方面,他们又牢骚满腹意气难平。他们拿到了体制的好处,同时,又在下属或同行那里获得义正辞严的口碑。因此,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真是遭遇了“内忧外患”。
丁帆在不同的场合批判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这里显然也隐含了他的自我批判。在批判这个群体的同时,他也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深怀不满。他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缺骨少血”。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著名记者舒晋瑜的采访时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就是所有人文知识分子所应该秉持的价值立场,这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和要求,正因为我们太缺失了,所以,有坚守者就十分不容易了。对,作为一个批评家就应该面对一切文学现象做出最公正的独立判断,包括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别林斯基对果戈里的严厉抨击就是知识分子良知的显现,他以公正的价值观彰显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应有的立场。”
读过丁帆的著述,我们对他的学术背景有大致如下的理解:他是一个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俄苏文化,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哺育的批评家。这是丁帆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思想文化背景。在理论批评方面,丁帆或许不那么新潮,当然,这不是说丁帆对新潮理论不了解,不接受。我们从他的《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及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生态素描》等文章中,大致可以了解他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背景。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经过学术训练、学术实践,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现实观察、了解、体悟后的一种自觉选择。如果从学术实践的批判性、开放性和家国关怀的角度理解,他无疑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血脉,正是这样的情怀,也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浓厚的“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还有多少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我们可能并不乐观。因此,丁帆是“50后”一代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学者和批评家。
丁帆还是散文随笔写作的一把好手。他曾先后出版过《江南悲歌》《夕阳帆影》《枕石观云》《江南文化散步》《人间风景》《天下美食》等散文随笔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丁帆作为现代文人的一面。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联想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性情。他们是新文化的先锋、新文学的闯将;他们也是个人生活的缔造者,他们的从容、自信和随心所欲,昭示了那是得天独厚的一代。他们的风采至今仍令人向往不已。
谢冕先生说,现在的文人最大的缺憾是无趣,没有故事。一个文人、一个教授、一个大学,怎么能没有故事呢。现在的文人群体确实是一个了无趣味的群体,但丁帆的散文随笔和日常生活,有文人的趣味。他的《天下美食》,是一本谈论喝酒和美食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士子暮年尚能酒否》,谈了他的饮酒史:
第一次喝酒是在六十年代的少年时期,偷喝了父亲放在碗橱上的一瓶四两装的金奖白兰地,先是偷抿一口,觉得辣中有甜;再喝一口,便觉得甜中藏怡。于是乎,一口一口喝将下去,可谓痛快淋漓,兴奋不已,不知不觉一瓶酒全部下了肚。人说酒是壮胆之物,当我喝第一口时,还生怕被父亲发觉要受罚,然而几口下肚,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口一口把自己十三岁的“少年愁滋味”全然吞咽了下去。第一次酒后的感觉甚好,那是一种微醺的境界,理智很清楚,只是兴奋,更有胆气。
喝酒人的少年时期大概都有这种体验,偷父亲酒喝的那个过程,恐慌、忙乱又不能自己,惟妙惟肖。丁帆的这本散文集,有八篇专事写喝酒,他写在国外和同行喝酒,写插队时喝酒,写古今文人雅士与酒的关系,写师生雅居等,篇篇有趣;特别是他那一声“断酒如断魂”,一个饮者的形象一览无余、八面威风。
散文随笔新著《人间风景》,是丁帆因访问、会议、讲学等到各地游历的见闻和思绪文章。这些风景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自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讨论了“风景的发现”后,一段时间里“风景”旋风骤起。任何风景书写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观察或“眺望”的主体,这个主体对风景有选择或“构建”的权力。因此,他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这些风景表达什么。梭罗写于1854年的《瓦尔登湖》,被誉为美国散文作品最早的典范之一。它平铺直叙,简洁和独到的观点,完全不像维多利亚中期散文那样散漫、用词精细、矫情和具体,也没有朦胧和抽象的气息。丁帆有幸去过瓦尔登湖。这水面不大,森林和土地都很有限的区域,只因梭罗而声名远播。但是,透过眼前的景致,丁帆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为何梭罗当年也没有能够坚持不懈地在瓦尔登湖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两年后他又回到了城市和人群中。无疑,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一种罪孽,不过人类要发展,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如何将代价降低到最低值,让现代文明去除污秽和血,以美好的姿态还自然和原始予人类生活,这才是梭罗作品的全部意义所在。
《豁蒙楼上》应该是丁帆随笔的名篇,甫一发表,便被《新华文摘》转载。豁蒙楼位于南京玄武区鸡鸣寺内、鸡笼山东北端,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其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修建的建筑。作者工作在这座城市,“几乎每天路过鸡鸣山脚下”,几十年后的重新登临,生出的却是别一番感慨。他写到了杨锐,写到了梁武帝,关键是触景生情,他写到了现代的两位大文人。一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五大右派”之一的储安平。这位迷恋“新月派”诗人气质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报人,在30年代初写过《豁蒙楼暮色》。在字里行间,丁帆看到是:“仿佛知识分子生的就是一副忧郁面孔”;十余年过后,另一个大文豪郭沫若也到过豁蒙楼。这时丁帆写到:同为文人,郭先生的豁蒙确实另一种状态,“难得糊涂”、见风使舵,可谓文人的另一种生存形态。据说郭沫若抽签抽中的是第三十五签,为上中签,内云:“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扫却当途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而郭沫若却似乎看不懂,连声对身旁的《南京人报》记者说:“没意思,没意思。”作为游弋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文人,郭先生当然不便说什么。联想到他老人家1949年后的种种表现,尤其是“文革”初期的焚书之举,真是令人感到先生在政治上的豁蒙是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丁帆的这类随笔,是游记也是学术随笔。无论怎样的景致,他总会触景生情“心事浩茫”浮想联翩,自然与人文相互交织自成一格。
能有这样两副笔墨的学者,现在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