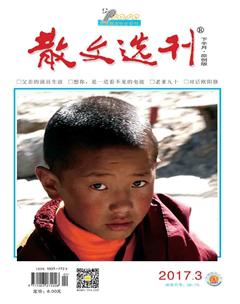我们歌唱白房子
王淑萍
一
那年的春天到来时,村子仍是一副被残冬的余威镇住的样子,枯寂而萧瑟。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一大早,爸爸妈妈就领着我和弟弟来到自留地里。村里的自留地是相互连着的,家家户户都在盖白色的房子,大人抡着锤子,钉着钉子,小孩扛着木棒,拽着绳子,说笑声、喊叫声一阵一阵不断升起来,将凝在村子上空那层寒气惊散了。当最后一根麻绳被大人从房子后面甩出,越过房顶,被站在房子前的孩子接住,再由大人牢牢地绑在房子前的柱子上时,家家的白房子就盖成了。
我和村里的孩子都喜欢把韭菜住的房子喊作白房子,爸爸妈妈却更直白地把它叫作塑料大棚。在那时,塑料大棚在我们县城沿河一带的农田里属于新鲜事物,韭菜,因其生长规律的特殊性,被首选为实验对象。由于大棚的建造技术和种植技术都处于摸索阶段,人们最初给韭菜搭建的这种塑料大棚还是比较简易,被叫作冷棚,用的是塑料薄膜、竹条、木棒和绳子。
那年是我家第二年搭建塑料大棚,被请进大棚的仍然是我家的一亩韭菜。忙活了一上午,爸爸望着拔地而起的大棚,咧嘴笑了。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然后背起手到别人家地里溜达去了。
我和弟弟钻进了我家崭新的白房子。弟弟兴奋得像蚂蚱,使劲蹦跶着伸手去够白色的顶棚,兴奋地说:“姐,这白房子比咱屋里的房子好,房顶绵绵的跟棉花一样。”塑料大棚虽然没有窗户,但椭圆形的白房顶,透亮的白色墙壁,仍让我感到新奇。
我索性躺了下来,把地面当成我的大床。这时候,感觉是很美妙的,躺在大大的白房子里的我,变成了一只最早苏醒于春天的大蚕虫。
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太阳的脸儿一天比一天灿烂。韭菜齐刷刷长到有一寸长时,韭菜芽由黄变绿。爸爸和妈妈说,照这样的速度,再有半月左右,韭菜就能长到八九寸长,就可以铲了去卖。
妈妈计划着这些,其实是忽略了天气的料峭不定。在北方,身为季节的长子,春天,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任性胡闹,想干啥就干啥。就在爸爸给塑料大棚通风的那天下午,原本是温和细软的春风,不一会就变得面目可憎了。它怀揣千万把刀子,呼呼地游走在村子,似乎要将村子肢解,村子吓得瑟瑟发抖。最遭殃的是村里所有人家的塑料大棚,风刀子游龙一般钻进塑料大棚,鼓荡着,翻滚着,然后唰唰唰地将好端端的大棚割得体无完肤。爸爸和村里人赶去时,棚里的木头柱子和竹板架子已经东倒西歪,被撕碎的塑料片戏谑似的在村子上空忽上忽下飘着,或是挂在树枝上招摇着,让人看着气恼,却无可奈何。
村里人在不安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风收住了魔性,大家跑到地里去查看,正如他们所担心的,昨天还好好的韭菜芽一夜间被就冻死了。因为痛惜韭菜幼芽,痛惜新建的塑料大棚,痛惜付出的心血和热情被瞬间摧折,好些人都站在地埂上愤愤地大骂,该死的风,简直是个大坏蛋。妈妈惆怅着脸挖苦爸爸:“你的木匠手艺到底好在哪里?连个棚子都搭不结实,这下怎么办?”
爸爸没好气地说:“只能重新搭建大棚了,还能咋办?”
“哪能那么容易呀?前面的塑料布都是赊来的。”妈妈深深叹气道。
二
新盖的塑料大棚被风撕得片甲不留,新出芽的韭菜冻没了。
大家开始带着钉锤已经对歪倒的柱子和竹板进行扶正和修缮。妈妈和几个婶子心里不舍,她们将那些被风撕碎,挂在树枝上、丢在渠沟里、躺在路旁枯草中的破破烂烂的塑料片捡了回来,一片一片缝缀在一起,连成几张大片的,盖在韭菜根上。爸爸硬着头皮到城里农资销售店,又赊来整张的白塑料薄膜。
爸爸和妈妈叫上我和弟弟,又去搭盖塑料大棚。干活时,妈妈喊:“要弄结实,要弄结实,再不敢出麻烦了。”爸爸说:“你放心吧,这次建的大棚能抗住十级台风呢!”他特意在隆起的塑料棚身上多勒了几根绳子和布条,还给大棚的四周压上更厚的泥土和大石头。
或许是妈妈的喊叫起了作用,春天终于恢复了温情的面目。春风变得分外柔和,太阳更加热心,不几天,韭菜缓过劲,重新冒出小叶片来。爸爸给韭菜通风,揭开大棚两边的门洞后,再也不敢离开了,而是蹲守在大棚旁边,像是对上次干过坏事的风仍耿耿于怀,他想等待它的到来,然后将它逮住,以解心头之恨。
爸爸每天小心翼翼地照顾大棚,韭菜生长得比较顺当。一个月后,我和弟弟开学时,韭菜已有两拃长,到了开铲的时候。爸爸开始做准备工作,收拾架子车,磨铲子,又将曬干的马兰草放在水盆浸泡。泡软后的马兰草柔韧结实,适合捆绑韭菜。因为要赶早去卖,韭菜得在凌晨四五点铲。爸爸妈妈叫醒我和弟弟时,天还黑黑的,尽管不愿意,我们还是随着他们出发。
到韭菜大棚里,爸爸把马灯点着,挂在柱子上照亮,爸爸妈妈蹲在前面铲,我和弟弟跟在后面,把铲下来的韭菜一捆一捆捆好,摆在我们身后。大棚里不算太冷,只是时间一长,感觉有些憋闷。
这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一家,村里所有人家都在铲韭菜,而那又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
天渐渐亮时,铲下来的韭菜够装一架子车了,我们把捆好的韭菜抱出大棚,交给爸爸,爸爸将韭菜根一律朝外,一捆一捆码到架子车上,码起来的韭菜垛子高得像座小山。妈妈生怕早上的寒气伤着韭菜,又把一块旧帆布盖在车上。
爸爸将韭菜拉到街上去卖。五六里的乡路坑坑洼洼,还有大坡小坡,并不平坦。我和弟弟正好要去上学,便帮爸爸推车。一路上不止我们和爸爸的身影,我们车子的前面和后面,都是拉着架子车去卖菜的村里人。他们,有的埋头拉车,急急赶路,有的则相互吆喝着说话,从他们沙沙的脚步声和笑谈声中,听得出他们的内心和爸爸一样都是欢喜的。这样的买菜队伍浩浩荡荡,生气勃勃,雄壮成一条迎着晨光向城里昂扬行进的长龙。
卖菜有时并不顺利,那些年,最繁华的卖菜市场是在县城西街,每天早上的西街,买菜人和卖菜人会聚于此,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那些卖菜者都是来自县城近郊各个村子的农民,他们的架子车和毛驴车密集地摆放在街道两边。爸爸去得稍迟点,找不到空地停放车子了。爸爸只有从西街辗转到东街或者南街的小巷小道,吆喝着尽快把韭菜卖完。不光爸爸,其他来自乡村的卖菜人也是如此。农民的艰辛,就是这样随着他们的脚步,从土地延伸到城里。
卖完韭菜后,爸爸还要急急地赶回家,地里的其他农活也得打理。
三
后来,村里人都不再种植冷棚,而是侍弄起暖棚来。暖棚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房子,除了美观气派,更重要的是比较坚固,保暖性强。三面围着土打墙,柱子是水泥铸的,房脊呈斜坡,上面备有稻草编成的帘子,帘子随着早晚天气变化,可以拉起放下,用于调节棚内温度。这时候,白房子里除了韭菜,还有黄瓜、茄子、辣子、西红柿、芹菜、白菜、豆角……
我家发展到四个暖棚。韭菜、黄瓜和西红柿平起平坐,各自独享一室。菠菜、油菜、白菜、芹菜、香菜等这些随意撒上种子,不需要特别照顾的小菜们被妈妈规划在一个棚里。与那些小菜不同,最难伺候的是黄瓜和西红柿。除了操心日照和通风,从它们长出茎蔓开始,就要为其搭上架杆,让它们攀爬生长。搭架杆需要许多枝条,枝条往往不够,爸爸便拿起长把的砍刀,到我家那些白杨树身上一棵一棵地砍。架杆搭好后,黄瓜和西红柿也就进入了开花期。这时候,已是冬季,尽管外面天气阴冷多风,偶尔还碰上大雪,但棚里面是热烘烘的,棚里的活,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候。西红柿需要整枝打杈,还要点花。打杈是为防止西红柿秧叶徒长疯长,不坐果实。点花就是给绽开的花朵抹药,避免那些黄灿灿的花朵脱落,花凋谢了,收获的西红柿就只能是寥寥无几。
给西红柿点花也是很缠人的活,一手端着药碗,一手要轻轻按住娇嫩的花枝,往碗里蘸,让每朵花、每束花都涂上药汁。我们对这些花儿涂涂抹抹,梳洗打扮,心里盼的是它们能结出硕大的西红柿,让我家挣到更多的钱。但是整整一座大棚,无数的黄花花啊,又开得不齐整。全家人钻进棚里,好几天都做不完,棚里闷热潮湿,稍稍一会,整个人就像蒸了一场桑拿,浑身湿溜溜的。我和弟弟动不动会因为忍受不了热,大喊大叫着累。
爸爸妈妈最害怕的不是吃苦出力,而是棚里的蔬菜生出毛病。比如黄瓜,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黄瓜最爱生虫,虫子一旦泛滥,黄瓜叶子会很快干枯,黄瓜花就纷纷凋谢,花一谢,黄瓜就颗粒无收。因此,对黄瓜三天两头进行喷药灭虫是必须要做的。但是,爸爸妈妈有好几次因为忙不过来,这项工作就出现了拖拉,一拖拉,惨烈的事情就爆发了。那次我家因为虫害,整整一座大棚,陆陆续续才开始结小黄瓜的黄瓜秧,不到半月就抱病而亡了。在清理大棚时,妈妈非常伤心,她抱着枯掉的黄瓜蔓准备出棚时,脚下一绊摔倒了,妈妈跌爬在藤蔓上,一气一急竟然哭起来,那情形,就像自己辛苦拉养的孩子半路夭折一般。
从冷棚到暖棚,长期地置身于闷热潮湿的环境,妈妈患上了职业性的风湿病,腰腿疼痛,弯曲难伸,爸爸的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多次,我对爸爸妈妈说:“干脆别种棚了。”但是,爸爸说:“没办法,一家人要生活,光凭几亩薄田连你们以后上大学的学费都攒不够。大棚蔬菜收入好,我们舍不得放弃。”
这些白色的房子啊,亮堂着爸爸妈妈的心,也亮堂着我们家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