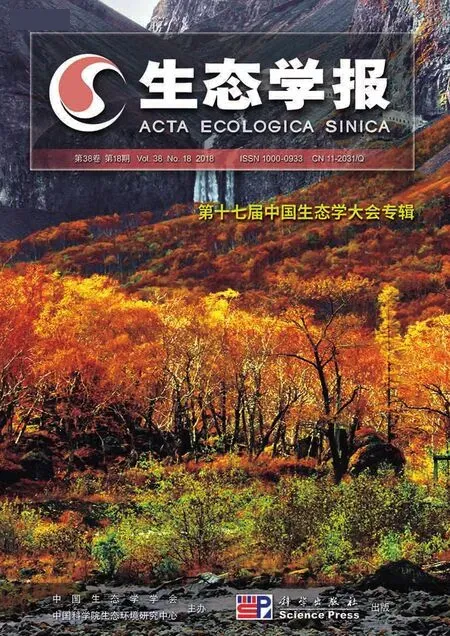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生物量分配格局
聂秀青,熊 丰,李长斌,杨路存,肖元明,周国英,*
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8 2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8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灌丛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具有分布广泛,生产力高等特点,在群落的演替与生态保护和能源替代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中国是全球灌丛分布面积最广泛的国家之一,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20%,约为现存森林面积的2倍[2]。然而,相比较草地与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灌丛生态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灌丛生态系统的研究列入草地或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一部分[3]。因此,灌丛生态系统在我国陆地碳汇评估中是最不确定的[1]。灌丛是青藏高原灌丛生态系统重要的植被类型之一,有必要开展灌丛生态系统的研究。
植物生物量包含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由于地下生物量的数据相对较少,地下生物量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4]。生物量分配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准确估算地下生物量[5-6],而且有助于评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植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7]。草地生态系统生物量的大小及其分配关系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区域尺度,如青藏高原草地[8],内蒙古草地[9]等;到国家尺度,如中国北方草地[10],中国草地[11-12]等。整体而言,中国草地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幂函数[11-13],尽管高寒草原,温性荒漠草原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山地草甸,温带草甸草原,温性草原生态系统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因此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存在不同的相关关系。
灌丛生态系统植被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分别包括植物灌木层生物量与草本层生物量。已有学者对青藏高原灌丛生物量进行相关研究[14- 20]。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单一群落类型,如金露梅群系;或者仅涉及到地上生物量或地下生物量。虽然高寒灌丛生态系统中的灌木层地上地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大小,分布格局及其与年均温度和年均降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20],但未涉及草本层的生物量分配与气候因素关系的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分配关系及其气候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该领域的认知。本研究通过2011—2013的野外采样与室内分析,试图明确:(1)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大小及其相关关系。(2)草本层的根冠比大小及其与气候因素之间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图1 样地分布示意图Fig.1 Locations of sampling sites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位置为31.88°—38.06°N与95.30°—102.38°E之间。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典型的植被类型如百里香杜鹃群系(Rhododendronthymifolium),金露梅群系(Potentillafruticosa),山生柳(Salixoritrepha),鲜卑花群系(Sibiraealaevigata),细枝绣线菊(Spiraeamyrtilloides),头花杜鹃(Rhododendroncapitatum),青海杜鹃(Rhododendronqinghaiense),鬼箭锦鸡儿(Caraganajubata)等。草本层优势种主要为矮嵩草(Kobresiahumilis),高山嵩草(Kobresiapygmaea),珠芽蓼(Polygonumviviparum),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紫花针茅(Stipapurpurea),垂穗披碱草(Elymusnutans)等。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分别为-5.6—8.9℃与17.6—764.4 mm[21]。
1.2 样品采集
2011—2013年每年的7—8月,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进行了连续3年的采样活动,选择了49个样地,147个样方(图1)。每个样地设置3个样方,其中高寒灌丛的样方调查面积为5 m×5 m。在每个样方中,再设置一个1 m×1 m的子样方。子样方内所有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均用收获法获取[22]。地下根用水清洗,通过根的颜色,一致性等判断依据,将死根拣出。活根与相应的地上部分在65℃的环境下烘干至恒重,精确至0.1 g,用于分析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4-5]。具体采样方法见《生态系统固碳观测与调查技术规范》[23]。
1.3 气象数据
由于采样地附近没有相应的气候站点,因此样地的温度与降雨等气象资料来自全球气候网站(http://www.worldclim.org/)[24]。通过采样地的经度、纬度等数据提取样地的月均温度与月均降雨量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出各个采样点的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的数据。
2 结果和分析
2.1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生物量的大小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与根冠比的范围分别为39.3—289.2 g/m2,145.7—1648.2 g/m2,1.4—9.2(表1), 平均值为132.0 g/m2,526.4 g/m2,4.1,中值分别为121.1 g/m2,342.8 g/m2,3.6(图2)。
表1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灌木层与草本层)与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与根冠比
Table1Thesizeofabovegroundbiomass(AGB),belowgroundbiomass(BGB)androot/shootbiomassratio(R/S)inthealpineshrublandecosystems(shrublayerandgrasslayer)andgrasslandsontheTibetanPlateau

高寒生态系统Alpine ecosystem地上生物量AGB地下生物量BGB根冠比R/S中值Medium范围Range中值Medium范围Range中值Medium范围Rangen参考文献References灌木层Alpine shrub layer1036.4340.2—4816.5951.6170.2—2597.31.00.5—2.049[20]草本层Alpine grass layer121.139.3—289.2342.8145.7—1648.23.61.4—9.249本研究高寒草地Alpine grasslands59.79.8—347.5330.544.6—2784.85.80.8—13.0112[8]
AGB: 地上生物量,Aboveground biomass;BGB:地下生物量,Belowground biomass;R/S:根冠比;Root/shoot biomass ratio

图2 草本层生物量与根冠比的频率分布图地上生物量(AGB),地下生物量(BGB),根冠比(R/S)Fig.2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AGB), belowground biomass (BGB), and root/shoot biomass ratio (R/S)
2.2 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关系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呈幂函数相关关系y=8.0x0.83(R2=0.48,P<0.001) (图3)。

图3 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s between aboveground biomass (AGB)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BGB) in the Tibetan Plateau grass layer
2.3 气候因素对草本层根冠比的影响
随着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的增加,青藏高原草本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图4)。

图4 根冠比与年均温度、年均降雨量的关系Fig.4 Relationships between root/shoot biomass ratio (R/S) and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3 讨论
3.1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大小与根冠比的大小
Yang 等测定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分别为59.7 g/m2,330.5 g/m2,均小于高寒灌丛草本层的地上生物量的121.1 g/m2与地下生物量的342.8 g/m2。首先,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的土层较薄与土壤较为贫瘠[25]。相比较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具有更多的凋落物输入,其不仅具有草本层的凋落物,还具有灌木层的凋落物[26]。大量凋落物的输入,利于土壤腐殖质含量的增加[26],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为草本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条件。其次灌木层为草本层的生长提供相对较高的温度。已有研究表明,灌木层下土壤的温度显著高于草地生态系统下的土壤温度[27-28]。青藏高原具有寒冷、干旱的气候特征[29],而灌木层的存在为草本层生长提供更为适宜的温度。因此相比较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的草本层具有更大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的根冠比为3.6,小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根冠比(5.8)[30]。一方面,较多的凋落物输入可能会促进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土壤具有较高的有机质,草本根系更容易获取养分;另一方面,灌木层的存在,抑制草本层对光照的吸收。植被会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地上部分,获取更多光照,以实现最大速率地生长[31]。因此,相较于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草本层具有更大的根冠比。高寒灌丛灌木层的根冠比(1.0)[20]小于草本层的根冠比(3.6)。这说明,相较于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灌木层,草本层将更多的生物量碳储存在地下。
3.2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表明,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呈现幂函数相关关系y=8.0x0.83(R2=0.48,P<0.001)。然而,通过对中国草地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研究发现,不同的草地类型其相关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别,虽然整体而言,符合幂函数的关系,但是温带草原,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P>0.05)[11]。
青藏高原草地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符合幂函数(R2=0.67,P<0.001)[8],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灌木层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也呈现幂函数关系(R2=0.66,P<0001)[20]。这表明,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与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与灌木层)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均符合幂函数的关系。因此,在估算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与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地下生物量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幂函数的关系进行推算。
3.3 气候因素对草本层根冠比的影响
随着年均降雨量与年均温度的增加,草本层的根冠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该结论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研究结果相同[8]。这表明气候因子并不能显著影响青藏高原草本植物的生物量分配。然而,随着年均温度的增加,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灌木层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地上部分,使得根冠比降低[20]。青藏高原地处高海拔区域,年均温度较低,CO2的浓度降低[32],植被的生长季缩短[33]。当温度变高时,植被会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受限制的地上部分,来增加光合作用[34]。然而,青藏高原草本植物的根冠比与年均温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8]。这表明,青藏高原灌丛生态系统的根冠比与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根冠比对温度的响应是不同的。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年均温度也在增加[34]。增加的温度会促进灌丛植被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地上部分。灌丛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青藏高原灌丛的扩张。